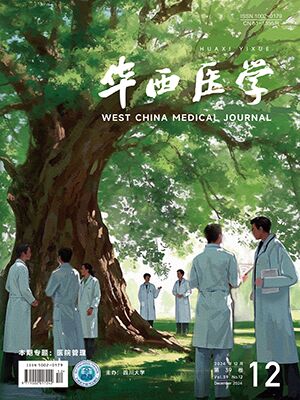引用本文: 劉芮杉, 劉婭妮, 張世洪. 輸血相關可逆性后部腦病綜合征伴遲發性腦血管痙攣一例. 華西醫學, 2024, 39(5): 833-837. doi: 10.7507/1002-0179.202403303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病例介紹 患者,女,48 歲,因“頭暈 17 d,頭痛 7 d,雙眼視力下降 4 d”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以下簡稱“我院”)神經內科。患者既往有慢性貧血病史 10+年,未規律診治,本次病前無腹痛、黑便;否認高血壓、腎病、使用腫瘤化療藥物以及其他血管活性藥物特殊病史。2021 年 6 月 4 日患者出現頭暈,伴視物旋轉,無發熱、意識不清、肢體無力、麻木以及耳鳴等,立即于當地市級醫院住院治療,當天完善血常規提示血紅蛋白 38 g/L,次日開始 2 d 內共輸注紅細胞懸液 1 200 mL,輸血過程中收縮壓一度升高達 160 mm Hg(1 mm Hg=0.133 kPa)。輸血后患者于 6 月 7 日復查血紅蛋白為 100 g/L,頭暈緩解后回家。6 月 14 日患者出現頭痛,額部脹痛為主,伴視物模糊,無發熱,自服止痛藥后頭痛癥狀稍緩解及視物模糊減輕;6 月 17 日晨起后雙眼視力明顯下降,僅有微弱光感,伴頭部脹痛明顯,再次于當地市級醫院完善檢查(6 月 17 日):頭部 MRI 示左側枕頂葉腦回腫脹,呈長 T1、長 T2 信號,液體衰減反轉恢復(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序列高信號,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稍高信號,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spersion coefficient, ADC)稍低信號。予以抗血小板等急性腦梗死相關治療后,視物模糊無好轉,于當天由外院轉入我院急診科。急診血壓 190/84 mm Hg,并于當天完善相關檢查:血紅蛋白 103 g/L;頭部 CT 平掃示:顱內未見確切異常密度影;頭頸部 CT 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 CTA)示:基底動脈遠段、右側大腦后動脈管腔不均勻中-重度狹窄,雙側椎動脈 V4 段、基底動脈纖細(圖1a);CT 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 CTP)示:雙側大腦半球灌注基本對稱,未見局限大片低灌注區。
 圖1
患者發病期間顱內血管痙攣和腦實質影像學演變
圖1
患者發病期間顱內血管痙攣和腦實質影像學演變
a. 2021 年 6 月 17 日頭頸部 CTA 結果顯示右側大腦后動脈不均勻中-重度狹窄;b. 2021 年 6 月 23 日頭部 CT 結果顯示雙側頂枕葉大片低密度影,左側頂枕葉病灶見條狀高密度影;c~f. 2021 年 6 月 24 日頭部 MRI 結果顯示雙側顳頂枕葉皮質及皮質下片狀、斑片狀 T1 低信號(c)、T2 高信號(d)、T2-FLAIR 高信號(e),雙側頂葉部分腦溝內可見少許 SWI 低信號(f);g、h. 2021 年 6 月 25 日 DSA 結果顯示右側(g)及左側(h)頸內動脈顱內段中度狹窄、右側(g)及左側(h)大腦中動脈主干彌漫重度狹窄;i. 2021 年 6 月 30 日頭部 MRI T2-FLAIR 結果顯示病變范圍較前增大;j. DWI 結果顯示右側額葉、雙側顳頂枕葉及島葉多發斑片狀高信號;k. ADC 結果顯示右側額葉、雙側顳頂枕葉相應區域部分低信號;l. 2021 年 7 月 12 日頭頸部 CTA 結果顯示右側椎動脈略纖細,雙側椎動脈、頸內動脈、頸外動脈均未見異常管腔狹窄。CTA:CT 血管造影;FLAIR:液體衰減反轉恢復;SWI:磁敏感加權成像;DAS:數字減影血管造影;ADC:表觀彌散系數
患者經急診對癥處理后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轉入我院神經內科繼續診治,入科后體格檢查:血壓 151/86 mm Hg,脈搏 61 次/min,呼吸頻率 20 次/ min,體溫 37℃。神志清,表情淡漠,反應遲鈍,雙眼無光感,無構音障礙,四肢肌力 5 級,雙側病理征陰性,腦膜刺激征陰性。6 月 22 日患者言語混亂、認知下降,迅速出現呼之不應,雙眼向右凝視,雙側瞳孔等大等圓,約 3 mm,對光反射遲鈍,左側肢體無自發活動,隨即復查血液指標,血紅蛋白 120 g/L,血糖、生化以及免疫指標大致正常。入院診斷:可逆性后部腦病綜合征(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 PRES)?6 月 22 日完善腰椎穿刺術,腦脊液初壓 120 mm H2O(1 mm H2O=0.009 81 kPa)、末壓 10 mm H2O,腦脊液常規、生化、微生物培養無明顯異常。6 月 23 日復查頭 CT 報告:雙側頂枕葉大片低密度影,其中左側頂枕葉病灶見條狀高密度影(圖1b);6 月 23 日 MRI 頭部增強掃描:雙側顳頂枕葉皮質及皮質下、左側島葉片狀、斑片狀長 T1、長 T2 信號,FLAIR 高信號(圖1c~1e),雙側頂葉部分腦溝內可見少許短 T2 信號影,磁敏感加權成像呈低信號,提示蛛網膜下腔出血(圖1f)。6 月 24 日復查頭頸部 CTA 報告:雙側大腦前動脈 A2 段局部重度狹窄,雙側大腦中動脈 M1 段管腔纖細,基底動脈遠段、右側大腦后動脈官腔不均勻中-重度狹窄,雙側椎動脈 V4 段、基底動脈纖細,即前、后循環均存在管壁不均勻狹窄,考慮顱內廣泛血管痙攣可能。6 月 24 日復查 CTP 報告:雙側額頂枕葉見異常低灌注,表現為雙側額葉、頂葉、枕葉存在腦血流流量與腦血流容量不匹配區。于 6 月 25 日行全腦血管造影(圖1g、1h):雙側頸內動脈顱內段中度狹窄、雙側大腦中動脈主干彌漫性重度狹窄;右側椎動脈外段長段輕中度狹窄,基底動脈遠端漸進性纖細,提示前后循環顱內大動脈廣泛嚴重痙攣。6 月 26 日患者能自發睜眼,不能配合檢查,有亂吐口水、打飽嗝、發出特殊聲音等精神癥狀,疼痛刺激右上肢有自發活動,右下肢有回縮,肌力可達 3 級,左側肢體無活動。6 月 30 日復查頭顱 MRI:右側額葉、雙側顳頂枕葉及島葉多發斑片狀長 T1 長 T2 信號影,FLAIR 高信號(圖1i),彌散受限(圖1j),相應區域 ADC 部分低信號(圖1k),雙側頂枕葉皮質邊緣可見短 T1 短 T2 信號,考慮雙側大腦半球以后部皮質為主梗死伴少量出血。入院 2 周后患者能進行簡單語言交流,少量口中進飲食,左側肢體偏癱好轉,肌力達 3 級,右側肢體肌力 5– 級,視力障礙無變化。住院期間予以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100 mg、1 次/d)、口服尼莫地平(30 mg、3 次/d)、靜脈注射地塞米松(6 月 25 日—29 日,10 mg、1 次/d)、靜脈滴注甘露醇(250 mL、每 8 小時 1 次,逐漸減量至 125 mL、每 12 小時 1 次)減輕腦水腫、補液擴容、康復理療等治療。住院治療 16 d 后,患者神志清楚,言語較清晰,可進行簡單對話和動作,左側偏癱明顯緩解,四肢肌力可達 4 級,視力無變化,血壓穩定,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出院,出院時診斷為 PRES。
2021 年 7 月 12 日(發病后 38 d),患者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上錦醫院復查頭頸部 CTA(圖1l)未見異常管腔狹窄。發病后 3 個月經電話隨訪,患者雙眼視力恢復,遺留視野缺損,近記憶力下降,時間、地點、人物定向力正常,可與人正常交流,可獨自行走,左下肢肌力 5– 級,其余肢體肌力正常,生活基本自理。發病后 1 年經電話隨訪,患者視野缺損程度同前,記憶力恢復基本如常,肌力恢復如常,可正常交流、行走。
討論 PRES 于 1996 年首次報道,主要臨床表現包括急性起病的頭痛、癲癇、視力障礙,可出現精神、意識狀態改變及偏癱等局灶性神經功能缺失體征[1]。其影像學典型改變為雙側頂枕葉病變,MRI T2-FLAIR 序列呈高信號。PRES 相關危險因素主要為高血壓、細胞毒性藥物、敗血癥、先兆子癇或子癇和多器官功能障礙[2-3],但由輸血誘發 PRES 較少見。本文報告的該例患者符合 PRES 的典型臨床特征,在發病前有短期內快速輸血史,輸血后血壓明顯增高,應考慮輸血為 PRES 的重要病因,即輸血相關 PRES。
截至目前,國內外尚未開展以輸血為主要病因的 PRES 病例的大樣本病例對照研究或隊列研究,相關報道主要局限于個案病例的形式。為明確輸血相關 PRES的特征,并為 PRES 的診治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指導,本研究小組檢索 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中國知網、維普和萬方數據庫于 2024 年前發表的有關輸血相關 PRES 病例報道。由于鐮狀細胞貧血與器官移植相關 PRES 有獨特的發病機制[4],因此合并上述疾病的輸血相關 PRES 病例報道未被納入。最終,共檢索到 30 篇輸血相關 PRES 病例報告,患者 36 例[5-34]。由此,在納入本文報告病例后,共報告輸血相關 PRES 病例 37 例。
在 37 例患者中,男性 2 例,女性 35 例;年齡 6~75 歲,平均年齡(43.16±14.68)歲;2 例男性及 28 例女性均為亞洲國家患者;貧血病程:慢性貧血 28 例(75.7%),其中在慢性貧血的基礎上急性失血 1 例(2.7%),其他急性或亞急性失血 5 例(13.5%),貧血病程不詳 4 例(10.8%);慢性貧血的病因以血液系統疾病[39.3%(11/28)]與婦科疾病[39.3%(11/28)]居多,急性或亞急性失血的病因以術后出血[60.0%(3/5)]居多;發病前合并高血壓病史 10 例(27.0%);輸血量:血色素升高 50 g/L 及以上 23 例(62.2%),血色素升高 50 g/L 以下 7 例(18.9%),輸血量不詳 7 例(18.9%);神經系統損害起病時間 1~18 d,多發生在輸血后的 1 周內;常見臨床表現:癲癇 33 例(89.2%),意識障礙 27 例(73.0%),頭痛 26 例(70.3%),頭痛有“雷擊樣”特征 4 例[15.4%(4/26)],視力障礙 13 例(35.1%),偏癱或四肢癱 6 例(16.2%),部分患者出現惡心、嘔吐、認知功能下降、精神癥狀等;頭部影像學檢查:雙側頂枕葉與額葉皮質下白質區域為病變常見部位,多呈 T2 高信號、DWI 低信號或等信號、ADC 高信號的血管源性水腫,但仍有 5 例(13.5%)存在以 DWI 高信號、ADC 低信號為特征的細胞毒性水腫,其中 4 例(10.8%)同時存在血管源性水腫及細胞毒性水腫;3 例(8.1%)伴腦實質出血,2 例(5.4%)伴蛛網膜下腔出血;行動脈血管檢查(包括磁共振血管造影、CTA、數字減影血管造影等)16 例(43.2%),其中血管痙攣 14 例[87.5%(14/16)],包括同時累及大腦后動脈和大腦中動脈 9 例、僅累及大腦后動脈 4 例、僅累及大腦前動脈 1 例;預后大多良好,28 例(75.7%)未遺留任何癥狀,9 例(24.3%)遺留視力障礙、意識障礙等癥狀。
上述病案報道的匯總結果(以下簡稱本系列患者)提示,輸血相關 PRES 在流行病學特征、合并癥、血管痙攣以及顱內水腫等方面呈現出一定特點,且其臨床癥狀與預后與輸血情況密切相關。盡管目前缺乏大型臨床研究的報道,但國內外學者已初步對輸血相關 PRES 的發病機制、臨床特征、影像學表現、治療與結局進行了探索。
① 發病機制。PRES具體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既往報道中以腦高灌注學說最常見,即快速進展的高血壓超出腦血流自動調節上限,腦灌注增加,血腦屏障破壞,液體外滲導致血管源性腦水腫;其他學說包括腦小血管痙攣,或缺氧或藥物等毒性作用導致血管內皮損傷及血腦屏障破壞[35]。
輸血相關 PRES 可能存在較其他病因或危險因素的 PRES 獨特的發病機制。首先,本系列患者發病前合并高血壓 10 例[27.0%(10/37)]低于總體 PRES 患者合并高血壓比例(80%~85%)[36-37],提示基礎高血壓可能不是輸血相關 PRES 患者早期高灌注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認為,短期內快速輸血可在血壓正常下直接引發高灌注,損傷腦血管內皮細胞與血腦屏障,造成血管源性水腫[1,5]。其次,在本系列患者中已完善血管檢查 14 例[87.5%(14/16)]存在血管收縮或痙攣。輸血誘發腦血管痙攣的機制可能包括黏度迅速增加而引起的急性血管內皮功能障礙,以及慢性貧血引起血管持續擴張的狀態被迅速糾正[15,21]。此外,低雌激素可能是輸血相關 PRES 的促進因素,導致輸血相關 PRES 女性多見且與婦科疾病密切相關[32]。最后,有學者認為,慢性嚴重貧血狀態下,輸血介導的自身免疫可能易導致 PRES[17]。
② 臨床特征。以往研究顯示,PRES 平均年齡約 48 歲,以女性多見[38]。本系列患者平均年齡(43.16±14.68)歲,在兒童中也有發現。PRES 有 87%為白種人[39],而在本系列患者中多為亞洲女性[75.7%(28/37)],種族和基因是否與輸血相關 PRES 的發生率有關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輸血相關 PRES 系列患者貧血病程以慢性病程為主,大部分患者血紅蛋白水平增加至少 50 g/dL,提示大量、快速輸血、血液黏度快速上升是發病的關鍵。患者主要臨床表現依次為癲癇、意識障礙、頭痛、視力障礙、肢體癱瘓等,與其他病因 PRES 的常見臨床表現相似[36]。在 26 例頭痛患者中,4 例頭痛有“雷擊樣”特征,影像學顯示發病時腦血管節段性收縮及復查時血管收縮完全恢復,基本滿足“可逆性腦血管收縮綜合征”診斷標準[40-41]。
③ 影像學表現。既往報道的 PRES 典型的腦實質影像學表現為頂枕葉皮質下白質區域為主的血管源性水腫,可同時伴有額顳葉、灰質區域受累,或伴有細胞毒性水腫[1]。本系列患者也具有上述影像學表現。
PRES 腦水腫以血管源性水腫為主時 MRI 表現為 DWI 序列上呈等或稍低信號,ADC 序列呈稍高信號,出現細胞毒性水腫為主時 MRI 表現為 DWI 序列高信號、ADC 序列呈部分低信號,后者提示低灌注引起的缺血性損傷,多與嚴重的血管痙攣有關。細胞毒性水腫影像改變在本系列患者中的發生比例為 13.5%(5/37),在其他病因的 PRES 病例報道中為 11%~32.9%[36,42-43],比例基本相似。通常情況下,單純血管源性水腫病灶是可逆的,而細胞毒性水腫病灶是不完全可逆的[7]。在本系列患者中,5 例細胞毒性水腫相應部位血管均可見明顯痙攣,其中 3 例[60.0%(3/5)]患者遺留神經系統后遺癥,而僅有血管源性水腫遺留后遺癥者僅 6 例[18.8%(6/32)]。
在本系列患者中,對伴血管痙攣的 14 例患者發現,13 例患者[92.9%(13/14)]痙攣部位均包括單側或雙側大腦后動脈,包括 4 例僅累及大腦后動脈和 9 例同時累及大腦后動脈和大腦中動脈。有學者認為,血管痙攣先累及遠端小動脈,可能超出影像學所能識別范圍,因此出現腦血管痙攣的“遲發性”或“向心性”現象[15]。
④ 治療與結局。目前,尚無針對 PRES 治療的臨床試驗,臨床上以早期監測與控制血壓降低高灌注、對癥治療(脫水降顱壓)、控制并發癥如抗癲癇為主。對于輸血相關 PRES,應注意輸血量和補充速度,并在血紅蛋白升高超過 50g/L 的情況下適當補充晶體,以降低血液黏度[17]。對于伴血管痙攣的患者,尼莫地平在解除痙攣和保護內皮細胞方面可能有效[44-45]。本系列患者總體預后良好,9 例[24.3%(9/37)]報告神經系統后遺癥,其比例與其他病因 PRES 人群相似(10%~20%)[46]。輸血相關 PRES神經系統后遺癥可能與腦血管嚴重痙攣所致的廣泛細胞毒性水腫相關[7,10]。
綜上,輸血相關的 PRES 多為女性,多因嚴重貧血短期內大量輸血的誘因,臨床表現基本同其他病因的 PRES。輸血相關的 PRES 腦實質影像通常表現為血管源性水腫,部分病例可呈現細胞毒性水腫的特點,但血管影像顯示較其他原因的 PRES 更高比例的血管痙攣。輸血相關的 PRES 可能存在與其他病因 PRES 不同的發病機制,但需進一步研究證實,治療上目前無特效治療措施報告,尼莫地平等治療是否存在特異性療效需更多病例驗證。大部分輸血相關的 PRES 預后良好,但少部分病例病情可進行性加重,遺留神經功能缺損后遺癥,與腦血管痙攣的范圍、程度增加密切相關。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除需進一步關注發病機制及最佳治療方式的研究外,對于表現為 PRES 患者,應注意詢問輸血病史,做到早期病因診斷,監測腦血管痙攣的發生,及時處理,避免繼發腦缺血損傷及神經后遺癥。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病例介紹 患者,女,48 歲,因“頭暈 17 d,頭痛 7 d,雙眼視力下降 4 d”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以下簡稱“我院”)神經內科。患者既往有慢性貧血病史 10+年,未規律診治,本次病前無腹痛、黑便;否認高血壓、腎病、使用腫瘤化療藥物以及其他血管活性藥物特殊病史。2021 年 6 月 4 日患者出現頭暈,伴視物旋轉,無發熱、意識不清、肢體無力、麻木以及耳鳴等,立即于當地市級醫院住院治療,當天完善血常規提示血紅蛋白 38 g/L,次日開始 2 d 內共輸注紅細胞懸液 1 200 mL,輸血過程中收縮壓一度升高達 160 mm Hg(1 mm Hg=0.133 kPa)。輸血后患者于 6 月 7 日復查血紅蛋白為 100 g/L,頭暈緩解后回家。6 月 14 日患者出現頭痛,額部脹痛為主,伴視物模糊,無發熱,自服止痛藥后頭痛癥狀稍緩解及視物模糊減輕;6 月 17 日晨起后雙眼視力明顯下降,僅有微弱光感,伴頭部脹痛明顯,再次于當地市級醫院完善檢查(6 月 17 日):頭部 MRI 示左側枕頂葉腦回腫脹,呈長 T1、長 T2 信號,液體衰減反轉恢復(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FLAIR)序列高信號,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稍高信號,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spersion coefficient, ADC)稍低信號。予以抗血小板等急性腦梗死相關治療后,視物模糊無好轉,于當天由外院轉入我院急診科。急診血壓 190/84 mm Hg,并于當天完善相關檢查:血紅蛋白 103 g/L;頭部 CT 平掃示:顱內未見確切異常密度影;頭頸部 CT 血管造影(CT angiography, CTA)示:基底動脈遠段、右側大腦后動脈管腔不均勻中-重度狹窄,雙側椎動脈 V4 段、基底動脈纖細(圖1a);CT 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 CTP)示:雙側大腦半球灌注基本對稱,未見局限大片低灌注區。
 圖1
患者發病期間顱內血管痙攣和腦實質影像學演變
圖1
患者發病期間顱內血管痙攣和腦實質影像學演變
a. 2021 年 6 月 17 日頭頸部 CTA 結果顯示右側大腦后動脈不均勻中-重度狹窄;b. 2021 年 6 月 23 日頭部 CT 結果顯示雙側頂枕葉大片低密度影,左側頂枕葉病灶見條狀高密度影;c~f. 2021 年 6 月 24 日頭部 MRI 結果顯示雙側顳頂枕葉皮質及皮質下片狀、斑片狀 T1 低信號(c)、T2 高信號(d)、T2-FLAIR 高信號(e),雙側頂葉部分腦溝內可見少許 SWI 低信號(f);g、h. 2021 年 6 月 25 日 DSA 結果顯示右側(g)及左側(h)頸內動脈顱內段中度狹窄、右側(g)及左側(h)大腦中動脈主干彌漫重度狹窄;i. 2021 年 6 月 30 日頭部 MRI T2-FLAIR 結果顯示病變范圍較前增大;j. DWI 結果顯示右側額葉、雙側顳頂枕葉及島葉多發斑片狀高信號;k. ADC 結果顯示右側額葉、雙側顳頂枕葉相應區域部分低信號;l. 2021 年 7 月 12 日頭頸部 CTA 結果顯示右側椎動脈略纖細,雙側椎動脈、頸內動脈、頸外動脈均未見異常管腔狹窄。CTA:CT 血管造影;FLAIR:液體衰減反轉恢復;SWI:磁敏感加權成像;DAS:數字減影血管造影;ADC:表觀彌散系數
患者經急診對癥處理后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轉入我院神經內科繼續診治,入科后體格檢查:血壓 151/86 mm Hg,脈搏 61 次/min,呼吸頻率 20 次/ min,體溫 37℃。神志清,表情淡漠,反應遲鈍,雙眼無光感,無構音障礙,四肢肌力 5 級,雙側病理征陰性,腦膜刺激征陰性。6 月 22 日患者言語混亂、認知下降,迅速出現呼之不應,雙眼向右凝視,雙側瞳孔等大等圓,約 3 mm,對光反射遲鈍,左側肢體無自發活動,隨即復查血液指標,血紅蛋白 120 g/L,血糖、生化以及免疫指標大致正常。入院診斷:可逆性后部腦病綜合征(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 PRES)?6 月 22 日完善腰椎穿刺術,腦脊液初壓 120 mm H2O(1 mm H2O=0.009 81 kPa)、末壓 10 mm H2O,腦脊液常規、生化、微生物培養無明顯異常。6 月 23 日復查頭 CT 報告:雙側頂枕葉大片低密度影,其中左側頂枕葉病灶見條狀高密度影(圖1b);6 月 23 日 MRI 頭部增強掃描:雙側顳頂枕葉皮質及皮質下、左側島葉片狀、斑片狀長 T1、長 T2 信號,FLAIR 高信號(圖1c~1e),雙側頂葉部分腦溝內可見少許短 T2 信號影,磁敏感加權成像呈低信號,提示蛛網膜下腔出血(圖1f)。6 月 24 日復查頭頸部 CTA 報告:雙側大腦前動脈 A2 段局部重度狹窄,雙側大腦中動脈 M1 段管腔纖細,基底動脈遠段、右側大腦后動脈官腔不均勻中-重度狹窄,雙側椎動脈 V4 段、基底動脈纖細,即前、后循環均存在管壁不均勻狹窄,考慮顱內廣泛血管痙攣可能。6 月 24 日復查 CTP 報告:雙側額頂枕葉見異常低灌注,表現為雙側額葉、頂葉、枕葉存在腦血流流量與腦血流容量不匹配區。于 6 月 25 日行全腦血管造影(圖1g、1h):雙側頸內動脈顱內段中度狹窄、雙側大腦中動脈主干彌漫性重度狹窄;右側椎動脈外段長段輕中度狹窄,基底動脈遠端漸進性纖細,提示前后循環顱內大動脈廣泛嚴重痙攣。6 月 26 日患者能自發睜眼,不能配合檢查,有亂吐口水、打飽嗝、發出特殊聲音等精神癥狀,疼痛刺激右上肢有自發活動,右下肢有回縮,肌力可達 3 級,左側肢體無活動。6 月 30 日復查頭顱 MRI:右側額葉、雙側顳頂枕葉及島葉多發斑片狀長 T1 長 T2 信號影,FLAIR 高信號(圖1i),彌散受限(圖1j),相應區域 ADC 部分低信號(圖1k),雙側頂枕葉皮質邊緣可見短 T1 短 T2 信號,考慮雙側大腦半球以后部皮質為主梗死伴少量出血。入院 2 周后患者能進行簡單語言交流,少量口中進飲食,左側肢體偏癱好轉,肌力達 3 級,右側肢體肌力 5– 級,視力障礙無變化。住院期間予以口服阿司匹林腸溶片(100 mg、1 次/d)、口服尼莫地平(30 mg、3 次/d)、靜脈注射地塞米松(6 月 25 日—29 日,10 mg、1 次/d)、靜脈滴注甘露醇(250 mL、每 8 小時 1 次,逐漸減量至 125 mL、每 12 小時 1 次)減輕腦水腫、補液擴容、康復理療等治療。住院治療 16 d 后,患者神志清楚,言語較清晰,可進行簡單對話和動作,左側偏癱明顯緩解,四肢肌力可達 4 級,視力無變化,血壓穩定,于 2021 年 7 月 7 日出院,出院時診斷為 PRES。
2021 年 7 月 12 日(發病后 38 d),患者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上錦醫院復查頭頸部 CTA(圖1l)未見異常管腔狹窄。發病后 3 個月經電話隨訪,患者雙眼視力恢復,遺留視野缺損,近記憶力下降,時間、地點、人物定向力正常,可與人正常交流,可獨自行走,左下肢肌力 5– 級,其余肢體肌力正常,生活基本自理。發病后 1 年經電話隨訪,患者視野缺損程度同前,記憶力恢復基本如常,肌力恢復如常,可正常交流、行走。
討論 PRES 于 1996 年首次報道,主要臨床表現包括急性起病的頭痛、癲癇、視力障礙,可出現精神、意識狀態改變及偏癱等局灶性神經功能缺失體征[1]。其影像學典型改變為雙側頂枕葉病變,MRI T2-FLAIR 序列呈高信號。PRES 相關危險因素主要為高血壓、細胞毒性藥物、敗血癥、先兆子癇或子癇和多器官功能障礙[2-3],但由輸血誘發 PRES 較少見。本文報告的該例患者符合 PRES 的典型臨床特征,在發病前有短期內快速輸血史,輸血后血壓明顯增高,應考慮輸血為 PRES 的重要病因,即輸血相關 PRES。
截至目前,國內外尚未開展以輸血為主要病因的 PRES 病例的大樣本病例對照研究或隊列研究,相關報道主要局限于個案病例的形式。為明確輸血相關 PRES的特征,并為 PRES 的診治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指導,本研究小組檢索 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中國知網、維普和萬方數據庫于 2024 年前發表的有關輸血相關 PRES 病例報道。由于鐮狀細胞貧血與器官移植相關 PRES 有獨特的發病機制[4],因此合并上述疾病的輸血相關 PRES 病例報道未被納入。最終,共檢索到 30 篇輸血相關 PRES 病例報告,患者 36 例[5-34]。由此,在納入本文報告病例后,共報告輸血相關 PRES 病例 37 例。
在 37 例患者中,男性 2 例,女性 35 例;年齡 6~75 歲,平均年齡(43.16±14.68)歲;2 例男性及 28 例女性均為亞洲國家患者;貧血病程:慢性貧血 28 例(75.7%),其中在慢性貧血的基礎上急性失血 1 例(2.7%),其他急性或亞急性失血 5 例(13.5%),貧血病程不詳 4 例(10.8%);慢性貧血的病因以血液系統疾病[39.3%(11/28)]與婦科疾病[39.3%(11/28)]居多,急性或亞急性失血的病因以術后出血[60.0%(3/5)]居多;發病前合并高血壓病史 10 例(27.0%);輸血量:血色素升高 50 g/L 及以上 23 例(62.2%),血色素升高 50 g/L 以下 7 例(18.9%),輸血量不詳 7 例(18.9%);神經系統損害起病時間 1~18 d,多發生在輸血后的 1 周內;常見臨床表現:癲癇 33 例(89.2%),意識障礙 27 例(73.0%),頭痛 26 例(70.3%),頭痛有“雷擊樣”特征 4 例[15.4%(4/26)],視力障礙 13 例(35.1%),偏癱或四肢癱 6 例(16.2%),部分患者出現惡心、嘔吐、認知功能下降、精神癥狀等;頭部影像學檢查:雙側頂枕葉與額葉皮質下白質區域為病變常見部位,多呈 T2 高信號、DWI 低信號或等信號、ADC 高信號的血管源性水腫,但仍有 5 例(13.5%)存在以 DWI 高信號、ADC 低信號為特征的細胞毒性水腫,其中 4 例(10.8%)同時存在血管源性水腫及細胞毒性水腫;3 例(8.1%)伴腦實質出血,2 例(5.4%)伴蛛網膜下腔出血;行動脈血管檢查(包括磁共振血管造影、CTA、數字減影血管造影等)16 例(43.2%),其中血管痙攣 14 例[87.5%(14/16)],包括同時累及大腦后動脈和大腦中動脈 9 例、僅累及大腦后動脈 4 例、僅累及大腦前動脈 1 例;預后大多良好,28 例(75.7%)未遺留任何癥狀,9 例(24.3%)遺留視力障礙、意識障礙等癥狀。
上述病案報道的匯總結果(以下簡稱本系列患者)提示,輸血相關 PRES 在流行病學特征、合并癥、血管痙攣以及顱內水腫等方面呈現出一定特點,且其臨床癥狀與預后與輸血情況密切相關。盡管目前缺乏大型臨床研究的報道,但國內外學者已初步對輸血相關 PRES 的發病機制、臨床特征、影像學表現、治療與結局進行了探索。
① 發病機制。PRES具體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既往報道中以腦高灌注學說最常見,即快速進展的高血壓超出腦血流自動調節上限,腦灌注增加,血腦屏障破壞,液體外滲導致血管源性腦水腫;其他學說包括腦小血管痙攣,或缺氧或藥物等毒性作用導致血管內皮損傷及血腦屏障破壞[35]。
輸血相關 PRES 可能存在較其他病因或危險因素的 PRES 獨特的發病機制。首先,本系列患者發病前合并高血壓 10 例[27.0%(10/37)]低于總體 PRES 患者合并高血壓比例(80%~85%)[36-37],提示基礎高血壓可能不是輸血相關 PRES 患者早期高灌注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認為,短期內快速輸血可在血壓正常下直接引發高灌注,損傷腦血管內皮細胞與血腦屏障,造成血管源性水腫[1,5]。其次,在本系列患者中已完善血管檢查 14 例[87.5%(14/16)]存在血管收縮或痙攣。輸血誘發腦血管痙攣的機制可能包括黏度迅速增加而引起的急性血管內皮功能障礙,以及慢性貧血引起血管持續擴張的狀態被迅速糾正[15,21]。此外,低雌激素可能是輸血相關 PRES 的促進因素,導致輸血相關 PRES 女性多見且與婦科疾病密切相關[32]。最后,有學者認為,慢性嚴重貧血狀態下,輸血介導的自身免疫可能易導致 PRES[17]。
② 臨床特征。以往研究顯示,PRES 平均年齡約 48 歲,以女性多見[38]。本系列患者平均年齡(43.16±14.68)歲,在兒童中也有發現。PRES 有 87%為白種人[39],而在本系列患者中多為亞洲女性[75.7%(28/37)],種族和基因是否與輸血相關 PRES 的發生率有關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輸血相關 PRES 系列患者貧血病程以慢性病程為主,大部分患者血紅蛋白水平增加至少 50 g/dL,提示大量、快速輸血、血液黏度快速上升是發病的關鍵。患者主要臨床表現依次為癲癇、意識障礙、頭痛、視力障礙、肢體癱瘓等,與其他病因 PRES 的常見臨床表現相似[36]。在 26 例頭痛患者中,4 例頭痛有“雷擊樣”特征,影像學顯示發病時腦血管節段性收縮及復查時血管收縮完全恢復,基本滿足“可逆性腦血管收縮綜合征”診斷標準[40-41]。
③ 影像學表現。既往報道的 PRES 典型的腦實質影像學表現為頂枕葉皮質下白質區域為主的血管源性水腫,可同時伴有額顳葉、灰質區域受累,或伴有細胞毒性水腫[1]。本系列患者也具有上述影像學表現。
PRES 腦水腫以血管源性水腫為主時 MRI 表現為 DWI 序列上呈等或稍低信號,ADC 序列呈稍高信號,出現細胞毒性水腫為主時 MRI 表現為 DWI 序列高信號、ADC 序列呈部分低信號,后者提示低灌注引起的缺血性損傷,多與嚴重的血管痙攣有關。細胞毒性水腫影像改變在本系列患者中的發生比例為 13.5%(5/37),在其他病因的 PRES 病例報道中為 11%~32.9%[36,42-43],比例基本相似。通常情況下,單純血管源性水腫病灶是可逆的,而細胞毒性水腫病灶是不完全可逆的[7]。在本系列患者中,5 例細胞毒性水腫相應部位血管均可見明顯痙攣,其中 3 例[60.0%(3/5)]患者遺留神經系統后遺癥,而僅有血管源性水腫遺留后遺癥者僅 6 例[18.8%(6/32)]。
在本系列患者中,對伴血管痙攣的 14 例患者發現,13 例患者[92.9%(13/14)]痙攣部位均包括單側或雙側大腦后動脈,包括 4 例僅累及大腦后動脈和 9 例同時累及大腦后動脈和大腦中動脈。有學者認為,血管痙攣先累及遠端小動脈,可能超出影像學所能識別范圍,因此出現腦血管痙攣的“遲發性”或“向心性”現象[15]。
④ 治療與結局。目前,尚無針對 PRES 治療的臨床試驗,臨床上以早期監測與控制血壓降低高灌注、對癥治療(脫水降顱壓)、控制并發癥如抗癲癇為主。對于輸血相關 PRES,應注意輸血量和補充速度,并在血紅蛋白升高超過 50g/L 的情況下適當補充晶體,以降低血液黏度[17]。對于伴血管痙攣的患者,尼莫地平在解除痙攣和保護內皮細胞方面可能有效[44-45]。本系列患者總體預后良好,9 例[24.3%(9/37)]報告神經系統后遺癥,其比例與其他病因 PRES 人群相似(10%~20%)[46]。輸血相關 PRES神經系統后遺癥可能與腦血管嚴重痙攣所致的廣泛細胞毒性水腫相關[7,10]。
綜上,輸血相關的 PRES 多為女性,多因嚴重貧血短期內大量輸血的誘因,臨床表現基本同其他病因的 PRES。輸血相關的 PRES 腦實質影像通常表現為血管源性水腫,部分病例可呈現細胞毒性水腫的特點,但血管影像顯示較其他原因的 PRES 更高比例的血管痙攣。輸血相關的 PRES 可能存在與其他病因 PRES 不同的發病機制,但需進一步研究證實,治療上目前無特效治療措施報告,尼莫地平等治療是否存在特異性療效需更多病例驗證。大部分輸血相關的 PRES 預后良好,但少部分病例病情可進行性加重,遺留神經功能缺損后遺癥,與腦血管痙攣的范圍、程度增加密切相關。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除需進一步關注發病機制及最佳治療方式的研究外,對于表現為 PRES 患者,應注意詢問輸血病史,做到早期病因診斷,監測腦血管痙攣的發生,及時處理,避免繼發腦缺血損傷及神經后遺癥。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