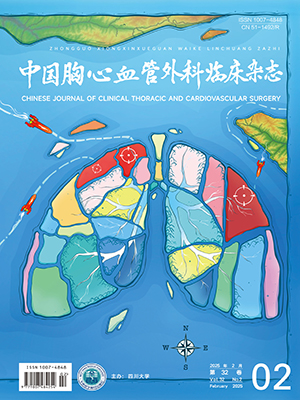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單純手術后容易復發及轉移,術前新輔助化療及術后輔助化療雖能使患者獲益,但5年生存率提升不明顯。近年來隨著免疫治療的興起,NSCLC免疫治療也逐漸受到重視,學者對可切除NSCLC的免疫治療也進行了很多探索,并且獲得了可喜的結果。多個3期研究結果的公布正式開啟了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新篇章。然而,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本文就目前相關研究進行綜述,為臨床應用提供參考。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肺癌是全球導致患者死亡最多的癌癥之一,其中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約占80%~85%[1]。手術是可切除NSCLC的核心治療手段,但單純手術后容易出現局部復發及遠處轉移,5年生存率低,僅約20%~50%[2]。以手術為核心的綜合治療已成為局部晚期NSCLC的標準治療模式,包括術前新輔助治療及術后輔助治療,而以化療為核心的輔助治療最為重要[3-4]。既往研究[3-4]表明,術前新輔助化療及術后輔助化療雖然能使患者獲益,但5年生存率提高并不明顯,僅約5%,仍有較多患者出現復發及遠處轉移。因此,尋找一種新的輔助治療手段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隨著免疫治療在多個癌種的治療中取得突破性進展,免疫治療在肺癌治療中的應用也逐漸受到重視。隨著多個研究[5-7]數據的披露,目前免疫治療已成為晚期和復發NSCLC的一線治療手段。而新輔助免疫治療在NSCLC中的應用研究也在多個中心開展,并取得了可喜的前期成果,同時得到了胸外科專家的認可。以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CheckMate816[8]、KEYNOTE-671[9]研究及術后輔助免疫治療KEYNOTE-091[10]、IMpower010[11]研究為代表的Ⅲ期臨床研究結果的披露,掀開了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的新篇章。本文綜述國內外相關研究,為臨床應用提供參考。
1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
術前新輔助治療已經成為多個局部晚期癌種的標準治療模式。術前使用免疫治療,能夠更早地激活人體免疫系統,持續消滅腫瘤,使患者獲益[12]。目前可切除NSCLC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模式多種多樣,包括免疫單藥、雙免疫等(主要研究[13-20]見表1),均獲得了可喜的結果,但不同模式在療效及副反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1.1 免疫單藥
CheckMate159研究[13-14]開創了NSCLC新輔助免疫治療的探索,結果顯示:治療過程中無4級或5級不良反應,所有患者治療后手術均按計劃進行,R0切除率約95%(20/21),術后患者的主要病理緩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率為45%(9例),病理學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率為15%(3例),均高于文獻[21]報道的接受新輔助化療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總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分別為60%和80%,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陽性及術后MPR患者有更好的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術前使用nivolumab單藥新輔助免疫治療的研究顯示,術后患者的MPR率為24%,pCR率為10%,未出現因不良事件停藥情況[15]。Gao等[16]的研究表明,新輔助免疫治療后92.5%的患者接受了手術(37/40),MPR率為40.5%(15/37),pCR率為16.2%(6/37);術后3年隨訪結果顯示,3年OS率為88.5%,3年無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率為75.0%,并且PD-L1陽性患者的3年OS及DFS率更高,分別為95.5%和81.8%[17]。LCMC3研究[18-19]是迄今為止最大的術前免疫單藥治療NSCLC的研究,共納入181例患者(ⅠB~ⅢB期),治療完成率約94%(171/181),未觀察到新的不良事件;88%(159/181)的患者行手術治療,R0切除率約91%(145/159);143例EGFR/ALK基因突變陰性患者中,MPR率為20%(30/147),95%CI(14%,28%),pCR率為7%(10/147),95%CI(3%,12%),MPR率與新輔助化療相當[21]。從既往研究來看,可切除NSCLC單藥新輔助免疫治療MPR率約20%~45%,pCR率約7%~15%,與文獻[21]報道的新輔助化療效果相當,并且副反應少,患者長期生存能夠獲益。然而,LCMC3研究顯示,影像學評價腫瘤緩解僅約6%(11/181),有7%(13/181)的患者出現影像學進展,81%的患者(147/181)病情穩定,從影像學角度來看,此方案并未明顯使腫瘤降期,而本研究之所以有91%的R0切除率,可能與入組患者多為Ⅰ、Ⅱ期患者有關。因此,從目前的證據來看,單藥新輔助免疫治療可能是化療不能耐受患者的一種較好的替代治療手段,而在邊緣可切除NSCLC中的應用需慎重。
1.2 免疫雙藥
除了單藥免疫治療外,也有臨床試驗探索雙藥新輔助免疫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一項2期臨床研究(NEOSTAR)[15]納入了44例Ⅰ~Ⅲ期可切除NSCLC患者,其中A組23例隨機接受nivolumab單藥治療,B組21例隨機接受nivolumab+ipilimumab治療,治療完成率分別為96%、90%,B組MPR率及PCR率均高于A組(38% vs. 22%,29% vs. 9%)。Reuss等[20]的研究顯示,nivolumab聯合ipilimumab雙藥新輔助治療后達到pCR的患者長期生存能明顯獲益;然而,由于15例患者中有9例出現嚴重毒性反應,治療方案不得不提前終止。因此,雖然雙藥新輔助免疫治療相比單藥能夠獲得更好的療效,但是雙藥副作用更大,嚴重的副反應可能導致手術延遲甚至患者死亡。雙藥免疫治療還需要更多隨機對照研究進行探索,篩選合適人群,優化方案。
2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化療
化療目前仍然是可切除NSCLC術前新輔助治療的核心治療手段[22]。有研究[23-25]表明,化療可提高腫瘤對免疫治療的敏感性。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率先在晚期NSCLC治療中取得突破性進展[26-28]。研究者[8,29-31]開啟了術前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探索;見表2。NADIM研究[29]率先報道了可切除NSCLC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療效,術后患者的MPR率達到83%,pCR率達到63%。一項單臂Ⅱ期研究[31]顯示,使用2~3周期術前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疾病控制率為90%,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為70%,術后MPR率和pCR率分別為62.5%和31.25%。一項回顧性研究[32]對比了術前接受新輔助化療或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NSCLC患者的療效,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的ORR及病理緩解率均高于化療組(70.9% vs. 47.3%,53.2% vs. 14.3%);中位隨訪17.0個月,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患者有更好的DFS[(13.28±6.34)個月vs.(12.60±7.13)個月]。一項隊列研究[33]顯示,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相比化療,有更高的MPR率(78.95% vs. 10.26%,P<0.001)及pCR率(57.89% vs. 5.13%,P<0.001),并且OS及DFS均明顯改善。Fei等[34]的研究顯示,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與化療組具有相似的安全性,沒有增加手術難度,術后MPR率、pCR率明顯高于化療組(76.2% vs. 11.9%、50.0% vs. 4.7%)。在CheckMate 816研究[8]中,新輔助nivolumab+化療較化療有更高的ORR和pCR率(30.7% vs. 23.5%,24% vs. 2.2%),具有相似的3/4級治療相關不良反應發生率(33.5% vs. 36.9%);3年隨訪數據顯示,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較化療持續改善無病生存率[無事件生存率(event-free survival,EFS)57% vs. 43%],3年OS改善14%(78% vs. 64%);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術后復發比例更低(28% vs. 42%),腦轉移更少,直接和間接改善生活質量,并且僅在未達到pCR的患者中出現腦轉移復發。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相比化療,具有相似的安全性,并且有更好的療效。但是在臨床應用過程中,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適合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真實世界中,采用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更多的仍然是鱗狀細胞癌(鱗癌)患者,而對于腺癌患者,特別是驅動基因陽性患者,免疫治療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對于這類患者術前新輔助靶向治療也已經在多個研究中開展,免疫治療與靶向治療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并且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周期數對手術及預后的影響也未知,現有臨床應用及相關前瞻性研究中,更多的是采用2~4周期化療加免疫治療方案,在治療過程中,何時手術仍然存在較大爭議,免疫治療周期太短可能達不到預期療效,過長是否會出現因手術延遲導致疾病進展,也未知。總之,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相比單純化療更能使患者獲益,基于CheckMate 816研究3年隨訪數據,該治療方案適應證已經在美國、中國等國家獲批。然而,基于現有臨床問題,此方案仍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進一步探索與完善。
3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其他治療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其他治療包括聯合放化療、抗血管生成治療等。
3.1 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
新輔助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是治療早期NSCLC的一種有前途的策略,因為放療會產生免疫治療的抗腫瘤作用,導致遠離原發放射部位的非放射轉移瘤消退。其抽象作用被認為是一種可能由免疫治療刺激的系統性抗腫瘤免疫反應[35-36]。MEDI4736研究[37]顯示,對于不可切除晚期NSCLC,放化療后序貫接受Durvalumab免疫維持治療,能夠顯著改善PFS及OS(PFS:17.2個月vs. 5.6個月;24個月OS率:66.3% vs. 55.6%,雙側P=0.005)。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可減少局部復發和轉移,增強整體全身治療效果。目前新輔助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相關前瞻性研究尚在進行中[38],INCREASE試驗[39]計劃招募29例可切除或臨界可切除T3~4N0~1 NSCLC患者,探索在術前放化療中添加 IPI/NIVO 的安全性及其對病理腫瘤反應的影響,同時評估對DFS率和OS率的影響。目前研究已于2020 年 2 月開始,尚在進行中,此方案具體療效還需等待后續數據證實。
3.2 免疫治療聯合抗血管生成治療
有研究[40]表明,腫瘤血管生成可促進免疫抑制,從而導致腫瘤對免疫治療耐藥。抗血管生成治療可使腫瘤血管正常化,從而增強免疫治療療效[41]。研究人員首先在晚期NSCLC中探索了免疫聯合抗血管生成治療的協同作用。IMpower150研究[42]納入1202例化療初治的轉移性NSCLC患者,隨機分配(1∶1∶1),每3周接受ACP(atezolizumab聯合卡鉑和紫杉醇)、BCP(bevacizumab聯合卡鉑和紫杉醇)或ABCP(atezolizumab+BCP)治療,結果顯示,ABCP方案可改善EGFR陽性患者的PFS。Lam等[43]的研究顯示,對于晚期既往接受靶向治療后進展的NSCLC患者使用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和抗血管生成治療(atezolizumab+bevacizumab+培美曲塞+卡鉑),具有與IMpower150研究類似的ORR(為62.5%),中位PFS為9.4個月,95%CI(56%,83%),并且毒性得到了改善。因此,有研究開始探索免疫聯合抗血管生成治療在可切除NSCLC的治療療效及安全性,目前此研究尚在進行中,結果尚未披露。從晚期治療的效果來看,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和抗血管生成治療,可能是可切除NSCLC術前新輔助治療的一種很有前景的治療手段,特別是對于EGFR基因/ALK基因陽性患者,此聯合治療可能會帶來更多希望。
4 術后輔助免疫治療
NSCLC單純手術后容易復發,術后輔助化療可以降低復發風險,但效果并不明顯,5年生存率改善僅約5%[4],對于單獨手術后NSCLC,尋找一種更好的術后輔助治療手段顯得尤為重要。隨著ADAURA研究[44]長期生存結果的公布,術后輔助靶向治療已成為EGFR基因突變陽性NSCLC的標準治療手段。然而NSCLC術后還有很大部分是EGFR基因野生型患者,這類患者的術后輔助治療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在多個癌種中獲得可喜的生存獲益[45]。因此,也有研究[10-11]對NSCLC術后輔助免疫治療進行了探索;見表3。目前最重要的2個研究是KEYNOTE-091及IMpower010研究。IMpower010研究[11]顯示:對于PD-L1 TC≥1%Ⅱ~ⅢA期人群,atezolizumab組的中位DFS明顯優于對照組(NE vs. 35.3個月),顯著降低了復發或死亡風險,HR=0.66(P=0.004)。2年后atezolizumab組的DFS率為74.6%,高于對照組的61.0%;3年后兩組的DFS率分別降至60.0%和48.2%,并且未見新的治療相關不良事件發生。KEYNOTE-091研究[10]顯示,pembrolizumab組和安慰劑組的中位DFS分別為58.7個月(39.2個月~NR)和34.9個月(28.6個月~NR)(HR=0.73)。其中,在PD-L1 TPS≥50%患者中,pembrolizumab組(n=143)和安慰劑組(n=141)的中位DFS均未達到(HR=0.80)。兩組中3~5級不良事件發生率分別為34.3%和25.7%。基于KEYNOTE-091研究,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準了pembrolizumab輔助治療適應證,用于ⅠB期(T2a≥4 cm)、Ⅱ期或ⅢA期NSCLC患者切除和輔助含鉑化療后的輔助治療。
5 圍術期免疫治療(術前新輔助聯合術后輔助治療)
既往研究表明,無論是術前新輔助還是術后輔助免疫治療都能使患者獲益。從圍術期治療來看,新輔助免疫治療和輔助免疫治療的全程應用是否可行,是否會進一步改善患者預后,成為目前臨床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目前研究的熱點;見表4。在2023年美國ASCO會議上,多個Ⅲ期研究公布了圍術期免疫治療的研究結果。AEGEAN研究[46]是首個公布結果的“新輔助免疫治療+手術+輔助免疫治療”模式的Ⅲ期研究,評估無EGFR及ALK突變的可切除ⅡA~ⅢB(N2)期NSCLC患者使用Durvalumab進行“新輔助免疫治療+手術切除+術后輔助免疫治療”方案的療效與安全性,研究結果顯示,試驗組明顯提高了MPR及pCR率(33.3% vs. 12.3%,17.2% vs. 4.3%);并未發現有統計學差異的不良事件發生。中位隨訪11.7個月后發現,試驗組和對照組的中位EFS分別為NR和25.9個月[HR=0.68,95%CI(0.53,0.88),P=0.0039];并且EFS獲益并不受PD-L1表達情況及化療方案的影響。由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牽頭的Neotorch研究[47]是全球首個抗PD-1單抗用于NSCLC圍手術期治療達到主要終點的Ⅲ期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與單純化療相比,toripalimab聯合化療用于Ⅲ期可手術NSCLC患者圍手術期治療并在后續進行toripalimab單藥鞏固治療,可顯著延長患者EFS(研究者評估的中位EFS分別為未達到 vs. 15.1個月,P<0.0001),疾病復發、進展或死亡風險降低達60%[HR=0.40,95%CI(0.277,0.565),P<0.0001]。兩組的1年EFS率和2年EFS率分別為84.4% vs. 57.0%和64.7% vs. 38.7%。toripalimab聯合化療組的MPR率和pCR率均優于單純化療組,分別為48.5% vs. 8.4%(P<0.0001)和24.8% vs. 1.0%(P<0.0001)。toripalimab聯合化療組的OS也顯示出明顯的獲益趨勢。兩組中位OS分別為未成熟vs. 30.4個月[HR=0.62,95%CI(0.381,0.999)];1年OS率和2年OS率分別為94.4% vs. 89.6%和81.2% vs. 74.3%。在安全性方面,兩組患者無明顯差異。KEYNOTE-671研究[9]是首個以OS為主要研究終點的隨機、雙盲Ⅲ期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與安慰劑組相比,pembrolizumab組患者的疾病進展、疾病復發或死亡危險降低了42%(HR=0.58,P<0.001)。pembrolizumab組的MPR率是安慰劑組的近3倍(30.2% vs. 11.0%),pCR率是安慰劑組的4倍多(18.1% vs. 4.0%);在安全性方面,治療相關不良事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研究團隊比較了KEYNOTE-671與CheckMate 816的試驗數據。CheckMate 816研究中,沒有達到pCR的患者疾病進展、疾病復發或死亡的HR=0.84,而在KEYNOTE-671研究(新輔助免疫+輔助免疫治療)中HR=0.69。雖然這種比較不夠嚴謹,但也暗示了在新輔助免疫治療后使用輔助免疫治療或許能進一步提升治療效果。
6 敏感人群篩選
從以上研究可知,免疫治療為可切除NSCLC帶來了新的希望,然而,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從免疫治療中獲益,甚至部分患者因為免疫治療導致手術延遲、疾病進展,最終導致對患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因此,篩選出對免疫治療敏感的人群,進行個體化治療顯得更為重要。目前有很多研究探索了NSCLC患者對免疫治療敏感的生物標志物,其中以PD-L1、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及循環腫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最為重要。
PD-L1是一種在腫瘤細胞上表達的共調節分子,可抑制T細胞介導的細胞死亡。在PD-L1存在的情況下,T細胞的活性被抑制。免疫治療抑制PD-1與PD-L1的相互作用,從而提高內源性T細胞的抗腫瘤活性。多個晚期NSCLC免疫治療相關研究[6,48]顯示,PD-L1表達陽性及表達程度與患者免疫治療的療效直接相關。因此,FDA已經批準PD-L1的表達用于預測晚期NSCLC免疫治療療效的生物標志物。然而,PD-L1狀態是否可以作為NSCLC新輔助免疫治療的預測因素仍在討論中,不同研究得出不同結論,甚至有相反的結論。NEOSTAR研究[15]顯示,PD-L1的表達和表達程度與治療后更大的病理反應和更少的殘留腫瘤細胞相關,然而,在PD-L1陰性患者中也觀察到了病理反應,并且沒有發現治療后腫瘤PD-L1表達和反應之間的關聯。Checkmate-159研究[13]顯示,PD-L1的表達與治療后病理反應無關。CheckMate 816研究[8]亞組分析發現,PD-L1陽性患者更能從新輔助nivolumab+化療中獲益。AEGEAN研究[46]提示,PD-L1高表達(TC≥50%)在EFS和pCR上都表現出更優的獲益。Neotorch研究[47]顯示,無論PD-L1≥1%還是PD-L1<1%,新輔助toripalimab+化療較化療均改善EFS,但是PD-L1 1%~49%及PD-L1≥50% 的療效未知。KEYNOTE-671研究[9]顯示無論PD-L1表達情況如何均可從圍術期免疫治療中獲益。IMpower010研究[11]延長了PD-L1 TC≥1%患者的OS[HR=0.71,95%CI(0.49,1.03)],其中PD-L1 TC≥50%人群OS改善更為突出。而KEYNOTE-091研究[10]卻顯示,術后輔助免疫治療無論PD-L1是否表達都能獲益,而PDL-1 TC≥50%的患者卻是陰性結果,結果似乎相互矛盾,作者解釋這可能與安慰劑的超常發揮相關。綜上所述,從目前證據來看,PD-L1表達情況只能作為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的一種預測手段,而不能成為絕對指標。
TMB作為腫瘤組織的一種遺傳特征,正在成為免疫治療反應的潛在預測生物標志物。在晚期轉移性NSCLC中,TMB作為一種預測分子標記物的價值目前尚存在爭議[49]。理論上,更高的TMB可觸發免疫治療更好的反應,這已經在一些研究[50-51]中得以證實。盡管美國FDA在2020年批準pembrolizumab用于TMB高實體腫瘤,包括不可切除的NSCLC,但TMB在新輔助免疫治療中的應用仍有很多爭議[52]。在KEYNOTE-021、189、407研究[53]中發現,TMB與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療效無關,并且在LCMC3、NEOSTAR和NADIM試驗[15,18,30]中也觀察到了同樣的結果,Checkmate-159研究[13]發現TMB與MPR率呈負相關。而CheckMate 816研究[8]發現無論TMB值如何,pCR率均可獲益。
ctDNA被認為與晚期NSCLC的復發和預后密切相關[54]。ctDNA在新輔助免疫治療中的預測價值也在一些研究中進行了探索。CheckMate 816研究[8]收集入組患者的血液標本,進行了3個療程的ctDNA檢測。結果顯示,新輔助nivolumab+化療和化療治療組的ctDNA清除率分別為56%和34%。進一步研究發現ctDNA清除組的pCR率高于未清除組(nivolumab+化療組為46% vs. 24%,化療組為13% vs. 2.2%)。NADIM研究[30]發現了類似的結果。LCMC3研究[18]表明ctDNA可能是更好的病理反應和更長生存期的預測因子。因此,納入ctDNA評估可能有助于篩選出新輔助免疫治療敏感人群,從而避免昂貴和潛在毒性的輔助治療。
7 總結與展望
隨著Ⅲ期臨床研究結果的陸續公布,可切除NSCLC輔助治療正式進入免疫時代。免疫治療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1)單純新輔助免疫治療;(2)單純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化療;(3)單純術后輔助免疫治療;(4)“夾心餅”模式,即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術后輔助免疫治療。目前,模式1的應用還有較大爭議,還需大樣本隨機對照研究進一步證實,模式2及模式3均基于Ⅲ期研究結果得以獲批相應的適應證,而模式4的探討仍在進行中,還有多個Ⅲ期研究尚未達到研究終點。
整體來說,圍術期免疫治療相比化療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免疫治療既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挑戰,同時也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比如不同分期患者的治療選擇,雖然目前的研究納入的對象大多都包括ⅠB~ⅢA期,但是入組患者更多的還是Ⅲ期患者,與真實臨床應用基本吻合,對于ⅠB期患者臨床更多采用的還是直接手術,術前新輔助免疫在這類患者中是否能夠獲益還需進一步探索。因此,更加精準的敏感人群篩選顯得尤為重要,而最佳的治療模式及手術時機的選擇也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予以證實。隨著相關研究的進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也將不斷優化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的格局。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毫負責研究設計,論文撰寫;張程誠、張躍、張力文參與選題及設計;付茂勇負責總體設計與審校。
肺癌是全球導致患者死亡最多的癌癥之一,其中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約占80%~85%[1]。手術是可切除NSCLC的核心治療手段,但單純手術后容易出現局部復發及遠處轉移,5年生存率低,僅約20%~50%[2]。以手術為核心的綜合治療已成為局部晚期NSCLC的標準治療模式,包括術前新輔助治療及術后輔助治療,而以化療為核心的輔助治療最為重要[3-4]。既往研究[3-4]表明,術前新輔助化療及術后輔助化療雖然能使患者獲益,但5年生存率提高并不明顯,僅約5%,仍有較多患者出現復發及遠處轉移。因此,尋找一種新的輔助治療手段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隨著免疫治療在多個癌種的治療中取得突破性進展,免疫治療在肺癌治療中的應用也逐漸受到重視。隨著多個研究[5-7]數據的披露,目前免疫治療已成為晚期和復發NSCLC的一線治療手段。而新輔助免疫治療在NSCLC中的應用研究也在多個中心開展,并取得了可喜的前期成果,同時得到了胸外科專家的認可。以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CheckMate816[8]、KEYNOTE-671[9]研究及術后輔助免疫治療KEYNOTE-091[10]、IMpower010[11]研究為代表的Ⅲ期臨床研究結果的披露,掀開了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的新篇章。本文綜述國內外相關研究,為臨床應用提供參考。
1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
術前新輔助治療已經成為多個局部晚期癌種的標準治療模式。術前使用免疫治療,能夠更早地激活人體免疫系統,持續消滅腫瘤,使患者獲益[12]。目前可切除NSCLC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模式多種多樣,包括免疫單藥、雙免疫等(主要研究[13-20]見表1),均獲得了可喜的結果,但不同模式在療效及副反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1.1 免疫單藥
CheckMate159研究[13-14]開創了NSCLC新輔助免疫治療的探索,結果顯示:治療過程中無4級或5級不良反應,所有患者治療后手術均按計劃進行,R0切除率約95%(20/21),術后患者的主要病理緩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率為45%(9例),病理學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率為15%(3例),均高于文獻[21]報道的接受新輔助化療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和總生存(overall survival,OS)率分別為60%和80%,程序性死亡受體配體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陽性及術后MPR患者有更好的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術前使用nivolumab單藥新輔助免疫治療的研究顯示,術后患者的MPR率為24%,pCR率為10%,未出現因不良事件停藥情況[15]。Gao等[16]的研究表明,新輔助免疫治療后92.5%的患者接受了手術(37/40),MPR率為40.5%(15/37),pCR率為16.2%(6/37);術后3年隨訪結果顯示,3年OS率為88.5%,3年無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率為75.0%,并且PD-L1陽性患者的3年OS及DFS率更高,分別為95.5%和81.8%[17]。LCMC3研究[18-19]是迄今為止最大的術前免疫單藥治療NSCLC的研究,共納入181例患者(ⅠB~ⅢB期),治療完成率約94%(171/181),未觀察到新的不良事件;88%(159/181)的患者行手術治療,R0切除率約91%(145/159);143例EGFR/ALK基因突變陰性患者中,MPR率為20%(30/147),95%CI(14%,28%),pCR率為7%(10/147),95%CI(3%,12%),MPR率與新輔助化療相當[21]。從既往研究來看,可切除NSCLC單藥新輔助免疫治療MPR率約20%~45%,pCR率約7%~15%,與文獻[21]報道的新輔助化療效果相當,并且副反應少,患者長期生存能夠獲益。然而,LCMC3研究顯示,影像學評價腫瘤緩解僅約6%(11/181),有7%(13/181)的患者出現影像學進展,81%的患者(147/181)病情穩定,從影像學角度來看,此方案并未明顯使腫瘤降期,而本研究之所以有91%的R0切除率,可能與入組患者多為Ⅰ、Ⅱ期患者有關。因此,從目前的證據來看,單藥新輔助免疫治療可能是化療不能耐受患者的一種較好的替代治療手段,而在邊緣可切除NSCLC中的應用需慎重。
1.2 免疫雙藥
除了單藥免疫治療外,也有臨床試驗探索雙藥新輔助免疫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一項2期臨床研究(NEOSTAR)[15]納入了44例Ⅰ~Ⅲ期可切除NSCLC患者,其中A組23例隨機接受nivolumab單藥治療,B組21例隨機接受nivolumab+ipilimumab治療,治療完成率分別為96%、90%,B組MPR率及PCR率均高于A組(38% vs. 22%,29% vs. 9%)。Reuss等[20]的研究顯示,nivolumab聯合ipilimumab雙藥新輔助治療后達到pCR的患者長期生存能明顯獲益;然而,由于15例患者中有9例出現嚴重毒性反應,治療方案不得不提前終止。因此,雖然雙藥新輔助免疫治療相比單藥能夠獲得更好的療效,但是雙藥副作用更大,嚴重的副反應可能導致手術延遲甚至患者死亡。雙藥免疫治療還需要更多隨機對照研究進行探索,篩選合適人群,優化方案。
2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化療
化療目前仍然是可切除NSCLC術前新輔助治療的核心治療手段[22]。有研究[23-25]表明,化療可提高腫瘤對免疫治療的敏感性。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率先在晚期NSCLC治療中取得突破性進展[26-28]。研究者[8,29-31]開啟了術前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探索;見表2。NADIM研究[29]率先報道了可切除NSCLC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療效,術后患者的MPR率達到83%,pCR率達到63%。一項單臂Ⅱ期研究[31]顯示,使用2~3周期術前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疾病控制率為90%,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為70%,術后MPR率和pCR率分別為62.5%和31.25%。一項回顧性研究[32]對比了術前接受新輔助化療或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NSCLC患者的療效,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的ORR及病理緩解率均高于化療組(70.9% vs. 47.3%,53.2% vs. 14.3%);中位隨訪17.0個月,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患者有更好的DFS[(13.28±6.34)個月vs.(12.60±7.13)個月]。一項隊列研究[33]顯示,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相比化療,有更高的MPR率(78.95% vs. 10.26%,P<0.001)及pCR率(57.89% vs. 5.13%,P<0.001),并且OS及DFS均明顯改善。Fei等[34]的研究顯示,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與化療組具有相似的安全性,沒有增加手術難度,術后MPR率、pCR率明顯高于化療組(76.2% vs. 11.9%、50.0% vs. 4.7%)。在CheckMate 816研究[8]中,新輔助nivolumab+化療較化療有更高的ORR和pCR率(30.7% vs. 23.5%,24% vs. 2.2%),具有相似的3/4級治療相關不良反應發生率(33.5% vs. 36.9%);3年隨訪數據顯示,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較化療持續改善無病生存率[無事件生存率(event-free survival,EFS)57% vs. 43%],3年OS改善14%(78% vs. 64%);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組術后復發比例更低(28% vs. 42%),腦轉移更少,直接和間接改善生活質量,并且僅在未達到pCR的患者中出現腦轉移復發。
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相比化療,具有相似的安全性,并且有更好的療效。但是在臨床應用過程中,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適合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真實世界中,采用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更多的仍然是鱗狀細胞癌(鱗癌)患者,而對于腺癌患者,特別是驅動基因陽性患者,免疫治療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對于這類患者術前新輔助靶向治療也已經在多個研究中開展,免疫治療與靶向治療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并且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周期數對手術及預后的影響也未知,現有臨床應用及相關前瞻性研究中,更多的是采用2~4周期化療加免疫治療方案,在治療過程中,何時手術仍然存在較大爭議,免疫治療周期太短可能達不到預期療效,過長是否會出現因手術延遲導致疾病進展,也未知。總之,新輔助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相比單純化療更能使患者獲益,基于CheckMate 816研究3年隨訪數據,該治療方案適應證已經在美國、中國等國家獲批。然而,基于現有臨床問題,此方案仍需要更多前瞻性研究來進一步探索與完善。
3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其他治療
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其他治療包括聯合放化療、抗血管生成治療等。
3.1 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
新輔助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是治療早期NSCLC的一種有前途的策略,因為放療會產生免疫治療的抗腫瘤作用,導致遠離原發放射部位的非放射轉移瘤消退。其抽象作用被認為是一種可能由免疫治療刺激的系統性抗腫瘤免疫反應[35-36]。MEDI4736研究[37]顯示,對于不可切除晚期NSCLC,放化療后序貫接受Durvalumab免疫維持治療,能夠顯著改善PFS及OS(PFS:17.2個月vs. 5.6個月;24個月OS率:66.3% vs. 55.6%,雙側P=0.005)。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可減少局部復發和轉移,增強整體全身治療效果。目前新輔助放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相關前瞻性研究尚在進行中[38],INCREASE試驗[39]計劃招募29例可切除或臨界可切除T3~4N0~1 NSCLC患者,探索在術前放化療中添加 IPI/NIVO 的安全性及其對病理腫瘤反應的影響,同時評估對DFS率和OS率的影響。目前研究已于2020 年 2 月開始,尚在進行中,此方案具體療效還需等待后續數據證實。
3.2 免疫治療聯合抗血管生成治療
有研究[40]表明,腫瘤血管生成可促進免疫抑制,從而導致腫瘤對免疫治療耐藥。抗血管生成治療可使腫瘤血管正常化,從而增強免疫治療療效[41]。研究人員首先在晚期NSCLC中探索了免疫聯合抗血管生成治療的協同作用。IMpower150研究[42]納入1202例化療初治的轉移性NSCLC患者,隨機分配(1∶1∶1),每3周接受ACP(atezolizumab聯合卡鉑和紫杉醇)、BCP(bevacizumab聯合卡鉑和紫杉醇)或ABCP(atezolizumab+BCP)治療,結果顯示,ABCP方案可改善EGFR陽性患者的PFS。Lam等[43]的研究顯示,對于晚期既往接受靶向治療后進展的NSCLC患者使用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和抗血管生成治療(atezolizumab+bevacizumab+培美曲塞+卡鉑),具有與IMpower150研究類似的ORR(為62.5%),中位PFS為9.4個月,95%CI(56%,83%),并且毒性得到了改善。因此,有研究開始探索免疫聯合抗血管生成治療在可切除NSCLC的治療療效及安全性,目前此研究尚在進行中,結果尚未披露。從晚期治療的效果來看,化療聯合免疫治療和抗血管生成治療,可能是可切除NSCLC術前新輔助治療的一種很有前景的治療手段,特別是對于EGFR基因/ALK基因陽性患者,此聯合治療可能會帶來更多希望。
4 術后輔助免疫治療
NSCLC單純手術后容易復發,術后輔助化療可以降低復發風險,但效果并不明顯,5年生存率改善僅約5%[4],對于單獨手術后NSCLC,尋找一種更好的術后輔助治療手段顯得尤為重要。隨著ADAURA研究[44]長期生存結果的公布,術后輔助靶向治療已成為EGFR基因突變陽性NSCLC的標準治療手段。然而NSCLC術后還有很大部分是EGFR基因野生型患者,這類患者的術后輔助治療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術后輔助免疫治療在多個癌種中獲得可喜的生存獲益[45]。因此,也有研究[10-11]對NSCLC術后輔助免疫治療進行了探索;見表3。目前最重要的2個研究是KEYNOTE-091及IMpower010研究。IMpower010研究[11]顯示:對于PD-L1 TC≥1%Ⅱ~ⅢA期人群,atezolizumab組的中位DFS明顯優于對照組(NE vs. 35.3個月),顯著降低了復發或死亡風險,HR=0.66(P=0.004)。2年后atezolizumab組的DFS率為74.6%,高于對照組的61.0%;3年后兩組的DFS率分別降至60.0%和48.2%,并且未見新的治療相關不良事件發生。KEYNOTE-091研究[10]顯示,pembrolizumab組和安慰劑組的中位DFS分別為58.7個月(39.2個月~NR)和34.9個月(28.6個月~NR)(HR=0.73)。其中,在PD-L1 TPS≥50%患者中,pembrolizumab組(n=143)和安慰劑組(n=141)的中位DFS均未達到(HR=0.80)。兩組中3~5級不良事件發生率分別為34.3%和25.7%。基于KEYNOTE-091研究,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準了pembrolizumab輔助治療適應證,用于ⅠB期(T2a≥4 cm)、Ⅱ期或ⅢA期NSCLC患者切除和輔助含鉑化療后的輔助治療。
5 圍術期免疫治療(術前新輔助聯合術后輔助治療)
既往研究表明,無論是術前新輔助還是術后輔助免疫治療都能使患者獲益。從圍術期治療來看,新輔助免疫治療和輔助免疫治療的全程應用是否可行,是否會進一步改善患者預后,成為目前臨床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目前研究的熱點;見表4。在2023年美國ASCO會議上,多個Ⅲ期研究公布了圍術期免疫治療的研究結果。AEGEAN研究[46]是首個公布結果的“新輔助免疫治療+手術+輔助免疫治療”模式的Ⅲ期研究,評估無EGFR及ALK突變的可切除ⅡA~ⅢB(N2)期NSCLC患者使用Durvalumab進行“新輔助免疫治療+手術切除+術后輔助免疫治療”方案的療效與安全性,研究結果顯示,試驗組明顯提高了MPR及pCR率(33.3% vs. 12.3%,17.2% vs. 4.3%);并未發現有統計學差異的不良事件發生。中位隨訪11.7個月后發現,試驗組和對照組的中位EFS分別為NR和25.9個月[HR=0.68,95%CI(0.53,0.88),P=0.0039];并且EFS獲益并不受PD-L1表達情況及化療方案的影響。由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牽頭的Neotorch研究[47]是全球首個抗PD-1單抗用于NSCLC圍手術期治療達到主要終點的Ⅲ期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與單純化療相比,toripalimab聯合化療用于Ⅲ期可手術NSCLC患者圍手術期治療并在后續進行toripalimab單藥鞏固治療,可顯著延長患者EFS(研究者評估的中位EFS分別為未達到 vs. 15.1個月,P<0.0001),疾病復發、進展或死亡風險降低達60%[HR=0.40,95%CI(0.277,0.565),P<0.0001]。兩組的1年EFS率和2年EFS率分別為84.4% vs. 57.0%和64.7% vs. 38.7%。toripalimab聯合化療組的MPR率和pCR率均優于單純化療組,分別為48.5% vs. 8.4%(P<0.0001)和24.8% vs. 1.0%(P<0.0001)。toripalimab聯合化療組的OS也顯示出明顯的獲益趨勢。兩組中位OS分別為未成熟vs. 30.4個月[HR=0.62,95%CI(0.381,0.999)];1年OS率和2年OS率分別為94.4% vs. 89.6%和81.2% vs. 74.3%。在安全性方面,兩組患者無明顯差異。KEYNOTE-671研究[9]是首個以OS為主要研究終點的隨機、雙盲Ⅲ期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與安慰劑組相比,pembrolizumab組患者的疾病進展、疾病復發或死亡危險降低了42%(HR=0.58,P<0.001)。pembrolizumab組的MPR率是安慰劑組的近3倍(30.2% vs. 11.0%),pCR率是安慰劑組的4倍多(18.1% vs. 4.0%);在安全性方面,治療相關不良事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研究團隊比較了KEYNOTE-671與CheckMate 816的試驗數據。CheckMate 816研究中,沒有達到pCR的患者疾病進展、疾病復發或死亡的HR=0.84,而在KEYNOTE-671研究(新輔助免疫+輔助免疫治療)中HR=0.69。雖然這種比較不夠嚴謹,但也暗示了在新輔助免疫治療后使用輔助免疫治療或許能進一步提升治療效果。
6 敏感人群篩選
從以上研究可知,免疫治療為可切除NSCLC帶來了新的希望,然而,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從免疫治療中獲益,甚至部分患者因為免疫治療導致手術延遲、疾病進展,最終導致對患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因此,篩選出對免疫治療敏感的人群,進行個體化治療顯得更為重要。目前有很多研究探索了NSCLC患者對免疫治療敏感的生物標志物,其中以PD-L1、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及循環腫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最為重要。
PD-L1是一種在腫瘤細胞上表達的共調節分子,可抑制T細胞介導的細胞死亡。在PD-L1存在的情況下,T細胞的活性被抑制。免疫治療抑制PD-1與PD-L1的相互作用,從而提高內源性T細胞的抗腫瘤活性。多個晚期NSCLC免疫治療相關研究[6,48]顯示,PD-L1表達陽性及表達程度與患者免疫治療的療效直接相關。因此,FDA已經批準PD-L1的表達用于預測晚期NSCLC免疫治療療效的生物標志物。然而,PD-L1狀態是否可以作為NSCLC新輔助免疫治療的預測因素仍在討論中,不同研究得出不同結論,甚至有相反的結論。NEOSTAR研究[15]顯示,PD-L1的表達和表達程度與治療后更大的病理反應和更少的殘留腫瘤細胞相關,然而,在PD-L1陰性患者中也觀察到了病理反應,并且沒有發現治療后腫瘤PD-L1表達和反應之間的關聯。Checkmate-159研究[13]顯示,PD-L1的表達與治療后病理反應無關。CheckMate 816研究[8]亞組分析發現,PD-L1陽性患者更能從新輔助nivolumab+化療中獲益。AEGEAN研究[46]提示,PD-L1高表達(TC≥50%)在EFS和pCR上都表現出更優的獲益。Neotorch研究[47]顯示,無論PD-L1≥1%還是PD-L1<1%,新輔助toripalimab+化療較化療均改善EFS,但是PD-L1 1%~49%及PD-L1≥50% 的療效未知。KEYNOTE-671研究[9]顯示無論PD-L1表達情況如何均可從圍術期免疫治療中獲益。IMpower010研究[11]延長了PD-L1 TC≥1%患者的OS[HR=0.71,95%CI(0.49,1.03)],其中PD-L1 TC≥50%人群OS改善更為突出。而KEYNOTE-091研究[10]卻顯示,術后輔助免疫治療無論PD-L1是否表達都能獲益,而PDL-1 TC≥50%的患者卻是陰性結果,結果似乎相互矛盾,作者解釋這可能與安慰劑的超常發揮相關。綜上所述,從目前證據來看,PD-L1表達情況只能作為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的一種預測手段,而不能成為絕對指標。
TMB作為腫瘤組織的一種遺傳特征,正在成為免疫治療反應的潛在預測生物標志物。在晚期轉移性NSCLC中,TMB作為一種預測分子標記物的價值目前尚存在爭議[49]。理論上,更高的TMB可觸發免疫治療更好的反應,這已經在一些研究[50-51]中得以證實。盡管美國FDA在2020年批準pembrolizumab用于TMB高實體腫瘤,包括不可切除的NSCLC,但TMB在新輔助免疫治療中的應用仍有很多爭議[52]。在KEYNOTE-021、189、407研究[53]中發現,TMB與化療聯合免疫治療的療效無關,并且在LCMC3、NEOSTAR和NADIM試驗[15,18,30]中也觀察到了同樣的結果,Checkmate-159研究[13]發現TMB與MPR率呈負相關。而CheckMate 816研究[8]發現無論TMB值如何,pCR率均可獲益。
ctDNA被認為與晚期NSCLC的復發和預后密切相關[54]。ctDNA在新輔助免疫治療中的預測價值也在一些研究中進行了探索。CheckMate 816研究[8]收集入組患者的血液標本,進行了3個療程的ctDNA檢測。結果顯示,新輔助nivolumab+化療和化療治療組的ctDNA清除率分別為56%和34%。進一步研究發現ctDNA清除組的pCR率高于未清除組(nivolumab+化療組為46% vs. 24%,化療組為13% vs. 2.2%)。NADIM研究[30]發現了類似的結果。LCMC3研究[18]表明ctDNA可能是更好的病理反應和更長生存期的預測因子。因此,納入ctDNA評估可能有助于篩選出新輔助免疫治療敏感人群,從而避免昂貴和潛在毒性的輔助治療。
7 總結與展望
隨著Ⅲ期臨床研究結果的陸續公布,可切除NSCLC輔助治療正式進入免疫時代。免疫治療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1)單純新輔助免疫治療;(2)單純新輔助免疫治療聯合化療;(3)單純術后輔助免疫治療;(4)“夾心餅”模式,即術前新輔助免疫治療+術后輔助免疫治療。目前,模式1的應用還有較大爭議,還需大樣本隨機對照研究進一步證實,模式2及模式3均基于Ⅲ期研究結果得以獲批相應的適應證,而模式4的探討仍在進行中,還有多個Ⅲ期研究尚未達到研究終點。
整體來說,圍術期免疫治療相比化療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免疫治療既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挑戰,同時也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比如不同分期患者的治療選擇,雖然目前的研究納入的對象大多都包括ⅠB~ⅢA期,但是入組患者更多的還是Ⅲ期患者,與真實臨床應用基本吻合,對于ⅠB期患者臨床更多采用的還是直接手術,術前新輔助免疫在這類患者中是否能夠獲益還需進一步探索。因此,更加精準的敏感人群篩選顯得尤為重要,而最佳的治療模式及手術時機的選擇也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予以證實。隨著相關研究的進行,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也將不斷優化可切除NSCLC免疫治療的格局。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楊毫負責研究設計,論文撰寫;張程誠、張躍、張力文參與選題及設計;付茂勇負責總體設計與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