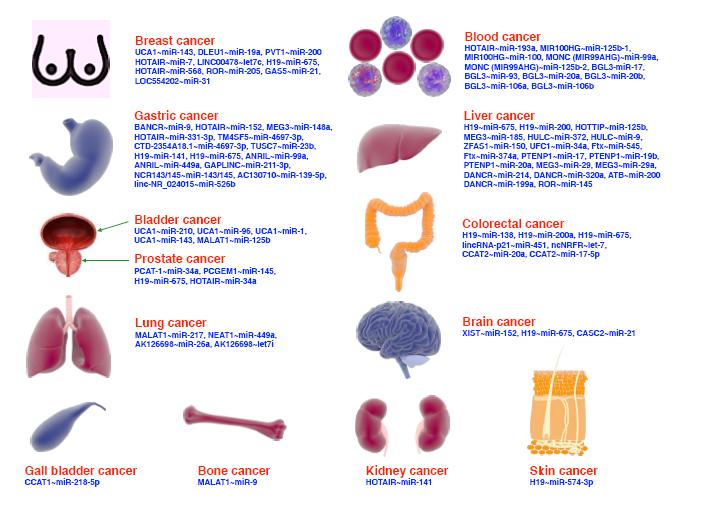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一種高致死率、高并發癥率主動脈急癥。ATAAD急診修復術后30 d死亡率為10%~35%[1],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也居高不下。ATAAD急診修復術后急性腎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AKI)發生率可達40%~55%[2-4],遠高于其他類型心臟開放手術[5]。ATAAD修復術患者腎功能損傷病因復雜。首先,ATAAD具有獨特的病理生理特征,當動脈內膜夾層累及單側或雙側腎動脈時,可能導致腎臟灌注不良,進而增加腎臟缺血-再灌注損傷風險[6]。其次,ATAAD修復手術本身具有復雜性,手術時間長以及深低溫停循環技術的應用都會增加腎功能受損風險。
既往觀點認為,AKI是可逆的急性病變,其對患者長期預后并無影響。然而,近年來通過對臨床案例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發現即使是恢復速度較快的輕度AKI患者,其后續患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腎纖維化乃至終末期腎病的風險均呈現出顯著增高的趨勢,使得此類患者的死亡率也隨之上升[7-9]。然而,關于ATAAD修復術人群遠期腎功能情況及其圍術期危險因素,目前尚缺乏相應的研究數據。早期夾層累及腎動脈是否會造成遠期腎功能不全,以及圍術期AKI的預后轉歸情況等問題都亟待研究數據支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ATAAD修復術后早期腎功能恢復情況,明確ATAAD修復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生率并探討其圍術期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分析2020—2021年在廈門大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接受ATAAD修復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患者納入標準:接受ATAAD急診修復手術患者。早期腎功能隊列排除標準:(1)年齡<18歲患者;(2)術中死亡患者;(3)基線或術后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數據缺失患者。遠期腎功能隊列排除標準:(1)院內死亡患者;(2)術后6個月sCr數據缺失患者。根據術后早期腎功能將患者分為AKI組和非AKI組,根據術后遠期腎功能將患者分為CKD組和非CKD組。
1.2 手術方法
手術采用常規胸部正中切口,動脈插管采用單純股動脈或股動脈及右側腋動脈單泵雙管,上下腔靜脈置管建立體外循環,深低溫停循環患者采用選擇性順行性腦灌注或逆行性腦灌注。
1.3 數據收集和定義
收集可能與AKI和CKD具有相關性的變量。患者變量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糖尿病、高血壓、心臟壓塞、馬方綜合征、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夾層累及腎動脈、術前sCr、術前腎小球濾過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術前血紅蛋白(hemoglobin,Hb)、術前血細胞比容(hematocrit,Hct)、術前血小板(platelet,Plt)、術前丙氨酸轉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術前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和術前凝血酶原時間(preoperative prothrombin time,PT)。夾層累及腎動脈定義為經腹部超聲或加強CT明確夾層累及腎動脈;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定義為經腹部超聲或加強CT明確夾層累及腎動脈,同時合并術前eGFR<60 mL/(min·1.73 m2);心臟壓塞定義為經超聲心動圖明確心包積液>100 mL,同時合并動脈收縮壓<90 mm Hg(1 mm Hg=0.133 kPa)。
手術變量包括從首發癥狀到手術的時間間隔、總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中尿量、術中體液平衡、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深低溫停循環時間、術中紅細胞輸注量。
術后變量包括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術后1~14 d sCr,術后6個月sCr、二次開胸、神經系統并發癥(瞻望、腦卒中及截癱)、機械通氣時間、住重癥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時間、術后住院時間、院內死亡。
1.4 研究終點
主要終點為ATAAD修復術后遠期CKD發生率,定義為術后6個月eGFR<60 mL/(min·1.73 m2)[10]。eGFR采用Cockcroft-Gault方程計算[11],采樣時間為修復術后6個月,誤差時間在10 d內。
次要研究終點包括術后2 d內發生AKI。AKI的診斷和分級基于改善全球腎臟病預后組織(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標準[10]。符合以下情況之一者即可被診斷為AKI:在 48 h內,sCr上升≥0.3 mg/dL(≥26.5 μmol/L);sCr升至≥1.5 倍基線值水平。AKI分級標準為:sCr升高為基線的1.5~1.9倍,或絕對值升高超過26.5 μmol/L(0.3 mg/dL)為AKI 1級;sCr升高為基線的2.0~2.9倍為AKI 2級;sCr升高為基線的3倍,或絕對值≥353.6 μmol/L(4.0 mg/dL),或開始使用CRRT為AKI 3級。基線sCr規定為術前24 h內最接近手術時間所測sCr值,術后sCr為術后前2 d內sCr最高值。AKI的恢復情況觀察時間窗為AKI事件發生后2周內,sCr恢復至基線值的<1.5倍定義為AKI恢復。
其他次要研究終點事件為院內不良綜合預后,定義為術后發生以下任意一種不良事件:院內死亡、術后神經功能損傷(瞻望、腦卒中及截癱)、早期再次手術、術后住ICU時間延長≥5 d和機械通氣時間延長≥2 d。
1.5 統計學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的統計分析均采用R 3.3.3軟件。分類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檢驗水準α=0.05。
相關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探究術后AKI和CKD的獨立危險因素。在風險因素分析中,預測變量選自單變量分析中P<0.10的變量。基于最小赤池信息量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值,以后向剔除法選擇最佳模型,模型評價采用R2值。通過保留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評估多重共線性(VIF>2.5表示存在多重共線性)。為構建可靠的回歸模型,每個納入模型的協變量至少需要8例以上事件[12]。因此,在術后AKI作為因變量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中可納入14個協變量,在術后CKD作為因變量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中可納入5個協變量。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廈門大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2022-22。
2 結果
2.1 患者基線資料
2020—2021年于廈門大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接受ATAAD修復術患者共260例,排除<18歲患者1例,因術中死亡無法獲得術后sCr數據患者3例,以及基線或術后數據缺失患者1例。最終,共255例符合上述標準的患者被納入早期腎功能研究隊列,男200例、女55例,平均年齡(52.80±12.46)歲,其中AKI組112例,非AKI組143例。232例患者可獲得遠期sCr隨訪數據,納入遠期腎功能隊列,其中CKD組40例,非CKD組192例。多數患者(190/255,74.5%)有高血壓病史。其他合并癥包括心臟壓塞(14.9%)、馬方綜合征(3.1%)、冠心病(8.2%);見表1。
2.2 患者圍術期資料
根據KIDGO標準,112例患者在術后48 h內出現AKI,其中1、2和3級分別為47例(18.4%)、27例(10.6%)和38例(14.9%),27例(10.6%)患者需接受血液透析治療。此外,院內死亡率為7.1%,28例(11.0%)患者在修復術后需要再次開胸止血。呼吸機支持時間>2 d和ICU停留時間>5 d患者比例分別為52.5%和50.6%;見表2。
77.7%(87/112)AKI患者發生不良預后,這一比例在非AKI患者中僅為44.8%(64/143)(P<0.001);見表2。通過logistic回歸分析矯正年齡、性別、BMI、術前Plt、術前ALT、術前sCr、術前PT和CPB時間混雜因素后,AKI是術后不良綜合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OR=3.496,95%CI(1.955,6.379),P<0.001]。術后不良綜合預后的其他獨立危險因素包括女性[OR=0.442,95%CI(0.118,0.983),P=0.054]、術前Plt[OR=0.996,95%CI(0.992,1.000),P=0.036]、CPB時間[OR=1.051,95%CI(1.007,1.100),P=0.026]。
2.3 術后急性腎損傷的危險因素
術后AKI預測模型納入以下風險因素:基線sCr值、術前 PT、BMI、夾層累及腎動脈、術中紅細胞輸注量、術中尿量和CPB時間。由于CPB時間與手術時間,術中尿量與體液平衡或術中出血量之間存在共線性,因此總手術時間、體液平衡和術中出血量均未納入模型。經過校正,夾層累及腎動脈[OR=2.144,95%CI(1.234,3.765),P=0.007]、術中尿量[OR=0.761,95%CI(0.625,0.911),P=0.004]和術中紅細胞輸注量[OR=1.288,95%CI(1.088,1.543),P=0.004]與ATAAD修復術后早期AKI顯著相關;見表3。
2.4 腎功能恢復和慢性腎臟病
AKI組和非AKI組的平均sCr水平分別在術后第2 d和術后第1 d達到峰值,此后在非AKI組和輕中度AKI 組患者sCr水平呈逐漸下降趨勢,但在重度AKI 組患者中sCr常在術后2周內仍處于較高水平;見圖1。
術后14 d,112例AKI患者中有93例(83.0%)腎功能恢復。AKI 2級和3級患者的恢復率為70.3%,而1級患者的恢復率為96.0%(P=0.001)。
本研究在術后6個月對是否發生CKD進行了隨訪,91.0%(232/255)的患者可獲得遠期隨訪數據。其中,17.2%(40/232)的患者發生CKD。與非CKD組相比,CKD組患者年齡偏大(P=0.001),BMI指數較低(P<0.001)。CKD患者術前合并心臟壓塞(P=0.045)和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P<0.001)的比例高于非CKD患者。CKD患者術前Plt水平低于非CKD組(P=0.002)。CKD組患者術后住院時間較非CKD組患者更長(P=0.022);見表4~5。
在多變量分析中,術后6個月出現CKD的獨立預測因素為:較低的BMI (P=0.003)、心臟壓塞(P=0.005)、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P<0.001)、sCr達峰時間>3 d(P<0.001),術后AKI(P<0.05);見表6。
3 討論
目前,探究心臟術后遠期腎功能研究多以常規瓣膜或搭橋手術患者為研究對象,針對ATAAD修復術患者的研究尚屬于空白[13-15]。本研究證實,ATAAD修復術相關AKI大多(83%,93/112)可在術后兩周內康復;但相較于其他類型心臟開放手術,ATAAD修復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生率較高(17.2% vs. 5.4%)[14];且較低BMI、術前合并心臟壓塞和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術后sCr達到峰值的時間>3 d以及術后AKI是ATAAD修復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的獨立危險因素。
與既往研究[16-17]結果一致,ATAAD修復術圍術期發生AKI風險非常高,圍術期腎功能損傷也與院內不良預后密切相關。本研究進一步證實,多數患者手術相關AKI通常不會持續存在,且輕度AKI相較于中重度更易恢復,即1級AKI短期腎功能恢復率為96%,2級或3級AKI的恢復率為70%[18]。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按照sCr濃度的標準,AKI在出院前通常是可逆的,但是AKI的持續時間(術后sCr峰值時間>3 d)和嚴重程度均是為遠期腎功能不全的獨立危險因素。這一結果證實了最近另一項基于心臟開放手術人群研究[13]的結論。該研究發現,行心臟搭橋和瓣膜手術患者,圍術期AKI與術后遠期新發CKD之間存在顯著的分級依賴相關性,并且當AKI持續超過48 h相關性進一步增加。
盡管目前對AKI到CKD轉化機制的理解仍然不完整,但幾十年來研究提示,這種轉化可能源自細胞反應不當或修復錯誤[19]。正常情況下,腎臟發生短暫或輕微AKI后會啟動脫分化、應激適應、代謝改變、炎癥細胞滲透、細胞外基質合成以及殘留腎單位增生等一系列協同機制[20-21],迅速恢復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腎功能,這一過程被稱作適應性修復。然而,若上述機制和信號通路出現過度、不足、持續時間過長或引導方向錯誤等問題,則導致腎功能障礙和瘢痕形成,即適應性修復障礙;目前實驗[19]證實與此相關的具體機制涵蓋腎小管細胞周期阻滯、表觀遺傳調控、線粒體功能障礙等。AKI出現后,腎小管、血管和間質區域均可發生適應性修復障礙,導致間質纖維化風險增高[22]。因此,盡管在本研究中,按照sCr濃度的標準AKI通常是可逆的,但適應性修復障礙可持續存在并導致遠期腎功能受損。
本研究發現,較高的BMI被為遠期腎功能的保護性因素。這一現象可以用“肥胖悖論”解釋,即在健康人群中肥胖與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發生密切相關,但在慢性疾病如心力衰竭、腎衰竭和糖尿病人群中,超重或輕度肥胖可提高生存率和改善預后[23]。這是因為,超重個體體內存在的代謝儲備可在手術和術后恢復過程中提供較好的營養基礎,此時肥胖保護效應就超過有害代謝效應并體現生存優勢[24]。本研究人群肥胖患者多為1級和2級肥胖,3級肥胖僅1例;基本滿足“肥胖悖論“中輕中度肥胖人群特征。
心臟壓塞是夾層主要的并發癥之一[25],本研究結果提示,術前合并心臟壓塞的夾層患者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病率增加。其可能的解釋是心臟壓塞影響心臟搏出量進而引發術前持續性低血壓,導致包括腎臟在內的內臟器官血液供應不足,加之手術過程中深低溫停循環等過程帶來的“二次打擊”引起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病率增高。為避免心臟壓塞對患者血流動力學影響,縮短因心包積液造成器官灌注不足的時間,適時行心包積液穿刺引流術,盡早開展手術治療,可能會利于改善遠期腎臟功能,減少CKD發生。
關于夾層累及腎動脈與遠期腎功能關系這一問題,本研究提示,術前合并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增加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生率,但當夾層累及腎動脈而未導致術前腎功能不全的情況下,僅增加圍術期AKI的發生危險而不影響遠期腎功能[26]。在本研究中,雖然腎動脈受累患者比例達55.3%,但合并術前eGFR降低,即腎灌注不良征綜合征發生率僅為23%,這與Qian等[27]報道的22%相近。當夾層僅累及腎動脈但未引發術前eGFR降低,提示腎臟血供尚可通過假腔維持,且在夾層修復術后腎動脈真腔開放,腎臟血供進一步修復,而不引起遠期腎功能改變;但當發生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時,表明術前腎臟已處于灌注不良狀態,加之深低溫停循環損害,增加了遠期腎功能不全風險[28]。Cho等[29]也提出,盡管臨床灌注不良似乎不會增加手術風險,但臨床灌注不良與較差的預后相關。因此,對于合并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的夾層患者,提高手術技術,縮短CPB和深低停循環時間尤為重要;此外,若ATAAD修復術后仍無法改善腎臟灌注的患者,積極行腎動脈血管內支架植入術,恢復腎臟灌注,或可達到遠期腎功能保護作用。
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回顧性研究設計可能降低數據完整性和準確性,但本研究中87%的患者可有效獲得遠期腎功能數據;同時主要研究數據,如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發生率和AKI發生率與既往研究基本一致,說明研究數據具有一定可靠性。其次,由于多數患者圍術期應用利尿劑,可能會影響尿量作為AKI診斷標準的準確性,本研究未將術后尿量納為AKI診斷依據。最后,由于主動脈夾層病理生理特殊性,部分患者夾層累及腎血管灌注,可能導致入院基線sCr水平上升,影響基于sCr標準的AKI診斷。
綜上所述,ATAAD修復術相關AKI在術后早期可恢復,但AKI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均會影響遠期腎功能;此外,患者圍術期情況,包括營養狀況、是否合并心臟壓塞和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對遠期腎功能也有一定影響。基于以上危險因素,早期識別ATAAD修復術后CKD高危患者并對其進行積極的術后隨訪和早期腎功能保護干預措施,有利于延緩CKD疾病進展,避免終末期腎臟病發生。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顏翩翩、國勝文提出研究思路,負責研究設計;黃毅婷、蔣露露參與文獻檢索與整理;吳錫階、顏翩翩、盧梅麗、國勝文參與手術及資料收集;國勝文負責數據統計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國勝文、周延青、馬嘉榮負責論文修改及審閱。
急性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acute Stanford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TAAD)是一種高致死率、高并發癥率主動脈急癥。ATAAD急診修復術后30 d死亡率為10%~35%[1],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也居高不下。ATAAD急診修復術后急性腎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AKI)發生率可達40%~55%[2-4],遠高于其他類型心臟開放手術[5]。ATAAD修復術患者腎功能損傷病因復雜。首先,ATAAD具有獨特的病理生理特征,當動脈內膜夾層累及單側或雙側腎動脈時,可能導致腎臟灌注不良,進而增加腎臟缺血-再灌注損傷風險[6]。其次,ATAAD修復手術本身具有復雜性,手術時間長以及深低溫停循環技術的應用都會增加腎功能受損風險。
既往觀點認為,AKI是可逆的急性病變,其對患者長期預后并無影響。然而,近年來通過對臨床案例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發現即使是恢復速度較快的輕度AKI患者,其后續患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腎纖維化乃至終末期腎病的風險均呈現出顯著增高的趨勢,使得此類患者的死亡率也隨之上升[7-9]。然而,關于ATAAD修復術人群遠期腎功能情況及其圍術期危險因素,目前尚缺乏相應的研究數據。早期夾層累及腎動脈是否會造成遠期腎功能不全,以及圍術期AKI的預后轉歸情況等問題都亟待研究數據支持。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ATAAD修復術后早期腎功能恢復情況,明確ATAAD修復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生率并探討其圍術期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分析2020—2021年在廈門大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接受ATAAD修復手術患者的臨床資料。患者納入標準:接受ATAAD急診修復手術患者。早期腎功能隊列排除標準:(1)年齡<18歲患者;(2)術中死亡患者;(3)基線或術后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數據缺失患者。遠期腎功能隊列排除標準:(1)院內死亡患者;(2)術后6個月sCr數據缺失患者。根據術后早期腎功能將患者分為AKI組和非AKI組,根據術后遠期腎功能將患者分為CKD組和非CKD組。
1.2 手術方法
手術采用常規胸部正中切口,動脈插管采用單純股動脈或股動脈及右側腋動脈單泵雙管,上下腔靜脈置管建立體外循環,深低溫停循環患者采用選擇性順行性腦灌注或逆行性腦灌注。
1.3 數據收集和定義
收集可能與AKI和CKD具有相關性的變量。患者變量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糖尿病、高血壓、心臟壓塞、馬方綜合征、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夾層累及腎動脈、術前sCr、術前腎小球濾過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術前血紅蛋白(hemoglobin,Hb)、術前血細胞比容(hematocrit,Hct)、術前血小板(platelet,Plt)、術前丙氨酸轉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術前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和術前凝血酶原時間(preoperative prothrombin time,PT)。夾層累及腎動脈定義為經腹部超聲或加強CT明確夾層累及腎動脈;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定義為經腹部超聲或加強CT明確夾層累及腎動脈,同時合并術前eGFR<60 mL/(min·1.73 m2);心臟壓塞定義為經超聲心動圖明確心包積液>100 mL,同時合并動脈收縮壓<90 mm Hg(1 mm Hg=0.133 kPa)。
手術變量包括從首發癥狀到手術的時間間隔、總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中尿量、術中體液平衡、體外循環(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深低溫停循環時間、術中紅細胞輸注量。
術后變量包括連續性腎臟替代治療(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術后1~14 d sCr,術后6個月sCr、二次開胸、神經系統并發癥(瞻望、腦卒中及截癱)、機械通氣時間、住重癥監護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時間、術后住院時間、院內死亡。
1.4 研究終點
主要終點為ATAAD修復術后遠期CKD發生率,定義為術后6個月eGFR<60 mL/(min·1.73 m2)[10]。eGFR采用Cockcroft-Gault方程計算[11],采樣時間為修復術后6個月,誤差時間在10 d內。
次要研究終點包括術后2 d內發生AKI。AKI的診斷和分級基于改善全球腎臟病預后組織(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標準[10]。符合以下情況之一者即可被診斷為AKI:在 48 h內,sCr上升≥0.3 mg/dL(≥26.5 μmol/L);sCr升至≥1.5 倍基線值水平。AKI分級標準為:sCr升高為基線的1.5~1.9倍,或絕對值升高超過26.5 μmol/L(0.3 mg/dL)為AKI 1級;sCr升高為基線的2.0~2.9倍為AKI 2級;sCr升高為基線的3倍,或絕對值≥353.6 μmol/L(4.0 mg/dL),或開始使用CRRT為AKI 3級。基線sCr規定為術前24 h內最接近手術時間所測sCr值,術后sCr為術后前2 d內sCr最高值。AKI的恢復情況觀察時間窗為AKI事件發生后2周內,sCr恢復至基線值的<1.5倍定義為AKI恢復。
其他次要研究終點事件為院內不良綜合預后,定義為術后發生以下任意一種不良事件:院內死亡、術后神經功能損傷(瞻望、腦卒中及截癱)、早期再次手術、術后住ICU時間延長≥5 d和機械通氣時間延長≥2 d。
1.5 統計學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的統計分析均采用R 3.3.3軟件。分類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描述,組間比較采用Wilcoxon秩和檢驗。檢驗水準α=0.05。
相關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探究術后AKI和CKD的獨立危險因素。在風險因素分析中,預測變量選自單變量分析中P<0.10的變量。基于最小赤池信息量準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值,以后向剔除法選擇最佳模型,模型評價采用R2值。通過保留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評估多重共線性(VIF>2.5表示存在多重共線性)。為構建可靠的回歸模型,每個納入模型的協變量至少需要8例以上事件[12]。因此,在術后AKI作為因變量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中可納入14個協變量,在術后CKD作為因變量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中可納入5個協變量。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廈門大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2022-22。
2 結果
2.1 患者基線資料
2020—2021年于廈門大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接受ATAAD修復術患者共260例,排除<18歲患者1例,因術中死亡無法獲得術后sCr數據患者3例,以及基線或術后數據缺失患者1例。最終,共255例符合上述標準的患者被納入早期腎功能研究隊列,男200例、女55例,平均年齡(52.80±12.46)歲,其中AKI組112例,非AKI組143例。232例患者可獲得遠期sCr隨訪數據,納入遠期腎功能隊列,其中CKD組40例,非CKD組192例。多數患者(190/255,74.5%)有高血壓病史。其他合并癥包括心臟壓塞(14.9%)、馬方綜合征(3.1%)、冠心病(8.2%);見表1。
2.2 患者圍術期資料
根據KIDGO標準,112例患者在術后48 h內出現AKI,其中1、2和3級分別為47例(18.4%)、27例(10.6%)和38例(14.9%),27例(10.6%)患者需接受血液透析治療。此外,院內死亡率為7.1%,28例(11.0%)患者在修復術后需要再次開胸止血。呼吸機支持時間>2 d和ICU停留時間>5 d患者比例分別為52.5%和50.6%;見表2。
77.7%(87/112)AKI患者發生不良預后,這一比例在非AKI患者中僅為44.8%(64/143)(P<0.001);見表2。通過logistic回歸分析矯正年齡、性別、BMI、術前Plt、術前ALT、術前sCr、術前PT和CPB時間混雜因素后,AKI是術后不良綜合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OR=3.496,95%CI(1.955,6.379),P<0.001]。術后不良綜合預后的其他獨立危險因素包括女性[OR=0.442,95%CI(0.118,0.983),P=0.054]、術前Plt[OR=0.996,95%CI(0.992,1.000),P=0.036]、CPB時間[OR=1.051,95%CI(1.007,1.100),P=0.026]。
2.3 術后急性腎損傷的危險因素
術后AKI預測模型納入以下風險因素:基線sCr值、術前 PT、BMI、夾層累及腎動脈、術中紅細胞輸注量、術中尿量和CPB時間。由于CPB時間與手術時間,術中尿量與體液平衡或術中出血量之間存在共線性,因此總手術時間、體液平衡和術中出血量均未納入模型。經過校正,夾層累及腎動脈[OR=2.144,95%CI(1.234,3.765),P=0.007]、術中尿量[OR=0.761,95%CI(0.625,0.911),P=0.004]和術中紅細胞輸注量[OR=1.288,95%CI(1.088,1.543),P=0.004]與ATAAD修復術后早期AKI顯著相關;見表3。
2.4 腎功能恢復和慢性腎臟病
AKI組和非AKI組的平均sCr水平分別在術后第2 d和術后第1 d達到峰值,此后在非AKI組和輕中度AKI 組患者sCr水平呈逐漸下降趨勢,但在重度AKI 組患者中sCr常在術后2周內仍處于較高水平;見圖1。
術后14 d,112例AKI患者中有93例(83.0%)腎功能恢復。AKI 2級和3級患者的恢復率為70.3%,而1級患者的恢復率為96.0%(P=0.001)。
本研究在術后6個月對是否發生CKD進行了隨訪,91.0%(232/255)的患者可獲得遠期隨訪數據。其中,17.2%(40/232)的患者發生CKD。與非CKD組相比,CKD組患者年齡偏大(P=0.001),BMI指數較低(P<0.001)。CKD患者術前合并心臟壓塞(P=0.045)和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P<0.001)的比例高于非CKD患者。CKD患者術前Plt水平低于非CKD組(P=0.002)。CKD組患者術后住院時間較非CKD組患者更長(P=0.022);見表4~5。
在多變量分析中,術后6個月出現CKD的獨立預測因素為:較低的BMI (P=0.003)、心臟壓塞(P=0.005)、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P<0.001)、sCr達峰時間>3 d(P<0.001),術后AKI(P<0.05);見表6。
3 討論
目前,探究心臟術后遠期腎功能研究多以常規瓣膜或搭橋手術患者為研究對象,針對ATAAD修復術患者的研究尚屬于空白[13-15]。本研究證實,ATAAD修復術相關AKI大多(83%,93/112)可在術后兩周內康復;但相較于其他類型心臟開放手術,ATAAD修復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生率較高(17.2% vs. 5.4%)[14];且較低BMI、術前合并心臟壓塞和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術后sCr達到峰值的時間>3 d以及術后AKI是ATAAD修復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的獨立危險因素。
與既往研究[16-17]結果一致,ATAAD修復術圍術期發生AKI風險非常高,圍術期腎功能損傷也與院內不良預后密切相關。本研究進一步證實,多數患者手術相關AKI通常不會持續存在,且輕度AKI相較于中重度更易恢復,即1級AKI短期腎功能恢復率為96%,2級或3級AKI的恢復率為70%[18]。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按照sCr濃度的標準,AKI在出院前通常是可逆的,但是AKI的持續時間(術后sCr峰值時間>3 d)和嚴重程度均是為遠期腎功能不全的獨立危險因素。這一結果證實了最近另一項基于心臟開放手術人群研究[13]的結論。該研究發現,行心臟搭橋和瓣膜手術患者,圍術期AKI與術后遠期新發CKD之間存在顯著的分級依賴相關性,并且當AKI持續超過48 h相關性進一步增加。
盡管目前對AKI到CKD轉化機制的理解仍然不完整,但幾十年來研究提示,這種轉化可能源自細胞反應不當或修復錯誤[19]。正常情況下,腎臟發生短暫或輕微AKI后會啟動脫分化、應激適應、代謝改變、炎癥細胞滲透、細胞外基質合成以及殘留腎單位增生等一系列協同機制[20-21],迅速恢復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腎功能,這一過程被稱作適應性修復。然而,若上述機制和信號通路出現過度、不足、持續時間過長或引導方向錯誤等問題,則導致腎功能障礙和瘢痕形成,即適應性修復障礙;目前實驗[19]證實與此相關的具體機制涵蓋腎小管細胞周期阻滯、表觀遺傳調控、線粒體功能障礙等。AKI出現后,腎小管、血管和間質區域均可發生適應性修復障礙,導致間質纖維化風險增高[22]。因此,盡管在本研究中,按照sCr濃度的標準AKI通常是可逆的,但適應性修復障礙可持續存在并導致遠期腎功能受損。
本研究發現,較高的BMI被為遠期腎功能的保護性因素。這一現象可以用“肥胖悖論”解釋,即在健康人群中肥胖與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發生密切相關,但在慢性疾病如心力衰竭、腎衰竭和糖尿病人群中,超重或輕度肥胖可提高生存率和改善預后[23]。這是因為,超重個體體內存在的代謝儲備可在手術和術后恢復過程中提供較好的營養基礎,此時肥胖保護效應就超過有害代謝效應并體現生存優勢[24]。本研究人群肥胖患者多為1級和2級肥胖,3級肥胖僅1例;基本滿足“肥胖悖論“中輕中度肥胖人群特征。
心臟壓塞是夾層主要的并發癥之一[25],本研究結果提示,術前合并心臟壓塞的夾層患者術后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病率增加。其可能的解釋是心臟壓塞影響心臟搏出量進而引發術前持續性低血壓,導致包括腎臟在內的內臟器官血液供應不足,加之手術過程中深低溫停循環等過程帶來的“二次打擊”引起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病率增高。為避免心臟壓塞對患者血流動力學影響,縮短因心包積液造成器官灌注不足的時間,適時行心包積液穿刺引流術,盡早開展手術治療,可能會利于改善遠期腎臟功能,減少CKD發生。
關于夾層累及腎動脈與遠期腎功能關系這一問題,本研究提示,術前合并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增加遠期腎功能不全發生率,但當夾層累及腎動脈而未導致術前腎功能不全的情況下,僅增加圍術期AKI的發生危險而不影響遠期腎功能[26]。在本研究中,雖然腎動脈受累患者比例達55.3%,但合并術前eGFR降低,即腎灌注不良征綜合征發生率僅為23%,這與Qian等[27]報道的22%相近。當夾層僅累及腎動脈但未引發術前eGFR降低,提示腎臟血供尚可通過假腔維持,且在夾層修復術后腎動脈真腔開放,腎臟血供進一步修復,而不引起遠期腎功能改變;但當發生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時,表明術前腎臟已處于灌注不良狀態,加之深低溫停循環損害,增加了遠期腎功能不全風險[28]。Cho等[29]也提出,盡管臨床灌注不良似乎不會增加手術風險,但臨床灌注不良與較差的預后相關。因此,對于合并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的夾層患者,提高手術技術,縮短CPB和深低停循環時間尤為重要;此外,若ATAAD修復術后仍無法改善腎臟灌注的患者,積極行腎動脈血管內支架植入術,恢復腎臟灌注,或可達到遠期腎功能保護作用。
本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回顧性研究設計可能降低數據完整性和準確性,但本研究中87%的患者可有效獲得遠期腎功能數據;同時主要研究數據,如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發生率和AKI發生率與既往研究基本一致,說明研究數據具有一定可靠性。其次,由于多數患者圍術期應用利尿劑,可能會影響尿量作為AKI診斷標準的準確性,本研究未將術后尿量納為AKI診斷依據。最后,由于主動脈夾層病理生理特殊性,部分患者夾層累及腎血管灌注,可能導致入院基線sCr水平上升,影響基于sCr標準的AKI診斷。
綜上所述,ATAAD修復術相關AKI在術后早期可恢復,但AKI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均會影響遠期腎功能;此外,患者圍術期情況,包括營養狀況、是否合并心臟壓塞和腎臟灌注不良綜合征對遠期腎功能也有一定影響。基于以上危險因素,早期識別ATAAD修復術后CKD高危患者并對其進行積極的術后隨訪和早期腎功能保護干預措施,有利于延緩CKD疾病進展,避免終末期腎臟病發生。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顏翩翩、國勝文提出研究思路,負責研究設計;黃毅婷、蔣露露參與文獻檢索與整理;吳錫階、顏翩翩、盧梅麗、國勝文參與手術及資料收集;國勝文負責數據統計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國勝文、周延青、馬嘉榮負責論文修改及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