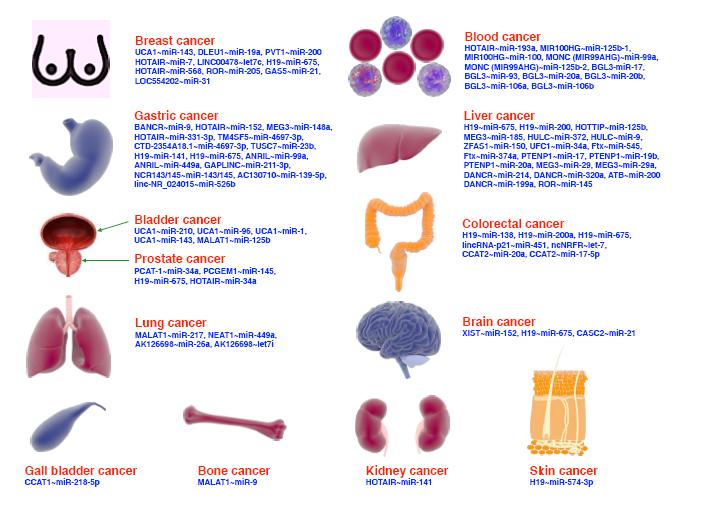近幾年,心血管外科領域革故鼎新、突飛猛進,多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為患者的健康福祉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新技術的層出不窮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希望,也帶來了對過去理念的不斷挑戰。本文旨在全面概述近年,尤其是2023年以來心血管外科的最新進展,介紹心血管外科領域的前沿知識和技術,包括主動脈瓣疾病的終身管理、人工瓣膜領域、二尖瓣領域、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治療選擇、心臟移植領域、左心室輔助領域、冠狀動脈外科領域、慢性心力衰竭的心臟結構干預手段、主動脈夾層領域及心房顫動的外科綜合治療,并深入分析和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以期為廣大心血管醫生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啟示,共同推動我國心血管外科事業的不斷前進。
近年來,心血管外科領域經歷了深刻的變革和飛速的發展,取得了多項突破性進展,為患者的健康和福祉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正如每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機遇與挑戰總是并存。新技術的層出不窮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希望,同時也對過去的理念提出了挑戰。本文旨在全面概述近年來,尤其是2023年以來心血管外科的最新進展,介紹心血管外科領域的前沿知識和技術,并深入分析和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
1 主動脈瓣疾病的終身管理
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適應證覆蓋全部高、中、低風險人群,乃至無癥狀人群[1]。TAVR技術不斷成熟,安全性指標包括死亡、致殘性卒中的數據已開始顯露出優于外科主動脈瓣置換(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AVR)的趨勢[2]。NOTION等研究[3-4]10年隨訪證實TAVR耐久性可能優于SAVR,經導管瓣中瓣(valve-in-valve,VIV)技術成熟也使得外科醫生認可的生物瓣應用年齡不斷下探[5-6]。年輕(<65歲)主動脈瓣病變患者在首次接受手術時實施TAVR還是SAVR?盡管從未在隨機對照試驗中驗證,但臨床實踐一直在推動TAVR在越來越年輕的患者中應用[7],低齡化即將成為必然。在預期壽命不斷增長的人群中制定終身管理策略,對于在生命各個階段實現主動脈瓣疾病治療的最佳結果至關重要[8-10]。患者的終身管理需要考慮一系列問題,沒有一種策略適合所有患者。最佳策略應根據患者選擇、合并疾病進展、術者經驗、根部解剖特征、設備技術特點進行個性化定制,全面的管理計劃需持續到術后20年以上[11-16]。首次瓣膜類型選擇幾乎為后續治療方案選擇定下了基調,再次手術的風險和效果是主要考量因素,如何保持首次及后續歷次手術人工瓣膜更優化的血流動力學,尤其是對小瓣環和假體-患者不匹配(prosthesis-patient mismatch,PPM)風險較大者,這些復雜問題及決策將在未來心臟團隊術前討論和患者溝通中變得更為普遍[17-21]。
目前廣泛的臨床研究已經得出較為明確的結論,包括:(1)PPM是加速瓣膜衰敗、引起長期預后不良的顯著危險因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容忍PPM,而環內瓣膜與PPM風險增加相關[22],因此小瓣環患者應該盡量避免使用環內瓣膜;現有研究[23]顯示SAVR聯合根部擴大術顯著降低了PPM的風險,且與單純SAVR手術相比近期和長期預后相當。近年來也出現了更為簡化、安全的根部擴大方法[24],因此對初次手術患者實施必要的根部擴大術以適應未來VIV的需要(包括降低VIV后PPM發生率)可能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當首次手術為SAVR時,第二次手術選擇VIV還是redo-SAVR的對比研究[25]中,VIV近期死亡率、卒中和大出血風險更低(redo-SAVR圍術期死亡率為3%~8%),VIV的PPM和小葉血栓風險更大,心力衰竭再住院率更高,尤其是使用球囊擴張瓣膜時。VIV相比redo-SAVR的早期獲益在1.5年后交叉并顯著減弱,整體上二者長期預后無明顯差異[26]。因此,瓣口面積更大的自膨脹瓣膜是TAVR VIV的首選,而對于首次SAVR的瓣膜選擇也有著潛在影響,19#、21#瓣膜使用將越來越少,盡可能大號的、支架可斷裂的牛心包支架內瓣膜、限位可擴張干瓣、免縫合瓣等類型的使用率均可能上升,以盡可能提高耐久性。Edwards Perimount瓣膜術后20年瓣膜衰敗風險為30%±3%,特定年齡組耐久性總體預測為19年,已被視為瓣膜耐久性的參照標準[11]。對于首次使用小號生物瓣的年輕SAVR患者,鑒于長期結局仍更推薦redo-SAVR。由于市面上大多數生物瓣使用的是支架內瓣膜,多數VIV冠狀動脈(冠脈)風險不高,對于VIV冠脈風險較高者可考慮使用煙囪支架、瓣葉撕裂技術(bioprosthetic or native aortic scallop intentional laceration to prevent iatrogenic coronary artery obstruction,BASILICA),對于PPM風險較大者可考慮人工瓣環斷裂技術,但長期安全性尚缺乏數據[27]。
(2)當首次手術為TAVR時,第二次手術選擇TAVR-in-TAVR或者TAVR移除后SAVR。TAVR瓣膜由于更大的結構設計而存在植入后需移除的潛在終身風險,尤其是因為冠脈遮擋風險和冠脈介入通路無法保留。在國家注冊登記數據庫中顯示,無法介入處理的大量瓣周漏、中重度PPM、感染性心內膜炎、不利的冠脈和竇部解剖結構、需進行其他心臟手術等因素導致不得不移除TAVR瓣膜(無法實施TAVR-in-TAVR)[13],而使用長支架自膨脹瓣膜可能面臨更大的TAVR移除幾率,且由于常需同時實施根部置換及其他手術,復雜且風險較大,30 d死亡率高達11%~20%,高于美國胸外科醫師協會(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評分預測死亡率[17]。因此當評估TAVR 優先策略時,與TAVR移除和TAVR-in-TAVR相關的風險是重點考慮問題,TAVR類型選擇、植入深度和最佳手術結果對于優化未來再次TAVR至關重要[9]。當長支架自膨脹TAVR出現衰敗時TAVR-in-TAVR可能是最主要選擇,應盡量避免在后期TAVR需移除風險較大的患者中初次手術選擇長支架TAVR。
(3)TAVR-in-TAVR手術技術上較為安全,除非首次TAVR為小型號,一般較少發生PPM或殘留高壓力梯度,30 d死亡和心血管不良事件率較低,小葉血栓形成率可能相對較高,長期瓣膜功能和預后尚缺乏數據[13]。然而在臨床實踐中,45.5%自膨脹瓣膜患者存在竇部封閉和冠脈堵塞風險(在各自正常的植入深度時自膨環上瓣發生率明顯高于球囊擴張瓣,高位植入雖降低傳導阻滯風險、改善瓣周漏和PPM,但增加了再次手術時冠脈阻塞風險),而球囊擴張瓣膜TAVR-in-TAVR冠脈風險僅2.0%[28]。當TAVR瓣膜交界高于竇管交界且距離竇管交界<2 mm,則認為是竇部封閉和冠脈阻塞高風險[29],并可能因此無法實施TAVR-in-TAVR。冠脈保護選擇十分有限,煙囪支架基本不可行,BASILICA操作難度也非常大,升級版的球囊輔助BASILICA、導管電外科瓣葉切除移除(CATHeter Electrosurgical Debulking and RemovAL,CATHEDRAL)技術或Leaflet Excision System瓣葉切除裝置可能帶來新的希望,外科直視下切除TAVR瓣葉后行VIV也是有效的,但應用仍十分有限[30]。因此,通過CT篩查出的竇管交界高度較低、直徑較小、瓣中瓣后竇部封閉風險較大的患者,應避免使用長支架環上瓣,盡管其存在血流動力學和耐受性優勢。
(4)TAVR人群中冠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病率約為50%,TAVR術后約10%的患者在中位25個月隨訪后因急性冠脈綜合征再入院,死亡率明顯高于未曾行TAVR的患者,占37%的死亡原因[31]。TAVR后冠脈再介入不成功發生在7.7%的患者中[32],其中大多數使用的是Evolut瓣膜(環上、高位植入導致瓣膜交界高于冠脈開口和竇管交界),而TAVR-in-TAVR后,雙層框架和高覆膜區更是限制了冠脈再介入的可能性。交界對齊越來越成為首次植入時考慮的重要問題,可能會影響瓣膜衰敗速度,甚至影響到亞臨床小葉血栓、瓣膜中心性反流的發生率[33]。小葉血栓盡管未證實與死亡或腦血管事件有關,但與瓣膜衰敗密切相關[34]。
(5)約15%~30%的主動脈瓣患者同時存在顯著二尖瓣反流或三尖瓣反流,TAVR術后目前僅觀察到大約一半患者術后二、三尖瓣反流程度降低,無改善的患者嚴重影響了長期生存率[35],因此在年輕主動脈瓣患者中評估伴隨瓣膜病的預期結局也至關重要。此外,主動脈根部擴張是否需外科手術的長期風險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6)年輕主動脈瓣患者多數都是二葉主動脈瓣,目前還缺乏關于這類患者的隨機對照試驗及耐久性數據,現有數據顯示TAVR術后的瓣周漏、永久起搏器植入、小葉血栓發生率高于SAVR[36]。
(7)主動脈瓣終身管理(≥3次手術)策略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也有所不同,一般包括SAVR-SAVR-TAVR、SAVR-TAVR-TAVR、TAVR-SAVR-TAVR、TAVR-TAVR-TAVR 4種,由于患者主動脈根部解剖條件各不相同,首次手術選擇可能會限制以后再干預選擇,各種CT后處理及虛擬瓣膜植入可模擬主瓣置換后的解剖結構,CT模擬可以預測患者一生中是否可以接受多次TAVR手術,及首次手術適合哪種類型的TAVR和植入策略[15],對于不適合進行兩次TAVR的患者推薦SAVR優先策略。
(8)最初的干預選擇對患者整個壽命有重大影響。相比而言,SAVR優先的終身管理策略(SAVR-TAVR-TAVR)相對成熟,目前證據更支持年輕患者首次手術優先考慮SAVR[9]。具體到不同根部解剖的患者而言,有以下幾種情況:① 對于瓣環較大、主動脈根部較大、沒有長期冠脈遮擋風險的患者,選擇TAVR-TAVR-TAVR似乎也合理,患者幾乎終身免于開胸,TAVR優先策略更會被考慮用于具有這類解剖結構的患者;② 對于瓣環小、根部結構大的患者,使用限位可擴張SAVR同期行瓣環擴大術可為將來VIV、瓣中瓣中瓣(valve-in-valve-in-valve,VIViV)留有充足空間,如首次行自膨脹環上瓣TAVR以優化血流動力學,可能最終到第三次手術需要面臨TAVR移除的問題;③ 對于瓣環大、根部結構小、冠脈高度足夠的患者,需考慮短支架、環內瓣甚至相對低位釋放,維持生物瓣交界或TAVR瓣膜交界不高于冠脈和竇管交界高度,以降低冠脈梗阻的發生率,否則在第二次及第三次手術中需要冠脈保護技術;④ 對于瓣環小、根部結構小、冠脈高度低的患者,首次選擇TAVR手術或二次手術TAVR-in-SAVR均會面臨較大的冠脈遮擋風險,年輕患者考慮SAVR-SAVR-TAVR可能才是最優解。
對Ross手術、AVNeo手術、根部擴大術和其他主動脈瓣成形技術的使用率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尤其在手術量大、有經驗的中心,Ross手術的圍術期和長期存活率已經非常理想,接近普通人群,高于機械瓣SAVR,更適合于<50歲患者[37-38]。
2 人工瓣膜領域
2023年瓣膜領域的新進展集中在新興瓣膜和新材料方面,多項研究公布Sutureless Perceval免縫合瓣膜的長期數據。一項德國單中心研究[39]中,Perceval應用10年隨訪結果顯示,547例患者中1.8%發生了人工瓣膜心內膜炎,19例患者接受了瓣膜再干預,平均無結構性瓣膜退變(structural valve degeneration,SVD)時間為 10.3年。一項意大利的單中心研究[40]中,1 157例患者植入Perceval瓣膜后平均5.6年內,共27例患者接受了手術再干預。一項比利時研究[41]中,Perceval應用長達15年隨訪數據顯示,1 136例患者中出現心內膜炎19 例(1.7%),發生率為0.50%/患者年,重度SVD出現28例(2.5%),發生率為0.74%/患者年,再手術干預18例(1.6%),發生率為0.48/患者年。總體上長期有效性與其他主流生物瓣相當。
INSPIRIS RESILIA主動脈干瓣已顯示出卓越的臨床結果,愛德華公司也在持續推進干瓣的商業化進程,二尖瓣位的MITRIS RESILIA于近期獲得了歐盟安全認證。從多項數據上看,一項加拿大的單中心回顧性研究[42]顯示,與MagnaEase相比,INSPIRIS組術后30個月內免于再入院率更高(94% vs. 86%,P=0.014),出院后、術后3個月、術后2年的跨瓣梯度均更低(P<0.001)。美國多中心的COMMENCE研究[43]隨訪顯示,689例患者術后5年免于SVD和免于再干預率分別為100%和98.7%,5年時有效瓣口面積為(1.6±0.5)cm2,平均梯度為(11.5±6.0)mm Hg(1 mm Hg=0.133 kPa),療效優異。COMMENCE研究5年結果和PARTNER 2A研究中的外科隊列[44]比較結果顯示,RESILIA的SVD相關的≥2級血流動力學瓣膜退化率更低(1.8% vs. 3.5%),在傾向性匹配隊列中達到統計學優效(1.0% vs. 4.8%,P=0.03)。最新納入15項研究、3 202例患者的Meta分析[45]顯示,在平均隨訪5.3年后,使用INSPIRIS RESILIA與MagnaEase死亡率和卒中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高分子聚合物瓣膜作為瓣膜市場的前沿探索方向,具備良好的耐久性和生物兼容性,但臨床試驗數據仍然非常有限。Foldax Tria主動脈瓣膜目前完成了單臂早期可行性研究[46],共納入15例受試者,隨訪1年中共出現1例考慮與瓣膜縫合環血栓有關的右冠脈栓塞,暫未出現心內膜炎或瓣膜功能障礙。Foldax也開始在印度開展人工二尖瓣的臨床研究。上海以心醫療Polymer SIKELIA瓣膜的首次人體可行性研究共在國內3家中心完成了9例植入,并于2023 TCT(Transcatheter Cardiovascular Therapeutics)會議上公布了1個月隨訪結果[47],除1例患者出現重度反流實施VIV外,其余患者術后30 d瓣膜功能良好。此外,國內還有多家聚合物外科或介入瓣膜處在臨床前階段。
組織工程瓣膜方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董念國教授團隊歷時20余年成功實現全球原創瓣膜材料細胞化技術,通過生物化學交聯技術體系獲得生物力學性能優良的瓣膜材料,研發出國際首個新型細胞化瓣膜,植入體內后自體細胞會在瓣膜材料內部生長,具有組織重塑與修復能力,不易發生鈣化衰敗,并在2023年完成了7例患者肺動脈瓣位原位植入。術后半年復查彩色超聲提示瓣膜功能良好,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顯示瓣膜表面細胞化程度良好。未來將有望實現生物材料由惰性置換向活性再生的根本性變革,推動全球生物瓣膜臨床應用迭代更新。
傳統機械瓣因其終身抗凝帶來的副作用影響,應用比例在逐年降低,已經不再是瓣膜發展主流。瑞士Novostia公司研發了一款無需終身抗凝的新型機械瓣膜Triflo valve[48],這是一款由高性能生物相容材料制成的突破性機械瓣,采用獨特的仿生理三葉瓣結構設計,具有低剪切應力和通過樞軸區域的湍流,不會產生高速回流射流,不會引發凝血反應,在保留出色的耐磨性和抗疲勞性基礎上解決了機械瓣最大的血栓問題,已在幾十頭動物實驗中證實術后1.5年無抗凝劑下沒有發生阻塞性血栓形成。Triflo valve已于2023年12月完成首例患者植入并持續推進早期可行性研究,未來有望成為年輕患者的新選擇。
3 二尖瓣領域
以二尖瓣緣對緣修復和經導管二尖瓣VIV/環中瓣為代表的二尖瓣技術徹底改變了二尖瓣外科的臨床實踐。對于退行性二尖瓣反流,盡管目前指南建議對高風險患者進行經導管緣對緣修復手術(transcatheter edge-to-edge repair,TEER),實際在中低風險患者中使用率也越來越高。目前,退行性二尖瓣反流(degenerative mitral regurgitation,DMR)患者進行外科二尖瓣修復(surgical mitral valve repair,SMVr)還是TEER的決定僅靠有限的數據和經驗,自EVERESTⅡ研究后一直缺乏高質量的對比結果,且缺乏長期預后數據。在美國,2012—2019年期間每年二尖瓣手術總量沒有明顯變化,外科手術不論置換還是修復均有下降趨勢,總體減少了1/3,取而代之的是TEER手術量快速增加,每年開展量已超過3 000例,累計超過15 000例,開展中心已超過400家[49]。美國國家臨床登記處研究[50]對年齡、虛弱和合并癥患者進行傾向性評分匹配,共篩選 4 532對DMR患者,TEER與SMVr術后3年生存率分別為65.9%和85.7%(P<0.001),心力衰竭再入院率分別為17.8%和11.2%(P<0.001),二尖瓣再介入率分別為6.1%和1.3%(P<0.001)。而在接受二尖瓣再次介入治療(TEER、手術修復或手術置換)的匹配患者中,30 d死亡率在初始TEER組為8.6%,在初始SMVr組為6.6%(P=0.59)。最近幾項對比TEER和SMVr的重磅隨機對照研究已經啟動:PRIMARY研究(NCT05051033)、MITRA-HR研究(NCT03271762)、REPAIR-MR(NCT04198870)。在TEER技術水平日益成熟的今天,這些隨機試驗評價其在高危、中危乃至低危患者中的真實療效,對于未來二尖瓣領域的醫療決策至關重要。
對于生物二尖瓣衰敗,再次二尖瓣置換術(surgical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SMVR)與經導管二尖瓣置換瓣中瓣植入術(transcatheter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valve-in-valve,TMVR-VIV)的長期預后差異的證據也比較有限。納入近10項研究的Meta分析[51]顯示,TMVR-VIV有相對更低的院內死亡率,但與SMVR相比1年死亡率無差異。一項研究[52]使用美國醫療保險隊列2016—2020年間的數據,共包括4 293例患者(redo-SMVR:64%,TMVR-VIV:36%),通過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共納入1 317對患者,TMVR-VIV與死亡和各種院內并發癥發生率較低均有關,隨訪前6個月內TMVR-VIV發生主要心血管事件(包括全因死亡、心力衰竭再住院、卒中和再干預)風險較低[adjusted HR=0.75,95%CI(0.63,0.88),P<0.001],但6個月后風險較高[adjusted HR=1.28,95%CI(1.04,1.58),P=0.02],可能與TMVR-VIV組殘余反流、更高的跨瓣梯度、三尖瓣反流曠置等有關。總體3年隨訪時二者結果均相似(44% vs. 44%),僅有二尖瓣再介入發生率TMVR-VIV組偏高[0.7% vs.1.6%,HR=2.51,95%CI(1.11,5.68),P=0.03]。另一項TMVR-VIV與SMVR對比的5年隨訪研究[53]顯示,TMVR-VIV與早期死亡率降低有關(2.4% vs. 10.2%,P=0.04),但2年死亡率和5年死亡率更高(24.5% vs. 20.7%,49.9% vs. 34.0%),但樣本量偏小(TMVR-VIV 組97例,SMVR組129例),且有明顯基線不匹配的偏倚。
4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治療選擇—微創心肌旋切術及其潛在擴展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是一種常見的可導致猝死和心力衰竭的遺傳性心肌病,據估算中國成人患者超過100萬[54],傳統治療方式包括冠脈間隔支化學消融和外科經主動脈間隔切除手術。近年來除了肌節收縮蛋白的靶向抑制藥物Mavacamten外,治療肥厚型心肌病的新型介入治療方式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經皮心肌內室間隔消融(LIWEN procedure)、經股心肌內射頻消融(DragonFire)、經右心室側室間隔脈沖消融、經股心內膜射頻消融、經冠脈射頻消融、無創精準放射消融等,共同點是通過消融能量使得室間隔基底局部心肌壞死,尤其適用于潛伏性梗阻,但對于部分患者反而易引起短期內心肌水腫導致的梗阻加重,使得其應用仍有一定的風險和限制。
由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魏翔教授團隊開發的一種新型經心尖室間隔心肌旋切術(transapical beating-heart septal myectomy,TA-BSM)成功應用于臨床,目前手術已經完成超過500例。2023年發表了其首次人體可行性研究[55]結果,47例患者器械成功率為97.9%,3個月隨訪有42例患者效果滿意,左心室流出道梯度由術前86 mm Hg降至術后3個月時的19 mm Hg,共出現1例器械無關的死亡、1例延遲性室間隔穿孔、1例心尖撕裂、1例使用永久起搏器,近期療效不劣于經主動脈間隔切除和酒精化學消融。隨后發表的TA-BSM擴大樣本的研究經驗(120例)[56],提示潛伏性梗阻或靜息性梗阻術后結果無差異。
除了切口更加微創、無需體外循環外,心肌旋切術的明顯優勢是可以實時超聲和血流動力學評估間隔切除的充分性,尤其適用于小主動脈瓣環間隔暴露不佳的兒童肥厚型心肌病患者,或先前已經進行過主動脈瓣置換的殘余梗阻患者,或術后復發性患者和不適合體外循環的孕婦患者[57-58],其創新性理念為多種臨床情況開辟了一條新的治療途徑。由于裝置易于到達中室間隔和心尖室間隔,可提供更長的切除范圍,被認為是影響切除效果的重要因素,另一個額外優勢包括肥厚型非梗阻性心肌病和心尖肥厚型心肌病患者也可能可以應用,目前正在進行相關探索并已經觀察到令人鼓舞的治療效果[59]。除心尖路徑外,旋切裝置同樣可以術中經主動脈使用,甚至升級為經股動脈介入器械。此外,還有提出是否可嘗試用于切除主動脈瓣下隔膜梗阻、右心室流出道肌肉梗阻等潛在應用場景[60]。
5 心臟移植領域
心臟移植仍然是提高終末期心力衰竭患者預后的金標準,國際心肺移植學會(ISHLT)最新報告[61]稱,2005—2017年間接受心臟移植的成年受試者在1、3、5和10年的存活率分別為85.0%~90%、79.1%、73.9%和69%。器官共享聯合網絡(UNOS)和ISHLT報告[62]稱,心臟移植成年接受者的中位生存期為13年。由于供需關系的巨大不平衡,擴大心臟捐贈者供體庫顯得至關重要,包括選擇帶有血液傳染病丙肝的供體、器官捐獻政策革新和公眾科普(由選擇加入向選擇退出政策的轉變、器官捐獻與接受互惠政策、器官捐獻受贈與法的約束而不僅是知情同意等)、拓展循環死亡后器官捐贈、基因編輯豬異種心臟移植的研究等[63-64]。
研究[65]顯示,丙型肝炎病毒陽性供體心臟移植聯合短療程直接抗病毒療法的近中期結果與丙型肝炎病毒陰性供體心臟移植相似,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治愈率為100%,沒有與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關的死亡,ISHLT也發表聲明[66]支持在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后在有治療經驗的中心使用丙型肝炎病毒血癥捐贈者的器官,主要風險在于短暫性丙型肝炎病毒血癥帶來的較高的急性細胞排斥反應(31%)和較低的短療程直接抗病毒療法不耐受率(<2%)[67-68]。
自2014年恢復循環死亡供體心臟移植以來,已實施超過500例心臟移植,先后在澳大利亞、英國、美國等數十個國家進行研究和應用。多項回顧性研究[69-71]顯示,腦死亡和循環死亡供心移植的機械循環支持率和支持時間、住院時間、排斥反應發生率、30 d生存率、1年和5年生存率均無差異,短期內移植物功能障礙發生率并無顯著升高。2023年美國胸外科協會(AATS)發布了循環死亡供心的成人心臟移植專家共識[72],以推動這一領域的規范發展。同時中國醫師協會器官移植醫師分會、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也聯合發布了《中國心臟死亡捐獻器官評估與應用專家共識(2022版)》[73],以更科學、規范地指導循環死亡器官捐獻的評估與應用。然而在真正普及前還需解決很多問題,包括循環死亡定義和評估標準、醫學倫理問題、立法制定規則等。
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進步,異種移植重新引起科學家的巨大興趣。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使用CRISPR-Cas9技術創建了10基因編輯豬(敲除αGal、NeuGc、B4Gal 3種最常見異種免疫表位基因,敲除編碼豬生長激素受體GHR基因以抑制移植物過度生長,插入兩個人類基因CD46和CD55以上調其表達,抑制補體級聯激活,插入人類編碼內皮蛋白C受體和血栓調節蛋白的PROCR和THBD基因來控制凝血紊亂,插入白細胞表面抗原CD47和血紅素加氧酶1基因以上調參與抗炎和免疫抑制途徑的基因表達)[74],成功克服了超急性排斥反應屏障,但免疫抑制和急性排斥反應(移植后數周至數月)尚未全部解決,包括抗體介導的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同時還需要滅活或消除豬細胞中的人畜共患病原體(豬內源性逆轉錄病毒、豬巨細胞病毒等)。2022年1月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成功對1 例57歲患者進行了首例10-GE豬-人心臟異種移植[75],然而在第49天出現了嚴重舒張性心力衰竭,第56天心內膜心肌活檢顯示病理性抗體介導的排斥,40%的心肌細胞壞死,異種移植物最終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損傷并在第60天死亡,尸檢結果顯示與典型的異種移植排斥不符,同時檢測到的豬巨細胞病毒推測可能對心臟移植產生破壞性影響[76]。在團隊改良了感染的預防措施,并且嘗試使用新的實驗性抗體以阻斷 CD154抗體介導的免疫排斥反應,2023年9月在1 例58歲晚期心臟病患者上實施了第2例豬心移植,不幸的是術后第40天仍然因為排斥反應而死亡[77]。異種心臟移植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遠。
另一方面,終末期心力衰竭常伴隨腎或肝功能障礙,會對單純心臟移植構成障礙,對迫切需要對心腎聯合移植和心肝聯合移植需求更加明顯,適當分配這一稀缺資源至關重要,同時需要對其進行明確的指導。2023年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發布了科學聲明[78]闡述心-腎和心-肝雙器官移植的適應證、評估和結果,探討腎和肝功能障礙的評估和對結局的潛在影響,并詳細梳理了患者選擇、圍術期管理和倫理問題。
6 左心室輔助領域
隨著第三代左心室輔助裝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治療效果不斷提升[79],以及適應證由中短期橋接移植向長期的邁進,中國已經進入LVAD時代,5種上市的心室輔助裝置(重慶永仁心EVAHEART 1、EVA-Pulsa,蘇州同心CH-VAD,天津航天泰心HeartCon,深圳核心Corheart 6)均在緊鑼密鼓地推動商業化進程,全國已有85家醫院完成超過500例植入,16家醫院完成10例以上,且國產裝置更好的體積、重量和性能也保障了臨床的易用性和療效,搏動性血流、流量自調節功能、生物相容性涂層等功能也更好地適應人體生理需求。2023年中國心室輔助裝置專家共識委員會發布了《中國左心室輔助裝置候選者術前評估與管理專家共識(2023年)》[80],四川省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會心臟重癥與輔助支持專業委員會等發布了《左心室輔助裝置植入全程管理專家共識(2023年)》[81],系統總結了 LVAD 的適應證與禁忌證、手術時機選擇、術前評估、術前狀態優化等最新認識及規范,以期指導臨床對此新療法的規范化應用,并在技術培訓、圍術期管理、質量控制、術后右心心力衰竭防治、康復訓練和護理、心理支持、病例注冊登記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開展。同時借鑒近期發布的美國心力衰竭學會(Heart Failure Society of America,HFSA)關于持久機械循環支持患者醫療管理的專家共識聲明[82]、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心力衰竭協會/歐洲心律協會心力衰竭患者植入式裝置治療融合管理的臨床共識聲明[83]、持久性機械循環支持JACC科學聲明[84]、ISHLT/HFSA急性機械循環支持指南[85]、ESC心力衰竭協會LVAD合并右心力衰竭的術前、術中和術后管理策略臨床共識聲明[86]、2023年ISHLT機械循環支持指南10年更新[87]等文件,推動我國LVAD行業平穩健康發展。
7 冠脈外科領域
2023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HA等6個學會聯合發布了慢性冠脈疾病指南[88],遭到AATS和STS的強烈抗議,尤其反對對三支血管病變患者搭橋手術推薦級別的降低[89],他們認為這版指南與2021年指南一樣沒有將治療推薦與現有最佳循證醫學證據相結合。與此同時,近期先后發布了ESC/歐洲心胸外科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EACTS)左主干冠脈疾病血運重建的指南建議[90]、EACTS/STS冠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導管選擇的專家評價[91],重申CABG在左主干病變的首選地位和證據級別,以及對橋血管類型選擇進行了系統闡述。CABG在復雜冠脈病變中逐年增多的臨床證據也顯示了其無可置疑的基石地位。近期的研究結果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左主干病變:最新Meta分析[92]綜合了目前最大的4項隨機對照研究(SYNTAX、PRECOMBAT、NOBLE和EXCEL),顯示無論是否合并急性冠脈綜合征狀態,患者在冠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或CABG術后5年死亡率無顯著差別,PCI術后再發心肌梗死和再次血運重建發生率高于CABG。然而另一項SWEDEHEART注冊登記研究[93]的真實世界數據顯示,在校正混雜因素后,PCI患者較CABG患者死亡風險更高、主要不良心腦血管事件(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新發血運重建)風險也更高。
(2)三支血管病變:FAME 3研究比較血流儲備分數指導PCI與CABG的臨床預后,1年隨訪結果PCI組主要終點(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再次血運重建的復合終點)發生率高于CABG組(10.6% vs. 6.9%)[94],3年隨訪結果依然如此(18.6% vs. 12.5%)[95],主要體現在死亡與卒中風險兩組間無差異,而心肌梗死和再次血運重建風險PCI組更高。CABG總體優于PCI,并優于藥物治療。
(3)射血分數低下的缺血性心肌病:在此前STICH研究[95]中,CABG聯合藥物治療較單純藥物治療可進一步降低射血分數低下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遠期死亡率,而REVIVED-BCIS2研究[96]中,PCI未能較單純藥物治療進一步降低射血分數低下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率和心力衰竭再住院率。迄今為止,尚無頭對頭比較CABG和PCI治療缺血性心力衰竭的隨機對照研究,STICH國際研究聯盟正在開展。近期報道的以英格蘭地區真實世界臨床數據使用計算機技術比較CABG和PCI的模擬隨機對照研究[97],在校正混雜因素后,CABG組較PCI組5年死亡和心力衰竭再住院復合終點發生率降低16.2%,確認CABG是治療這類患者的首選策略。
(4)橋血管選擇:CABG中至少選擇1根動脈橋已被證實具有更大的生存獲益,而左乳內-前降支橋基礎上,其他橋血管類型的最佳選擇一直缺少證據。RAPCO研究[98]是第一個證實橈動脈橋超遠期臨床結局優于右乳內或大隱靜脈橋的隨機對照試驗,遠期臨床獲益(主要心血管事件終點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和再次血運重建)在術后5年內差距不明顯,到術后15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橈動脈 vs. 右乳內,P=0.04;橈動脈 vs. 大隱靜脈,P=0.04);在接受1根動脈橋的基礎上,不同術者對大隱靜脈橋的使用數量習慣各異,一項美國的多中心研究[99]顯示,保守組(使用1~2根靜脈橋)與積極組(使用3~4根靜脈橋)的15年長期生存率沒有差異。
8 慢性心力衰竭的心臟結構干預手段
藥物治療一直以來都是慢性心力衰竭治療的基石,對于終末期心力衰竭和無法控制的急性失代償心力衰竭,短期或中長期機械輔助的循環替代治療已成為臨床診療共識。而對于尚未進入晚期的慢性心力衰竭,單純藥物治療尚不能全部滿足臨床治療需求,非藥物/器械治療前景仍十分廣闊,一眾從不同機制改善心力衰竭的非藥物/器械手段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本文主要關注結構干預療法在當前臨床實踐中治療心力衰竭的作用。
在外科治療中,梅奧醫院最新報道了一種心包切除術治療射血分數保留的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HFpEF)的早期臨床研究(n=4)[100],這一手段是基于HFpEF的病理生理機制之一—左心室高充盈壓部分由心包介導的心臟外在約束引起,運動時更為顯著。初步結果顯示,與術前心包完整時相比,即刻的容量負荷試驗后肺毛細血管楔壓(pulmonary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PCWP)上升幅度明顯下降[ΔPCWP (4±4)mm Hg vs.(9±2)mm Hg],且絕對值更低[(16±6)mm Hg vs.(21±4)mm Hg];在3個月和6個月隨訪時堪薩斯城心肌病問卷評分和峰值耗氧量較術前顯著增加。該研究中所觀察到的積極信號提示了這種非植入物理治療方式的潛在有效性,筆者推測另一個可能的潛在機制:心室可通過直接與胸壁粘連而借助胸廓呼吸運動來改善室壁順應性。需要繼續關注更大樣本量的隨機對照研究。
AccuCinch是一種經導管左心室修復系統,使用一系列錨定點對左心室基底部進行環縮,其治療機制是通過縮小左心室容積降低心肌壁應力,從而使左心室逆向重塑而改善心力衰竭。AccuCinch早在2016年即開始進行包括治療二尖瓣反流、擴張性心肌病在內的一系列臨床研究,并逐漸轉移到以治療射血分數降低的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HFrEF)為主。對于先前參與研究的無二尖瓣反流>2+的HFrEF患者,2023年首次發表了1年隨訪結果[101],共51例患者接受了經導管左心室修復,僅1例因左心室瘢痕而中止手術,手術即刻顯示左心室游離壁半徑平均減少9.2 mm,12個月隨訪顯示左心室舒張末期容積減少(33.6±34.8)mL,紐約心臟協會心功能分級、堪薩斯城心肌病問卷總分和6分鐘步行距離有顯著改善,隨訪期內僅1例死亡、1例接受左心輔助。進一步的隨機對照研究(NCT04331769)目前仍在患者招募中(n=400)。
心房分流術是另一項備受關注的新技術手段,第二項重磅隨機雙盲對照RELIEVE-HF研究[102]近期于美國心血管病學會年會上公布,出乎意料的結果引起了業內廣泛討論。該研究使用的是內徑5.1 mm沙漏狀Ventura房間隔分流器,508例患者在中位隨訪22個月后,整個隊列的主要終點并無顯著差異。但在HFrEF組亞組分析中,分流組(101例)較假手術組(108例)在年事件率顯示出優效性差異(49.0% vs. 88.6%,HR=0.55,P<0.000 1),尤其在心力衰竭再住院事件上改善最為顯著(26.0%/年 vs. 52.0%/年,HR=0.52,P=0.01);在HFpEF組亞組分析中,分流組(149例)較假手術組(153例)年事件發生率高(60.2% vs. 35.9%,HR=1.68,P=
9 主動脈夾層領域
近年來主動脈夾層的發病率及內外科治療呈快速增長態勢,對主動脈病理及發展機制也不斷有新的認識。盡管2022年ACC/AHA主動脈疾病的診斷和管理指南[103]和2024年EACTS/STS主動脈急性和慢性綜合征的診斷與治療指南[104]仍然以主動脈直徑≥5.5 cm為Ⅰ期、≥5.0 cm為Ⅱa期的手術干預推薦,新的研究仍在推進預防性升主動脈瘤干預指征前移的問題。耶魯大學團隊研究[105]發現,升主動脈直徑≥5 cm時患者發生急性事件風險迅速增加,當主動脈尺寸為3.5~3.9 cm、4.0~4.4 cm、4.5~4.9 cm、5.0~5.4 cm、5.5~5.9 cm和≥6.0 cm時,發生主動脈事件的年平均風險分別為0.2%、0.2%、0.3%、1.4%、2.0%和3.5%,10年無事件生存率分別為97.8%、98.2%、97.3%、84.6%、80.4%和70.9%,并建議將升主動脈瘤修復手術閾值從5.5 cm降低至5.0 cm。廣東省人民醫院團隊研究[106]認為,反映形態學的升主動脈容積是更好的風險預測指標,而不能僅關注升主動脈最大直徑、直徑增長率、長度指標。此外,升動脈瘤手術需要將年齡、遺傳病、家族史、糖尿病等各種因素納入決策中。
A型主動脈夾層血管內治療的應用一直以來受到缺乏合適的近端著陸區、存在明顯主動脈反流和心臟壓塞的限制,Endo-Bentall血管內瓣膜導管早在2014年就已被提出[107],已有一些病例報告和小系列隊列研究,主要是預期死亡風險較高的(如老年、多合并癥、神志不清、末端器官灌注不良)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解剖適應證標準相對較嚴格,可行性通常在40%以下。隨著血管內修復器械不斷更新和改進,更安全、解剖適應證更寬的產品不斷面世。郭偉教授及其團隊提出了新型模塊化Endo-Bentall系統并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植入,其包含了兩側冠脈內分支、冠脈重建支架和帶連接段支架介入主動脈瓣的全覆膜支架,且評估認為66.4%的A型夾層具有其解剖適應性,更適合主動脈根部內膜撕裂的患者。
10 心房顫動的外科綜合治療
2023年亞太心律協會發表了關于心房顫動(房顫)手術的專家共識聲明[108],在伴或不伴結構性心臟病的房顫手術治療中詳細敘述了目前的證據和建議。對于需打開或無需打開左心房的心臟外科手術的房顫患者,建議進行外科房顫消融(Ⅰ,B)。對于單純房顫患者,在仔細考慮安全性和有效性后,對于一次或多次導管消融失敗的患者,左心房擴張或藥物治療不耐受或難治性患者,應考慮采用微創胸腔鏡方法進行單獨的外科消融(Ⅱa,b)。癥狀性房顫患者應考慮外科消融、左心耳閉合聯合導管消融的復合雜交手術(Ⅱa,b)。當沒有迷宮手術或其他控制節律手術指征時(如嚴重左心房擴張、房顫持續時間長、預計無法轉復、手術時間長可能增加手術風險或影響術后恢復),推薦合并房顫的患者在實施體外循環或非體外循環手術時同期關閉左心耳(Ⅰ,A)。對于血栓栓塞或出血風險高的房顫患者,盡管有最佳的抗凝治療但不適用于經皮左心耳封堵時,建議采用胸腔鏡左心耳關閉術(Ⅱa,B)。
目前尚無足夠證據支持,指南暫不建議在常規心臟手術期間對非房顫患者進行預防性左心耳封堵,但盡管如此在心臟外科臨床實踐中已經比較廣泛地對老年、合并左心力衰竭和左心房擴大、合并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等房顫高危患者中進行預防性左心耳關閉。對于持續性或長期持續性房顫患者則更優先考慮內外科聯合消融+左心耳閉合的混合雜交手術,尤其是當抗心律失常藥物和基于導管的消融失敗時。基于目前的指南建議,將單純房顫外科消融的適應證應用于混合消融可能是合理的。近期JACC雜志上發表了對于混合雜交房顫手術目前的證據[109],盡管風險比導管消融更高,但更徹底完善的透壁消融可進一步提高轉復成功率并降低復發率。外科選擇方式有包含左心房頂到左心房底連接線的肺靜脈隔離、左心房后壁消融、后壁盒式病變消融,或是直接Cox-Maze手術,然后進行左心耳縫閉、導管消融程序。納入10余項隨機和非隨機研究的Meta分析[109]顯示,達到研究主要終點免于房性心律失常復發(910/1 241)的患者比例為0.75[95%CI(0.69,0.81)],選擇內外科分期消融和同期混合消融的成功率分別為0.83[95%CI(0.68,0.94),348/454]和0.71[95%CI(0.68,0.74),562/787]。進一步比較混合消融與導管消融的隨機對照試驗仍在進行中(HARTCAP-AF:NCT02441738;CEASE-AF:NCT02695277;HALT-AF:NCT05411614)。
11 總結與展望
作為醫療領域金字塔尖的學科,心血管外科乃至整個心血管領域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得益于國內外眾多創新與轉化項目的涌現,尤其是顛覆性生物材料、原創性醫療器械與突破性新技術,給心外科發展帶來了機遇和希望。許多醫學創新從醫生中來,由醫工結合共同實現,并最終服務于醫生和患者,未來技術發展也必然沿著這條醫學轉化大道不斷前行。同時,高質量的臨床研究也在不斷更新或者挑戰過去的治療理念,需要廣大心血管同行不斷參與和持續學習,以促進學科和個人發展,推動我國心血管外科事業的不斷前進。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張長東負責文獻檢索、文章撰寫;尚小珂負責選題設計、思路分析、文章撰寫;鐘禹成負責資料整理和潤色校對;董念國負責審閱和提出指導意見。
近年來,心血管外科領域經歷了深刻的變革和飛速的發展,取得了多項突破性進展,為患者的健康和福祉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正如每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機遇與挑戰總是并存。新技術的層出不窮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希望,同時也對過去的理念提出了挑戰。本文旨在全面概述近年來,尤其是2023年以來心血管外科的最新進展,介紹心血管外科領域的前沿知識和技術,并深入分析和探討未來的發展方向。
1 主動脈瓣疾病的終身管理
經導管主動脈瓣置換術(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TAVR)適應證覆蓋全部高、中、低風險人群,乃至無癥狀人群[1]。TAVR技術不斷成熟,安全性指標包括死亡、致殘性卒中的數據已開始顯露出優于外科主動脈瓣置換(surgical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SAVR)的趨勢[2]。NOTION等研究[3-4]10年隨訪證實TAVR耐久性可能優于SAVR,經導管瓣中瓣(valve-in-valve,VIV)技術成熟也使得外科醫生認可的生物瓣應用年齡不斷下探[5-6]。年輕(<65歲)主動脈瓣病變患者在首次接受手術時實施TAVR還是SAVR?盡管從未在隨機對照試驗中驗證,但臨床實踐一直在推動TAVR在越來越年輕的患者中應用[7],低齡化即將成為必然。在預期壽命不斷增長的人群中制定終身管理策略,對于在生命各個階段實現主動脈瓣疾病治療的最佳結果至關重要[8-10]。患者的終身管理需要考慮一系列問題,沒有一種策略適合所有患者。最佳策略應根據患者選擇、合并疾病進展、術者經驗、根部解剖特征、設備技術特點進行個性化定制,全面的管理計劃需持續到術后20年以上[11-16]。首次瓣膜類型選擇幾乎為后續治療方案選擇定下了基調,再次手術的風險和效果是主要考量因素,如何保持首次及后續歷次手術人工瓣膜更優化的血流動力學,尤其是對小瓣環和假體-患者不匹配(prosthesis-patient mismatch,PPM)風險較大者,這些復雜問題及決策將在未來心臟團隊術前討論和患者溝通中變得更為普遍[17-21]。
目前廣泛的臨床研究已經得出較為明確的結論,包括:(1)PPM是加速瓣膜衰敗、引起長期預后不良的顯著危險因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容忍PPM,而環內瓣膜與PPM風險增加相關[22],因此小瓣環患者應該盡量避免使用環內瓣膜;現有研究[23]顯示SAVR聯合根部擴大術顯著降低了PPM的風險,且與單純SAVR手術相比近期和長期預后相當。近年來也出現了更為簡化、安全的根部擴大方法[24],因此對初次手術患者實施必要的根部擴大術以適應未來VIV的需要(包括降低VIV后PPM發生率)可能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當首次手術為SAVR時,第二次手術選擇VIV還是redo-SAVR的對比研究[25]中,VIV近期死亡率、卒中和大出血風險更低(redo-SAVR圍術期死亡率為3%~8%),VIV的PPM和小葉血栓風險更大,心力衰竭再住院率更高,尤其是使用球囊擴張瓣膜時。VIV相比redo-SAVR的早期獲益在1.5年后交叉并顯著減弱,整體上二者長期預后無明顯差異[26]。因此,瓣口面積更大的自膨脹瓣膜是TAVR VIV的首選,而對于首次SAVR的瓣膜選擇也有著潛在影響,19#、21#瓣膜使用將越來越少,盡可能大號的、支架可斷裂的牛心包支架內瓣膜、限位可擴張干瓣、免縫合瓣等類型的使用率均可能上升,以盡可能提高耐久性。Edwards Perimount瓣膜術后20年瓣膜衰敗風險為30%±3%,特定年齡組耐久性總體預測為19年,已被視為瓣膜耐久性的參照標準[11]。對于首次使用小號生物瓣的年輕SAVR患者,鑒于長期結局仍更推薦redo-SAVR。由于市面上大多數生物瓣使用的是支架內瓣膜,多數VIV冠狀動脈(冠脈)風險不高,對于VIV冠脈風險較高者可考慮使用煙囪支架、瓣葉撕裂技術(bioprosthetic or native aortic scallop intentional laceration to prevent iatrogenic coronary artery obstruction,BASILICA),對于PPM風險較大者可考慮人工瓣環斷裂技術,但長期安全性尚缺乏數據[27]。
(2)當首次手術為TAVR時,第二次手術選擇TAVR-in-TAVR或者TAVR移除后SAVR。TAVR瓣膜由于更大的結構設計而存在植入后需移除的潛在終身風險,尤其是因為冠脈遮擋風險和冠脈介入通路無法保留。在國家注冊登記數據庫中顯示,無法介入處理的大量瓣周漏、中重度PPM、感染性心內膜炎、不利的冠脈和竇部解剖結構、需進行其他心臟手術等因素導致不得不移除TAVR瓣膜(無法實施TAVR-in-TAVR)[13],而使用長支架自膨脹瓣膜可能面臨更大的TAVR移除幾率,且由于常需同時實施根部置換及其他手術,復雜且風險較大,30 d死亡率高達11%~20%,高于美國胸外科醫師協會(Society of Thoracic Surgeons,STS)評分預測死亡率[17]。因此當評估TAVR 優先策略時,與TAVR移除和TAVR-in-TAVR相關的風險是重點考慮問題,TAVR類型選擇、植入深度和最佳手術結果對于優化未來再次TAVR至關重要[9]。當長支架自膨脹TAVR出現衰敗時TAVR-in-TAVR可能是最主要選擇,應盡量避免在后期TAVR需移除風險較大的患者中初次手術選擇長支架TAVR。
(3)TAVR-in-TAVR手術技術上較為安全,除非首次TAVR為小型號,一般較少發生PPM或殘留高壓力梯度,30 d死亡和心血管不良事件率較低,小葉血栓形成率可能相對較高,長期瓣膜功能和預后尚缺乏數據[13]。然而在臨床實踐中,45.5%自膨脹瓣膜患者存在竇部封閉和冠脈堵塞風險(在各自正常的植入深度時自膨環上瓣發生率明顯高于球囊擴張瓣,高位植入雖降低傳導阻滯風險、改善瓣周漏和PPM,但增加了再次手術時冠脈阻塞風險),而球囊擴張瓣膜TAVR-in-TAVR冠脈風險僅2.0%[28]。當TAVR瓣膜交界高于竇管交界且距離竇管交界<2 mm,則認為是竇部封閉和冠脈阻塞高風險[29],并可能因此無法實施TAVR-in-TAVR。冠脈保護選擇十分有限,煙囪支架基本不可行,BASILICA操作難度也非常大,升級版的球囊輔助BASILICA、導管電外科瓣葉切除移除(CATHeter Electrosurgical Debulking and RemovAL,CATHEDRAL)技術或Leaflet Excision System瓣葉切除裝置可能帶來新的希望,外科直視下切除TAVR瓣葉后行VIV也是有效的,但應用仍十分有限[30]。因此,通過CT篩查出的竇管交界高度較低、直徑較小、瓣中瓣后竇部封閉風險較大的患者,應避免使用長支架環上瓣,盡管其存在血流動力學和耐受性優勢。
(4)TAVR人群中冠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病率約為50%,TAVR術后約10%的患者在中位25個月隨訪后因急性冠脈綜合征再入院,死亡率明顯高于未曾行TAVR的患者,占37%的死亡原因[31]。TAVR后冠脈再介入不成功發生在7.7%的患者中[32],其中大多數使用的是Evolut瓣膜(環上、高位植入導致瓣膜交界高于冠脈開口和竇管交界),而TAVR-in-TAVR后,雙層框架和高覆膜區更是限制了冠脈再介入的可能性。交界對齊越來越成為首次植入時考慮的重要問題,可能會影響瓣膜衰敗速度,甚至影響到亞臨床小葉血栓、瓣膜中心性反流的發生率[33]。小葉血栓盡管未證實與死亡或腦血管事件有關,但與瓣膜衰敗密切相關[34]。
(5)約15%~30%的主動脈瓣患者同時存在顯著二尖瓣反流或三尖瓣反流,TAVR術后目前僅觀察到大約一半患者術后二、三尖瓣反流程度降低,無改善的患者嚴重影響了長期生存率[35],因此在年輕主動脈瓣患者中評估伴隨瓣膜病的預期結局也至關重要。此外,主動脈根部擴張是否需外科手術的長期風險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6)年輕主動脈瓣患者多數都是二葉主動脈瓣,目前還缺乏關于這類患者的隨機對照試驗及耐久性數據,現有數據顯示TAVR術后的瓣周漏、永久起搏器植入、小葉血栓發生率高于SAVR[36]。
(7)主動脈瓣終身管理(≥3次手術)策略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也有所不同,一般包括SAVR-SAVR-TAVR、SAVR-TAVR-TAVR、TAVR-SAVR-TAVR、TAVR-TAVR-TAVR 4種,由于患者主動脈根部解剖條件各不相同,首次手術選擇可能會限制以后再干預選擇,各種CT后處理及虛擬瓣膜植入可模擬主瓣置換后的解剖結構,CT模擬可以預測患者一生中是否可以接受多次TAVR手術,及首次手術適合哪種類型的TAVR和植入策略[15],對于不適合進行兩次TAVR的患者推薦SAVR優先策略。
(8)最初的干預選擇對患者整個壽命有重大影響。相比而言,SAVR優先的終身管理策略(SAVR-TAVR-TAVR)相對成熟,目前證據更支持年輕患者首次手術優先考慮SAVR[9]。具體到不同根部解剖的患者而言,有以下幾種情況:① 對于瓣環較大、主動脈根部較大、沒有長期冠脈遮擋風險的患者,選擇TAVR-TAVR-TAVR似乎也合理,患者幾乎終身免于開胸,TAVR優先策略更會被考慮用于具有這類解剖結構的患者;② 對于瓣環小、根部結構大的患者,使用限位可擴張SAVR同期行瓣環擴大術可為將來VIV、瓣中瓣中瓣(valve-in-valve-in-valve,VIViV)留有充足空間,如首次行自膨脹環上瓣TAVR以優化血流動力學,可能最終到第三次手術需要面臨TAVR移除的問題;③ 對于瓣環大、根部結構小、冠脈高度足夠的患者,需考慮短支架、環內瓣甚至相對低位釋放,維持生物瓣交界或TAVR瓣膜交界不高于冠脈和竇管交界高度,以降低冠脈梗阻的發生率,否則在第二次及第三次手術中需要冠脈保護技術;④ 對于瓣環小、根部結構小、冠脈高度低的患者,首次選擇TAVR手術或二次手術TAVR-in-SAVR均會面臨較大的冠脈遮擋風險,年輕患者考慮SAVR-SAVR-TAVR可能才是最優解。
對Ross手術、AVNeo手術、根部擴大術和其他主動脈瓣成形技術的使用率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尤其在手術量大、有經驗的中心,Ross手術的圍術期和長期存活率已經非常理想,接近普通人群,高于機械瓣SAVR,更適合于<50歲患者[37-38]。
2 人工瓣膜領域
2023年瓣膜領域的新進展集中在新興瓣膜和新材料方面,多項研究公布Sutureless Perceval免縫合瓣膜的長期數據。一項德國單中心研究[39]中,Perceval應用10年隨訪結果顯示,547例患者中1.8%發生了人工瓣膜心內膜炎,19例患者接受了瓣膜再干預,平均無結構性瓣膜退變(structural valve degeneration,SVD)時間為 10.3年。一項意大利的單中心研究[40]中,1 157例患者植入Perceval瓣膜后平均5.6年內,共27例患者接受了手術再干預。一項比利時研究[41]中,Perceval應用長達15年隨訪數據顯示,1 136例患者中出現心內膜炎19 例(1.7%),發生率為0.50%/患者年,重度SVD出現28例(2.5%),發生率為0.74%/患者年,再手術干預18例(1.6%),發生率為0.48/患者年。總體上長期有效性與其他主流生物瓣相當。
INSPIRIS RESILIA主動脈干瓣已顯示出卓越的臨床結果,愛德華公司也在持續推進干瓣的商業化進程,二尖瓣位的MITRIS RESILIA于近期獲得了歐盟安全認證。從多項數據上看,一項加拿大的單中心回顧性研究[42]顯示,與MagnaEase相比,INSPIRIS組術后30個月內免于再入院率更高(94% vs. 86%,P=0.014),出院后、術后3個月、術后2年的跨瓣梯度均更低(P<0.001)。美國多中心的COMMENCE研究[43]隨訪顯示,689例患者術后5年免于SVD和免于再干預率分別為100%和98.7%,5年時有效瓣口面積為(1.6±0.5)cm2,平均梯度為(11.5±6.0)mm Hg(1 mm Hg=0.133 kPa),療效優異。COMMENCE研究5年結果和PARTNER 2A研究中的外科隊列[44]比較結果顯示,RESILIA的SVD相關的≥2級血流動力學瓣膜退化率更低(1.8% vs. 3.5%),在傾向性匹配隊列中達到統計學優效(1.0% vs. 4.8%,P=0.03)。最新納入15項研究、3 202例患者的Meta分析[45]顯示,在平均隨訪5.3年后,使用INSPIRIS RESILIA與MagnaEase死亡率和卒中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高分子聚合物瓣膜作為瓣膜市場的前沿探索方向,具備良好的耐久性和生物兼容性,但臨床試驗數據仍然非常有限。Foldax Tria主動脈瓣膜目前完成了單臂早期可行性研究[46],共納入15例受試者,隨訪1年中共出現1例考慮與瓣膜縫合環血栓有關的右冠脈栓塞,暫未出現心內膜炎或瓣膜功能障礙。Foldax也開始在印度開展人工二尖瓣的臨床研究。上海以心醫療Polymer SIKELIA瓣膜的首次人體可行性研究共在國內3家中心完成了9例植入,并于2023 TCT(Transcatheter Cardiovascular Therapeutics)會議上公布了1個月隨訪結果[47],除1例患者出現重度反流實施VIV外,其余患者術后30 d瓣膜功能良好。此外,國內還有多家聚合物外科或介入瓣膜處在臨床前階段。
組織工程瓣膜方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董念國教授團隊歷時20余年成功實現全球原創瓣膜材料細胞化技術,通過生物化學交聯技術體系獲得生物力學性能優良的瓣膜材料,研發出國際首個新型細胞化瓣膜,植入體內后自體細胞會在瓣膜材料內部生長,具有組織重塑與修復能力,不易發生鈣化衰敗,并在2023年完成了7例患者肺動脈瓣位原位植入。術后半年復查彩色超聲提示瓣膜功能良好,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顯示瓣膜表面細胞化程度良好。未來將有望實現生物材料由惰性置換向活性再生的根本性變革,推動全球生物瓣膜臨床應用迭代更新。
傳統機械瓣因其終身抗凝帶來的副作用影響,應用比例在逐年降低,已經不再是瓣膜發展主流。瑞士Novostia公司研發了一款無需終身抗凝的新型機械瓣膜Triflo valve[48],這是一款由高性能生物相容材料制成的突破性機械瓣,采用獨特的仿生理三葉瓣結構設計,具有低剪切應力和通過樞軸區域的湍流,不會產生高速回流射流,不會引發凝血反應,在保留出色的耐磨性和抗疲勞性基礎上解決了機械瓣最大的血栓問題,已在幾十頭動物實驗中證實術后1.5年無抗凝劑下沒有發生阻塞性血栓形成。Triflo valve已于2023年12月完成首例患者植入并持續推進早期可行性研究,未來有望成為年輕患者的新選擇。
3 二尖瓣領域
以二尖瓣緣對緣修復和經導管二尖瓣VIV/環中瓣為代表的二尖瓣技術徹底改變了二尖瓣外科的臨床實踐。對于退行性二尖瓣反流,盡管目前指南建議對高風險患者進行經導管緣對緣修復手術(transcatheter edge-to-edge repair,TEER),實際在中低風險患者中使用率也越來越高。目前,退行性二尖瓣反流(degenerative mitral regurgitation,DMR)患者進行外科二尖瓣修復(surgical mitral valve repair,SMVr)還是TEER的決定僅靠有限的數據和經驗,自EVERESTⅡ研究后一直缺乏高質量的對比結果,且缺乏長期預后數據。在美國,2012—2019年期間每年二尖瓣手術總量沒有明顯變化,外科手術不論置換還是修復均有下降趨勢,總體減少了1/3,取而代之的是TEER手術量快速增加,每年開展量已超過3 000例,累計超過15 000例,開展中心已超過400家[49]。美國國家臨床登記處研究[50]對年齡、虛弱和合并癥患者進行傾向性評分匹配,共篩選 4 532對DMR患者,TEER與SMVr術后3年生存率分別為65.9%和85.7%(P<0.001),心力衰竭再入院率分別為17.8%和11.2%(P<0.001),二尖瓣再介入率分別為6.1%和1.3%(P<0.001)。而在接受二尖瓣再次介入治療(TEER、手術修復或手術置換)的匹配患者中,30 d死亡率在初始TEER組為8.6%,在初始SMVr組為6.6%(P=0.59)。最近幾項對比TEER和SMVr的重磅隨機對照研究已經啟動:PRIMARY研究(NCT05051033)、MITRA-HR研究(NCT03271762)、REPAIR-MR(NCT04198870)。在TEER技術水平日益成熟的今天,這些隨機試驗評價其在高危、中危乃至低危患者中的真實療效,對于未來二尖瓣領域的醫療決策至關重要。
對于生物二尖瓣衰敗,再次二尖瓣置換術(surgical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SMVR)與經導管二尖瓣置換瓣中瓣植入術(transcatheter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valve-in-valve,TMVR-VIV)的長期預后差異的證據也比較有限。納入近10項研究的Meta分析[51]顯示,TMVR-VIV有相對更低的院內死亡率,但與SMVR相比1年死亡率無差異。一項研究[52]使用美國醫療保險隊列2016—2020年間的數據,共包括4 293例患者(redo-SMVR:64%,TMVR-VIV:36%),通過傾向性評分匹配分析,共納入1 317對患者,TMVR-VIV與死亡和各種院內并發癥發生率較低均有關,隨訪前6個月內TMVR-VIV發生主要心血管事件(包括全因死亡、心力衰竭再住院、卒中和再干預)風險較低[adjusted HR=0.75,95%CI(0.63,0.88),P<0.001],但6個月后風險較高[adjusted HR=1.28,95%CI(1.04,1.58),P=0.02],可能與TMVR-VIV組殘余反流、更高的跨瓣梯度、三尖瓣反流曠置等有關。總體3年隨訪時二者結果均相似(44% vs. 44%),僅有二尖瓣再介入發生率TMVR-VIV組偏高[0.7% vs.1.6%,HR=2.51,95%CI(1.11,5.68),P=0.03]。另一項TMVR-VIV與SMVR對比的5年隨訪研究[53]顯示,TMVR-VIV與早期死亡率降低有關(2.4% vs. 10.2%,P=0.04),但2年死亡率和5年死亡率更高(24.5% vs. 20.7%,49.9% vs. 34.0%),但樣本量偏小(TMVR-VIV 組97例,SMVR組129例),且有明顯基線不匹配的偏倚。
4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治療選擇—微創心肌旋切術及其潛在擴展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是一種常見的可導致猝死和心力衰竭的遺傳性心肌病,據估算中國成人患者超過100萬[54],傳統治療方式包括冠脈間隔支化學消融和外科經主動脈間隔切除手術。近年來除了肌節收縮蛋白的靶向抑制藥物Mavacamten外,治療肥厚型心肌病的新型介入治療方式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經皮心肌內室間隔消融(LIWEN procedure)、經股心肌內射頻消融(DragonFire)、經右心室側室間隔脈沖消融、經股心內膜射頻消融、經冠脈射頻消融、無創精準放射消融等,共同點是通過消融能量使得室間隔基底局部心肌壞死,尤其適用于潛伏性梗阻,但對于部分患者反而易引起短期內心肌水腫導致的梗阻加重,使得其應用仍有一定的風險和限制。
由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魏翔教授團隊開發的一種新型經心尖室間隔心肌旋切術(transapical beating-heart septal myectomy,TA-BSM)成功應用于臨床,目前手術已經完成超過500例。2023年發表了其首次人體可行性研究[55]結果,47例患者器械成功率為97.9%,3個月隨訪有42例患者效果滿意,左心室流出道梯度由術前86 mm Hg降至術后3個月時的19 mm Hg,共出現1例器械無關的死亡、1例延遲性室間隔穿孔、1例心尖撕裂、1例使用永久起搏器,近期療效不劣于經主動脈間隔切除和酒精化學消融。隨后發表的TA-BSM擴大樣本的研究經驗(120例)[56],提示潛伏性梗阻或靜息性梗阻術后結果無差異。
除了切口更加微創、無需體外循環外,心肌旋切術的明顯優勢是可以實時超聲和血流動力學評估間隔切除的充分性,尤其適用于小主動脈瓣環間隔暴露不佳的兒童肥厚型心肌病患者,或先前已經進行過主動脈瓣置換的殘余梗阻患者,或術后復發性患者和不適合體外循環的孕婦患者[57-58],其創新性理念為多種臨床情況開辟了一條新的治療途徑。由于裝置易于到達中室間隔和心尖室間隔,可提供更長的切除范圍,被認為是影響切除效果的重要因素,另一個額外優勢包括肥厚型非梗阻性心肌病和心尖肥厚型心肌病患者也可能可以應用,目前正在進行相關探索并已經觀察到令人鼓舞的治療效果[59]。除心尖路徑外,旋切裝置同樣可以術中經主動脈使用,甚至升級為經股動脈介入器械。此外,還有提出是否可嘗試用于切除主動脈瓣下隔膜梗阻、右心室流出道肌肉梗阻等潛在應用場景[60]。
5 心臟移植領域
心臟移植仍然是提高終末期心力衰竭患者預后的金標準,國際心肺移植學會(ISHLT)最新報告[61]稱,2005—2017年間接受心臟移植的成年受試者在1、3、5和10年的存活率分別為85.0%~90%、79.1%、73.9%和69%。器官共享聯合網絡(UNOS)和ISHLT報告[62]稱,心臟移植成年接受者的中位生存期為13年。由于供需關系的巨大不平衡,擴大心臟捐贈者供體庫顯得至關重要,包括選擇帶有血液傳染病丙肝的供體、器官捐獻政策革新和公眾科普(由選擇加入向選擇退出政策的轉變、器官捐獻與接受互惠政策、器官捐獻受贈與法的約束而不僅是知情同意等)、拓展循環死亡后器官捐贈、基因編輯豬異種心臟移植的研究等[63-64]。
研究[65]顯示,丙型肝炎病毒陽性供體心臟移植聯合短療程直接抗病毒療法的近中期結果與丙型肝炎病毒陰性供體心臟移植相似,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治愈率為100%,沒有與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關的死亡,ISHLT也發表聲明[66]支持在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后在有治療經驗的中心使用丙型肝炎病毒血癥捐贈者的器官,主要風險在于短暫性丙型肝炎病毒血癥帶來的較高的急性細胞排斥反應(31%)和較低的短療程直接抗病毒療法不耐受率(<2%)[67-68]。
自2014年恢復循環死亡供體心臟移植以來,已實施超過500例心臟移植,先后在澳大利亞、英國、美國等數十個國家進行研究和應用。多項回顧性研究[69-71]顯示,腦死亡和循環死亡供心移植的機械循環支持率和支持時間、住院時間、排斥反應發生率、30 d生存率、1年和5年生存率均無差異,短期內移植物功能障礙發生率并無顯著升高。2023年美國胸外科協會(AATS)發布了循環死亡供心的成人心臟移植專家共識[72],以推動這一領域的規范發展。同時中國醫師協會器官移植醫師分會、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也聯合發布了《中國心臟死亡捐獻器官評估與應用專家共識(2022版)》[73],以更科學、規范地指導循環死亡器官捐獻的評估與應用。然而在真正普及前還需解決很多問題,包括循環死亡定義和評估標準、醫學倫理問題、立法制定規則等。
隨著基因編輯技術的進步,異種移植重新引起科學家的巨大興趣。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使用CRISPR-Cas9技術創建了10基因編輯豬(敲除αGal、NeuGc、B4Gal 3種最常見異種免疫表位基因,敲除編碼豬生長激素受體GHR基因以抑制移植物過度生長,插入兩個人類基因CD46和CD55以上調其表達,抑制補體級聯激活,插入人類編碼內皮蛋白C受體和血栓調節蛋白的PROCR和THBD基因來控制凝血紊亂,插入白細胞表面抗原CD47和血紅素加氧酶1基因以上調參與抗炎和免疫抑制途徑的基因表達)[74],成功克服了超急性排斥反應屏障,但免疫抑制和急性排斥反應(移植后數周至數月)尚未全部解決,包括抗體介導的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同時還需要滅活或消除豬細胞中的人畜共患病原體(豬內源性逆轉錄病毒、豬巨細胞病毒等)。2022年1月在美國馬里蘭大學成功對1 例57歲患者進行了首例10-GE豬-人心臟異種移植[75],然而在第49天出現了嚴重舒張性心力衰竭,第56天心內膜心肌活檢顯示病理性抗體介導的排斥,40%的心肌細胞壞死,異種移植物最終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損傷并在第60天死亡,尸檢結果顯示與典型的異種移植排斥不符,同時檢測到的豬巨細胞病毒推測可能對心臟移植產生破壞性影響[76]。在團隊改良了感染的預防措施,并且嘗試使用新的實驗性抗體以阻斷 CD154抗體介導的免疫排斥反應,2023年9月在1 例58歲晚期心臟病患者上實施了第2例豬心移植,不幸的是術后第40天仍然因為排斥反應而死亡[77]。異種心臟移植的研究仍然任重而道遠。
另一方面,終末期心力衰竭常伴隨腎或肝功能障礙,會對單純心臟移植構成障礙,對迫切需要對心腎聯合移植和心肝聯合移植需求更加明顯,適當分配這一稀缺資源至關重要,同時需要對其進行明確的指導。2023年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發布了科學聲明[78]闡述心-腎和心-肝雙器官移植的適應證、評估和結果,探討腎和肝功能障礙的評估和對結局的潛在影響,并詳細梳理了患者選擇、圍術期管理和倫理問題。
6 左心室輔助領域
隨著第三代左心室輔助裝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治療效果不斷提升[79],以及適應證由中短期橋接移植向長期的邁進,中國已經進入LVAD時代,5種上市的心室輔助裝置(重慶永仁心EVAHEART 1、EVA-Pulsa,蘇州同心CH-VAD,天津航天泰心HeartCon,深圳核心Corheart 6)均在緊鑼密鼓地推動商業化進程,全國已有85家醫院完成超過500例植入,16家醫院完成10例以上,且國產裝置更好的體積、重量和性能也保障了臨床的易用性和療效,搏動性血流、流量自調節功能、生物相容性涂層等功能也更好地適應人體生理需求。2023年中國心室輔助裝置專家共識委員會發布了《中國左心室輔助裝置候選者術前評估與管理專家共識(2023年)》[80],四川省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會心臟重癥與輔助支持專業委員會等發布了《左心室輔助裝置植入全程管理專家共識(2023年)》[81],系統總結了 LVAD 的適應證與禁忌證、手術時機選擇、術前評估、術前狀態優化等最新認識及規范,以期指導臨床對此新療法的規范化應用,并在技術培訓、圍術期管理、質量控制、術后右心心力衰竭防治、康復訓練和護理、心理支持、病例注冊登記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開展。同時借鑒近期發布的美國心力衰竭學會(Heart Failure Society of America,HFSA)關于持久機械循環支持患者醫療管理的專家共識聲明[82]、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心力衰竭協會/歐洲心律協會心力衰竭患者植入式裝置治療融合管理的臨床共識聲明[83]、持久性機械循環支持JACC科學聲明[84]、ISHLT/HFSA急性機械循環支持指南[85]、ESC心力衰竭協會LVAD合并右心力衰竭的術前、術中和術后管理策略臨床共識聲明[86]、2023年ISHLT機械循環支持指南10年更新[87]等文件,推動我國LVAD行業平穩健康發展。
7 冠脈外科領域
2023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HA等6個學會聯合發布了慢性冠脈疾病指南[88],遭到AATS和STS的強烈抗議,尤其反對對三支血管病變患者搭橋手術推薦級別的降低[89],他們認為這版指南與2021年指南一樣沒有將治療推薦與現有最佳循證醫學證據相結合。與此同時,近期先后發布了ESC/歐洲心胸外科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EACTS)左主干冠脈疾病血運重建的指南建議[90]、EACTS/STS冠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導管選擇的專家評價[91],重申CABG在左主干病變的首選地位和證據級別,以及對橋血管類型選擇進行了系統闡述。CABG在復雜冠脈病變中逐年增多的臨床證據也顯示了其無可置疑的基石地位。近期的研究結果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左主干病變:最新Meta分析[92]綜合了目前最大的4項隨機對照研究(SYNTAX、PRECOMBAT、NOBLE和EXCEL),顯示無論是否合并急性冠脈綜合征狀態,患者在冠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或CABG術后5年死亡率無顯著差別,PCI術后再發心肌梗死和再次血運重建發生率高于CABG。然而另一項SWEDEHEART注冊登記研究[93]的真實世界數據顯示,在校正混雜因素后,PCI患者較CABG患者死亡風險更高、主要不良心腦血管事件(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新發血運重建)風險也更高。
(2)三支血管病變:FAME 3研究比較血流儲備分數指導PCI與CABG的臨床預后,1年隨訪結果PCI組主要終點(死亡、心肌梗死、卒中和再次血運重建的復合終點)發生率高于CABG組(10.6% vs. 6.9%)[94],3年隨訪結果依然如此(18.6% vs. 12.5%)[95],主要體現在死亡與卒中風險兩組間無差異,而心肌梗死和再次血運重建風險PCI組更高。CABG總體優于PCI,并優于藥物治療。
(3)射血分數低下的缺血性心肌病:在此前STICH研究[95]中,CABG聯合藥物治療較單純藥物治療可進一步降低射血分數低下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遠期死亡率,而REVIVED-BCIS2研究[96]中,PCI未能較單純藥物治療進一步降低射血分數低下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死亡率和心力衰竭再住院率。迄今為止,尚無頭對頭比較CABG和PCI治療缺血性心力衰竭的隨機對照研究,STICH國際研究聯盟正在開展。近期報道的以英格蘭地區真實世界臨床數據使用計算機技術比較CABG和PCI的模擬隨機對照研究[97],在校正混雜因素后,CABG組較PCI組5年死亡和心力衰竭再住院復合終點發生率降低16.2%,確認CABG是治療這類患者的首選策略。
(4)橋血管選擇:CABG中至少選擇1根動脈橋已被證實具有更大的生存獲益,而左乳內-前降支橋基礎上,其他橋血管類型的最佳選擇一直缺少證據。RAPCO研究[98]是第一個證實橈動脈橋超遠期臨床結局優于右乳內或大隱靜脈橋的隨機對照試驗,遠期臨床獲益(主要心血管事件終點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和再次血運重建)在術后5年內差距不明顯,到術后15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橈動脈 vs. 右乳內,P=0.04;橈動脈 vs. 大隱靜脈,P=0.04);在接受1根動脈橋的基礎上,不同術者對大隱靜脈橋的使用數量習慣各異,一項美國的多中心研究[99]顯示,保守組(使用1~2根靜脈橋)與積極組(使用3~4根靜脈橋)的15年長期生存率沒有差異。
8 慢性心力衰竭的心臟結構干預手段
藥物治療一直以來都是慢性心力衰竭治療的基石,對于終末期心力衰竭和無法控制的急性失代償心力衰竭,短期或中長期機械輔助的循環替代治療已成為臨床診療共識。而對于尚未進入晚期的慢性心力衰竭,單純藥物治療尚不能全部滿足臨床治療需求,非藥物/器械治療前景仍十分廣闊,一眾從不同機制改善心力衰竭的非藥物/器械手段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本文主要關注結構干預療法在當前臨床實踐中治療心力衰竭的作用。
在外科治療中,梅奧醫院最新報道了一種心包切除術治療射血分數保留的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HFpEF)的早期臨床研究(n=4)[100],這一手段是基于HFpEF的病理生理機制之一—左心室高充盈壓部分由心包介導的心臟外在約束引起,運動時更為顯著。初步結果顯示,與術前心包完整時相比,即刻的容量負荷試驗后肺毛細血管楔壓(pulmonary capillary wedge pressure,PCWP)上升幅度明顯下降[ΔPCWP (4±4)mm Hg vs.(9±2)mm Hg],且絕對值更低[(16±6)mm Hg vs.(21±4)mm Hg];在3個月和6個月隨訪時堪薩斯城心肌病問卷評分和峰值耗氧量較術前顯著增加。該研究中所觀察到的積極信號提示了這種非植入物理治療方式的潛在有效性,筆者推測另一個可能的潛在機制:心室可通過直接與胸壁粘連而借助胸廓呼吸運動來改善室壁順應性。需要繼續關注更大樣本量的隨機對照研究。
AccuCinch是一種經導管左心室修復系統,使用一系列錨定點對左心室基底部進行環縮,其治療機制是通過縮小左心室容積降低心肌壁應力,從而使左心室逆向重塑而改善心力衰竭。AccuCinch早在2016年即開始進行包括治療二尖瓣反流、擴張性心肌病在內的一系列臨床研究,并逐漸轉移到以治療射血分數降低的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HFrEF)為主。對于先前參與研究的無二尖瓣反流>2+的HFrEF患者,2023年首次發表了1年隨訪結果[101],共51例患者接受了經導管左心室修復,僅1例因左心室瘢痕而中止手術,手術即刻顯示左心室游離壁半徑平均減少9.2 mm,12個月隨訪顯示左心室舒張末期容積減少(33.6±34.8)mL,紐約心臟協會心功能分級、堪薩斯城心肌病問卷總分和6分鐘步行距離有顯著改善,隨訪期內僅1例死亡、1例接受左心輔助。進一步的隨機對照研究(NCT04331769)目前仍在患者招募中(n=400)。
心房分流術是另一項備受關注的新技術手段,第二項重磅隨機雙盲對照RELIEVE-HF研究[102]近期于美國心血管病學會年會上公布,出乎意料的結果引起了業內廣泛討論。該研究使用的是內徑5.1 mm沙漏狀Ventura房間隔分流器,508例患者在中位隨訪22個月后,整個隊列的主要終點并無顯著差異。但在HFrEF組亞組分析中,分流組(101例)較假手術組(108例)在年事件率顯示出優效性差異(49.0% vs. 88.6%,HR=0.55,P<0.000 1),尤其在心力衰竭再住院事件上改善最為顯著(26.0%/年 vs. 52.0%/年,HR=0.52,P=0.01);在HFpEF組亞組分析中,分流組(149例)較假手術組(153例)年事件發生率高(60.2% vs. 35.9%,HR=1.68,P=
9 主動脈夾層領域
近年來主動脈夾層的發病率及內外科治療呈快速增長態勢,對主動脈病理及發展機制也不斷有新的認識。盡管2022年ACC/AHA主動脈疾病的診斷和管理指南[103]和2024年EACTS/STS主動脈急性和慢性綜合征的診斷與治療指南[104]仍然以主動脈直徑≥5.5 cm為Ⅰ期、≥5.0 cm為Ⅱa期的手術干預推薦,新的研究仍在推進預防性升主動脈瘤干預指征前移的問題。耶魯大學團隊研究[105]發現,升主動脈直徑≥5 cm時患者發生急性事件風險迅速增加,當主動脈尺寸為3.5~3.9 cm、4.0~4.4 cm、4.5~4.9 cm、5.0~5.4 cm、5.5~5.9 cm和≥6.0 cm時,發生主動脈事件的年平均風險分別為0.2%、0.2%、0.3%、1.4%、2.0%和3.5%,10年無事件生存率分別為97.8%、98.2%、97.3%、84.6%、80.4%和70.9%,并建議將升主動脈瘤修復手術閾值從5.5 cm降低至5.0 cm。廣東省人民醫院團隊研究[106]認為,反映形態學的升主動脈容積是更好的風險預測指標,而不能僅關注升主動脈最大直徑、直徑增長率、長度指標。此外,升動脈瘤手術需要將年齡、遺傳病、家族史、糖尿病等各種因素納入決策中。
A型主動脈夾層血管內治療的應用一直以來受到缺乏合適的近端著陸區、存在明顯主動脈反流和心臟壓塞的限制,Endo-Bentall血管內瓣膜導管早在2014年就已被提出[107],已有一些病例報告和小系列隊列研究,主要是預期死亡風險較高的(如老年、多合并癥、神志不清、末端器官灌注不良)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解剖適應證標準相對較嚴格,可行性通常在40%以下。隨著血管內修復器械不斷更新和改進,更安全、解剖適應證更寬的產品不斷面世。郭偉教授及其團隊提出了新型模塊化Endo-Bentall系統并成功完成全球首例植入,其包含了兩側冠脈內分支、冠脈重建支架和帶連接段支架介入主動脈瓣的全覆膜支架,且評估認為66.4%的A型夾層具有其解剖適應性,更適合主動脈根部內膜撕裂的患者。
10 心房顫動的外科綜合治療
2023年亞太心律協會發表了關于心房顫動(房顫)手術的專家共識聲明[108],在伴或不伴結構性心臟病的房顫手術治療中詳細敘述了目前的證據和建議。對于需打開或無需打開左心房的心臟外科手術的房顫患者,建議進行外科房顫消融(Ⅰ,B)。對于單純房顫患者,在仔細考慮安全性和有效性后,對于一次或多次導管消融失敗的患者,左心房擴張或藥物治療不耐受或難治性患者,應考慮采用微創胸腔鏡方法進行單獨的外科消融(Ⅱa,b)。癥狀性房顫患者應考慮外科消融、左心耳閉合聯合導管消融的復合雜交手術(Ⅱa,b)。當沒有迷宮手術或其他控制節律手術指征時(如嚴重左心房擴張、房顫持續時間長、預計無法轉復、手術時間長可能增加手術風險或影響術后恢復),推薦合并房顫的患者在實施體外循環或非體外循環手術時同期關閉左心耳(Ⅰ,A)。對于血栓栓塞或出血風險高的房顫患者,盡管有最佳的抗凝治療但不適用于經皮左心耳封堵時,建議采用胸腔鏡左心耳關閉術(Ⅱa,B)。
目前尚無足夠證據支持,指南暫不建議在常規心臟手術期間對非房顫患者進行預防性左心耳封堵,但盡管如此在心臟外科臨床實踐中已經比較廣泛地對老年、合并左心力衰竭和左心房擴大、合并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等房顫高危患者中進行預防性左心耳關閉。對于持續性或長期持續性房顫患者則更優先考慮內外科聯合消融+左心耳閉合的混合雜交手術,尤其是當抗心律失常藥物和基于導管的消融失敗時。基于目前的指南建議,將單純房顫外科消融的適應證應用于混合消融可能是合理的。近期JACC雜志上發表了對于混合雜交房顫手術目前的證據[109],盡管風險比導管消融更高,但更徹底完善的透壁消融可進一步提高轉復成功率并降低復發率。外科選擇方式有包含左心房頂到左心房底連接線的肺靜脈隔離、左心房后壁消融、后壁盒式病變消融,或是直接Cox-Maze手術,然后進行左心耳縫閉、導管消融程序。納入10余項隨機和非隨機研究的Meta分析[109]顯示,達到研究主要終點免于房性心律失常復發(910/1 241)的患者比例為0.75[95%CI(0.69,0.81)],選擇內外科分期消融和同期混合消融的成功率分別為0.83[95%CI(0.68,0.94),348/454]和0.71[95%CI(0.68,0.74),562/787]。進一步比較混合消融與導管消融的隨機對照試驗仍在進行中(HARTCAP-AF:NCT02441738;CEASE-AF:NCT02695277;HALT-AF:NCT05411614)。
11 總結與展望
作為醫療領域金字塔尖的學科,心血管外科乃至整個心血管領域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得益于國內外眾多創新與轉化項目的涌現,尤其是顛覆性生物材料、原創性醫療器械與突破性新技術,給心外科發展帶來了機遇和希望。許多醫學創新從醫生中來,由醫工結合共同實現,并最終服務于醫生和患者,未來技術發展也必然沿著這條醫學轉化大道不斷前行。同時,高質量的臨床研究也在不斷更新或者挑戰過去的治療理念,需要廣大心血管同行不斷參與和持續學習,以促進學科和個人發展,推動我國心血管外科事業的不斷前進。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張長東負責文獻檢索、文章撰寫;尚小珂負責選題設計、思路分析、文章撰寫;鐘禹成負責資料整理和潤色校對;董念國負責審閱和提出指導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