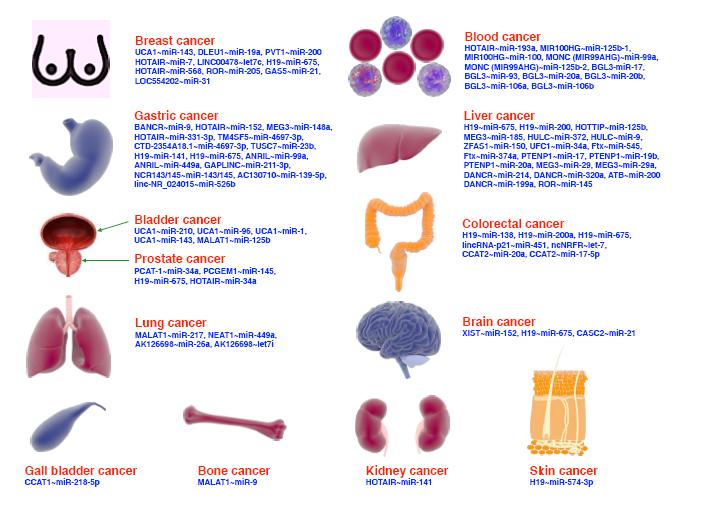原發性肝癌(簡稱“肝癌”)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惡性腫瘤之一,在我國約80%為肝細胞性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1]。2022年全球肝癌新發病例順位第6位,而中國肝癌新發病例數順位第4位;全球肝癌死亡順位第3位,而中國肝癌死亡順位第2位[2-3]。肝癌早期缺乏典型癥狀、惡性程度高、侵襲性強、易轉移復發,多數患者確診時常處于中晚期,這與相關免疫細胞調控HCC快速增殖、侵襲和早期轉移等復雜免疫機制有關,使得總體預后較差[4]。迫切需要深入了解HCC的免疫發病機制并采用更加有效的治療措施。近年,免疫治療在癌癥治療中展現了較高的潛力。HCC作為一種免疫原性癌癥,免疫治療有望提高HCC患者的生存率。補體系統作為先天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在免疫治療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具有顯著的潛在應用價值。筆者現就補體系統在HCC免疫治療方面的應用進展及前景作一綜述。
1 補體系統及它在癌癥中的免疫調節作用
人類補體系統由大約50種蛋白質和蛋白片段組成,包括補體固有成分、補體調節蛋白及補體受體,主要存在于血液或淋巴液循環(主要由肝臟分泌),它是人體先天性免疫反應的關鍵組成部分,可通過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蛋白質參與到免疫反應,在調節肝損傷、炎癥、再生反應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5]。
補體系統的激活是高度受控的,可防止對自體組織的損傷,主要通過3種途徑發生:經典途徑(CP)、凝集素途徑(LP)和旁路途徑(AP),這3條途徑又共同合并成末端途徑,以激活C3。免疫細胞表達的過敏毒素(包括C3a、C4a、C5a)與C3片段的特異性受體相互作用,從而將補體激活與免疫細胞功能調節聯系在一起。
早前普遍認為,補體系統有助于免疫監視癌癥,幫助身體識別和清除惡性轉化的細胞。然而2008年Markiewski等[6]在小鼠宮頸癌TC-1同基因模型小鼠皮下注射TC-1腫瘤細胞后發現,靶向敲除補體C3或C4基因片段的小鼠逃避了腫瘤的侵害,結果提示,在某些情況下,抑制補體成分的激活可能會延緩腫瘤的發展。另有多項研究[7-9]表明,補體成分有助于調節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功能,并在某些條件下通過發揮免疫調節作用增強抗腫瘤功能,但它也與腫瘤細胞增殖和再生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這些研究成果為補體成分的免疫調節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礎。
補體系統是抗腫瘤免疫反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作為人體一種內在效應機制協調著先天免疫反應和適應性免疫反應,從而促進或抑制腫瘤的發展[10]。在多種實體瘤中,補體系統的激活對調節TME中的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起到關鍵作用[11],而肝臟內的補體激活可能會通過多種機制促進HCC的發展,如肝內補體激活可能通過激活Kupffer細胞中的核因子-κB和肝細胞中的信號轉導因子和轉錄激活因子3促進HCC的發展[12]。因此,抑制腫瘤補體成分的激活可能有助于增強腫瘤免疫治療的療效。
2 補體系統在HCC免疫機制中的作用
2.1 HCC的免疫發病機制
肝臟內部的免疫調節和穩態由自然殺傷細胞、自然殺傷T細胞、γδ T細胞、Kupffer細胞等共同參與和維護[1]。然而慢性病毒感染、酗酒等危險因素可破壞肝臟內部的免疫穩態,從而導致肝炎、肝硬化等肝癌先兆疾病的發生[13];另外,自然殺傷細胞、自然殺傷T細胞、樹突狀細胞、腫瘤相關巨噬細胞、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髓源性抑制細胞等免疫細胞以及由這些細胞產生的趨化因子共同作用于TME,起著抑制或促進肝癌的發生和進展的作用[14];另一方面,HCC相關炎癥會導致基因組不穩定、癌細胞增殖、抗凋亡途徑增強,最終導致腫瘤擴散[15],而補體系統在HCC相關炎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補體成分通過啟動和放大炎癥反應、促進免疫細胞浸潤及調控細胞因子釋放,從而影響HCC的發生和發展[16]。由于補體系統在HCC相關炎癥中的調節作用,補體成分可能成為新的免疫治療靶點,如抑制補體活性可能減少有害的炎癥反應,而促進特定補體成分活性可能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17]。近年來,免疫因子、可溶性效應分子和趨化因子受體作為治療HCC的潛在靶點引起了廣泛關注,當前的免疫療法主要依賴于調節適應性免疫反應,因此,探索涉及先天性免疫的新機制可能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在這方面,補體系統成分的免疫調節已成為肝癌免疫治療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2.2 補體系統成分調節在HCC中的治療前景
研究[18]表明,補體激活可以通過增強血管生成、保護腫瘤細胞免受免疫監視、增加有絲分裂信號、激活抗凋亡機制和異常細胞增殖、侵襲和遷移來促進HCC。此研究結果提示,補體系統在HCC免疫治療中可能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并為未來利用補體聯合治療HCC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補體聯合治療雖在其他疾病中進行了初步探索,但在HCC治療的研究尚需要深入研究。直到最近,補體系統其中幾種成分在癌癥免疫抑制中的作用引起了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而它們在HCC免疫調節中的作用也已經被發現,它們在HCC免疫機制中的作用及其治療前景也已有初步研究成果。
2.2.1 補體固有成分
2.2.1.1 C1q
C1q是補體C1復合物的重要組成部分,負責啟動補體激活的經典途徑[19]。研究[20]表明,C1q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相關蛋白1(C1q and TNF related 1,C1qTNF1)已被確定為HCC的主要動態網絡生物標志物基因,發揮著抑制HCC侵襲和轉移的核心作用,C1qTNF1通過調節與血小板相關的腫瘤信號傳導途徑,為HCC治療提供了新的治療靶點;另有研究者[21]報道,C1qTNF6在HCC組織中特異性高表達,抑制C1qTNF6表達能夠使Akt信號通路失活,阻止腫瘤細胞的存活、遷移和侵襲,并促進HCC細胞凋亡。C1q能誘導膠原受體盤狀結構域受體1(disidin domain receptor 1,DDR1)的激活和上調,增強HepG2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能力,這與C1q誘導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又名Akt)PI3K/Akt信號的激活,并增加基質金屬蛋白酶-2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的表達相關,強烈提示了C1q-DDR1在促進HCC進展中的作用[22]。目前有研究[23]發現,使用C1q抑制劑可以有效調節β-連環蛋白途徑的激活,預防慢性肝炎患者的腫瘤進展。在用于治療不可切除HCC的免疫藥物中,如納武利尤單抗(nivolumab)和帕博利珠單抗(pembrolizumab),由于它們與補體C1q和Fc受體的親和力,在發揮抗腫瘤作用的同時,還能誘導補體激活,增強免疫反應[24]。美國FDA批準用于治療遺傳性血管性水腫的C1抑制劑已被證明可通過抑制C1q阻斷經典激活途徑,減少過度的補體活化,防止自身免疫反應導致的組織損傷[25]。以上結果提示,利用C1q抑制劑可以調控補體經典途徑的活性,減少炎癥反應,潛在地為HCC的治療提供了一種新的策略,但關于C1q在HCC免疫中的作用還需要更多研究確定其是否具有保護性或致病性。
2.2.1.2 C3
補體系統的核心成分C3在補體激活的經典途徑和旁路途徑中均發揮重要作用[26]。有研究[27]表明,肝星狀細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產生的C3通過影響樹突狀細胞的成熟和擴增腫瘤相關的骨髓來源抑制性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促進HCC的發生及發展。然而,補體C3缺陷的造血干細胞不能誘導MDSCs擴增,這與HSCs衍生因子B和因子D相關,導致C3裂解為iC3b和C3d,iC3b的加入促進了免疫抑制性MDSCs的分化[28]。在HCC中,MDSCs還具有促進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的作用[29]。以上研究為同時靶向C3和MDSCs治療HCC的未來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細胞內補體C3的激活可顯著抑制CD8+ T細胞的抗腫瘤活性,增強T細胞衰竭,促進M2巨噬細胞的形成,導致腫瘤細胞對抗程序性死亡蛋白配體 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1,PD-L1)治療產生抗性,使這種抗腫瘤免疫療法失效[30]。因此,阻斷腫瘤細胞衍生的C3可通過增強抗PD-L1治療的功效,從而增強抗腫瘤能力,這表明C3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合治療將會是HCC的潛在治療策略。
2.2.1.3 甘露糖結合凝集素(mannose-binding lectin,MBL)
MBL是補體激活凝集素途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免疫調節和腫瘤發生中起著關鍵作用[31]。大多數哺乳動物有兩種類型的MBL(MBL1和MBL2),其中MBL2參與先天免疫及其免疫調節[32]。MBL作為肝臟合成和分泌的一種特異性蛋白,它在HCC的發生及發展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Liao等[33]利用GSEA探索了MBL2影響HCC進展的潛在機制發現,MBL2低表達與多種通路激活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包括細胞周期、DNA復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信號通路和癌癥干細胞相關通路,此外,經過體內和體外實驗后證實,MBL2低表達可增強肝癌細胞的致癌能力;另一方面,MBL2高表達水平與抗腫瘤免疫細胞相關,包括自然殺傷細胞和CD8+ T細胞[34]。提示MBL在HCC免疫治療靶點方面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盡管之前有研究者認為,MBL2的基因多態性與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相關性HCC或單純性HCC之間無相關性,但Su等[35]的研究證實了MBL2基因突變是HCC患者的易感因素,而單核苷酸多態性(rs11003123)可能是中國人群發生HCC的潛在危險因素。在HCC小鼠模型研究[36]中,相對于野生型小鼠,MBL遺傳缺失促進了HCC的進展,恢復MBL表達后的小鼠抑制了HCC的進展,這可能與MBL下調ERK/COX-2/PGE2信號通路抑制肝星狀細胞活化有關。以上結果證明了MBL高表達具有抗腫瘤功能,可抑制HCC進展,靶向MBL治療將有助于開發新的策略提高肝癌免疫治療的有效性。
2.2.2 補體調節蛋白
2.2.2.1 補體因子H(complement factor H,CFH)
CFH主要參與調節旁路途徑的補體激活,而旁路途徑中補體的缺失會引起異常炎癥,從而導致腫瘤的發生。有研究[37]發現,CFH缺陷小鼠的肝臟內出現了自發的補體激活,缺乏 CFH 的小鼠會自發發展為HCC,這提示了CFH在控制肝臟補體激活方面具有關鍵作用,并且缺乏CFH可能會促進慢性炎癥和HCC的發展;并且還發現,CFH突變和CFH mRNA水平與HCC患者生存預后相關。Hyang Sook Seol等[38]發現CFH和C7可以刺激淋巴樣增強因子-1(LSF-1)的表達,導致干燥因子上調,最終增加癌癥的干燥程度。然而,C7和CFH促進淋巴樣增強因子-1表達的具體機制尚不清楚,深入研究這種機制有望為HCC治療提供一種逆轉腫瘤耐藥的新方法。另有研究[39]表明,CFH相關蛋白家族補體因子H相關蛋白3(Complement factor H-related 3,CFHR3)是補體調節炎癥反應的關鍵因素,CFHR3的表達調控與Wnt和NOTCH信號通路的激活以及肝癌發生、細胞增殖有關。此外,有較多研究鑒于CFHR3構建了較多相關模型,在優化HCC患者診斷、預后評估和免疫治療選擇方面具有巨大潛力,比如Chen等[40]基于CFHR3等基因構建的干細胞相關模型可以預測HCC患者的預后、免疫基因組表達及對化療藥物的反應,并在高風險模型中觀察到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及免疫檢查點的比例相較于低風險模型呈顯著增加;同樣Ruan等[41]發現,基于CFHR3等基因所構建的炎性相關鐵死亡預測模型在免疫檢查點抑制治療中有較高的應答率。以上結果提示CFH 和CFHR3表達調控與HCC預后密切相關,可作為HCC新的免疫治療靶點,并且基于CFHR3構建的預測模型在HCC患者的預后、免疫基因組表達及對化療藥物的反應方面具有良好的預測性。
2.2.2.2 C4B
C4B作為C3和C5轉化酶的關鍵組分,在補體系統經典途徑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42]。它不僅參與了補體級聯反應的傳播,而且具有多個輔助因子,如C4BPA和C4BPB,可以通過水解C4B并解離C4B2A復合物以抑制補體激活。一項研究發現,在HCC患者血漿的小細胞外囊泡中,C1QB、C1QC、C4BPA和C4BPB的表達上調,這也表明C1QB、C1QC、C4BPA和C4BPB可能是潛在的治療靶點[43]。作為HCC前兆的HCV感染患者進展為HCC的風險更大,需要一種敏感性更高的特異性生物標志物。Dalal等[44]發現,C4B水平升高是HCV相關終末期肝病患者的可靠標志物。因此,補體C4B直接參與HCC免疫反應的生物學調控,以及作為生物標志物區分患者群體的差異表達能力,表明補體C4B是HCC疾病調節和治療靶向的重要靶點。
2.2.2.3 CD46
CD46是一種在細胞表面表達的膜結合補體調節蛋白,具有抑制補體系統過度激活及保護組織免受損傷的作用;除了作為膜結合補體調節蛋白的作用外,它還在調節T細胞介導的免疫應答中發揮關鍵作用[45]。當肝臟受損時,肝臟會產生纖維化,這些成纖維細胞是由活化的HSCs分化形成的,HSCs從失活狀態到活化狀態的主要調節因子是CD46[46]。Liu等[47]發現,CD46的單核苷酸多態性(rs2796267)通過修飾啟動子活性增加了HCC的易感性和疾病結局的風險,還發現,單核苷酸多態性(rs2796267)的AG/GG基因型與接受切除手術的HCC患者不良預后相關。早有研究發現,HCC細胞系和臨床樣本都表達了高水平的CD46,通過使用靶向CD46、SG635-p53的新型纖維嵌合溶瘤腺病毒,在Hep-3B皮下異種移植肝癌模型中顯示出抗腫瘤活性,顯著抑制了易感小鼠體內的肝癌進展、提高了生存率,并促進了腫瘤的消退[48]。以上結果提示CD46調節腫瘤微環境中T細胞介導的免疫應答,并可激活HSCs,深入了解CD46有助于在HCC腫瘤微環境調控中發現重要作用;此外,深入研究靶向CD46、SG635-p53的新型纖維嵌合溶瘤腺病毒治療HCC的機制將為臨床上HCC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療策略。
2.2.2.4 CD59
CD59是一種細胞膜上的蛋白質,也被稱為細胞膜攻擊復合物(MAC)結合蛋白,可以抑制MAC的形成,保護細胞免受免疫系統的攻擊[49]。一些研究正在探索通過調控CD59表達或功能來治療HCC的方法。例如,通過抑制CD59的表達或功能,可以增強免疫系統對肝癌細胞的殺傷作用,從而提高對HCC的免疫治療效果[50]。Abdel-Latif等[51]在二乙基亞硝胺誘導的HCC大鼠模型中發現CD59的mRNA和蛋白表達增加,并促進了腫瘤的生長,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發現還輔酶Q10可能通過增加脂質含量、降低CD59表達和PLD活性起到抗腫瘤的作用。Lan等人[52]研究表明,CD59可能是HCC潛在的致癌驅動因素,并且發現CD59的高表達與HCC患者較差的總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相關。這可能與CD59的缺失通過過量的Smad7形成和Smad2/3磷酸化的消除,損害了體內、外的致瘤性和轉移能力有關。以上結果提示,通過抑制CD59表達可增強抗腫瘤能力而提高對HCC的免疫治療效果,可以作為HCC潛在的治療靶點。
2.2.3 補體受體
補體成分C5是補體級聯末端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C5激活后產生的C5a是一種過敏毒素和白細胞趨化物質,通過促進癌細胞的轉移在TME中發揮關鍵作用[53]。研究[54]表明,補體C5a受體(C5aR1)的自分泌激活可促進肝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導致細胞周期G0/G1期阻滯和細胞凋亡,并抑制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和Ki-67(一種增殖細胞的相關抗原)的表達。在肝癌細胞中,C5a-C5aR1軸通過上調轉錄因子Snail表達以及下調緊密連接蛋白-1(Claudin-1)和鈣粘蛋白E(E-cadherin)表達來誘導上皮細胞-間充質轉化(EMT)[55]。Lin等[56]研究發現C5aR1在HBV相關肝癌細胞中高度表達。通常來說,抗腫瘤治療的最大問題是免疫治療的耐藥性,根據以往的ICIs使用經驗,補體抑制藥物與其他療法聯合使用或許可以解決這一難題。有研究表明,C5aR1抑制劑聯合紫杉醇能夠促進干擾素-γ(IFN-γ)陽性巨噬細胞的重編程,使它從促腫瘤的M2型轉變為抗腫瘤的M1型,增加TME中CXCR3效應細胞和記憶CD8+ T細胞的數量和細胞毒性,從而提高紫杉醇化療的療效和敏感性[57]。另外,C5aR1抑制劑聯合替莫唑胺治療膠質母細胞瘤時可誘導DNA損傷和腫瘤細胞凋亡,增強替莫唑胺化療的敏感性[58]。有研究發現,聯合抑制C5a和PD-L1信號通路可能有助于抗腫瘤治療的協同作用[59],因為聯合阻斷C5a和PD-L1影響TME中MDSCs的數量,降低免疫抑制功能,增加腫瘤浸潤CD8+ T細胞的數量,促進內源性白細胞介素-10(IL-10)的產生,從而增強抗腫瘤功能[60]。這些數據都表明了C5aR1抑制劑在抗腫瘤治療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可作為治療HCC的候選藥物。補體相關療法與其他抗腫瘤免疫治療的聯合應用存在一定的風險和益處,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鑒于補體分子在調節HCC免疫機制中的作用,補體系統的各種分子可被視為HCC患者潛在的免疫治療靶點。
3 總結
補體系統協調著先天性免疫系統和適應性免疫系統,通過激活免疫細胞,在影響HCC免疫發病機制中至關重要。根據目前對各補體成分作為致癌驅動因素的認識,可以獨立開發補體抑制劑等相關靶向治療或者與目前一線和二線HCC免疫治療聯合應用。總之,更深入地了解補體系統在致瘤和抗腫瘤機制中的作用,并結合先進的生物信息學方法,有望促進HCC更加有效的臨床免疫治療設計和開發。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劉校伸負責論文的設計與撰寫;王志鑫負責文獻分析;王灝和杜磊負責數據整理;任利負責論文審校。
原發性肝癌(簡稱“肝癌”)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惡性腫瘤之一,在我國約80%為肝細胞性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1]。2022年全球肝癌新發病例順位第6位,而中國肝癌新發病例數順位第4位;全球肝癌死亡順位第3位,而中國肝癌死亡順位第2位[2-3]。肝癌早期缺乏典型癥狀、惡性程度高、侵襲性強、易轉移復發,多數患者確診時常處于中晚期,這與相關免疫細胞調控HCC快速增殖、侵襲和早期轉移等復雜免疫機制有關,使得總體預后較差[4]。迫切需要深入了解HCC的免疫發病機制并采用更加有效的治療措施。近年,免疫治療在癌癥治療中展現了較高的潛力。HCC作為一種免疫原性癌癥,免疫治療有望提高HCC患者的生存率。補體系統作為先天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在免疫治療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具有顯著的潛在應用價值。筆者現就補體系統在HCC免疫治療方面的應用進展及前景作一綜述。
1 補體系統及它在癌癥中的免疫調節作用
人類補體系統由大約50種蛋白質和蛋白片段組成,包括補體固有成分、補體調節蛋白及補體受體,主要存在于血液或淋巴液循環(主要由肝臟分泌),它是人體先天性免疫反應的關鍵組成部分,可通過一系列相互作用的蛋白質參與到免疫反應,在調節肝損傷、炎癥、再生反應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5]。
補體系統的激活是高度受控的,可防止對自體組織的損傷,主要通過3種途徑發生:經典途徑(CP)、凝集素途徑(LP)和旁路途徑(AP),這3條途徑又共同合并成末端途徑,以激活C3。免疫細胞表達的過敏毒素(包括C3a、C4a、C5a)與C3片段的特異性受體相互作用,從而將補體激活與免疫細胞功能調節聯系在一起。
早前普遍認為,補體系統有助于免疫監視癌癥,幫助身體識別和清除惡性轉化的細胞。然而2008年Markiewski等[6]在小鼠宮頸癌TC-1同基因模型小鼠皮下注射TC-1腫瘤細胞后發現,靶向敲除補體C3或C4基因片段的小鼠逃避了腫瘤的侵害,結果提示,在某些情況下,抑制補體成分的激活可能會延緩腫瘤的發展。另有多項研究[7-9]表明,補體成分有助于調節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功能,并在某些條件下通過發揮免疫調節作用增強抗腫瘤功能,但它也與腫瘤細胞增殖和再生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這些研究成果為補體成分的免疫調節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礎。
補體系統是抗腫瘤免疫反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它作為人體一種內在效應機制協調著先天免疫反應和適應性免疫反應,從而促進或抑制腫瘤的發展[10]。在多種實體瘤中,補體系統的激活對調節TME中的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起到關鍵作用[11],而肝臟內的補體激活可能會通過多種機制促進HCC的發展,如肝內補體激活可能通過激活Kupffer細胞中的核因子-κB和肝細胞中的信號轉導因子和轉錄激活因子3促進HCC的發展[12]。因此,抑制腫瘤補體成分的激活可能有助于增強腫瘤免疫治療的療效。
2 補體系統在HCC免疫機制中的作用
2.1 HCC的免疫發病機制
肝臟內部的免疫調節和穩態由自然殺傷細胞、自然殺傷T細胞、γδ T細胞、Kupffer細胞等共同參與和維護[1]。然而慢性病毒感染、酗酒等危險因素可破壞肝臟內部的免疫穩態,從而導致肝炎、肝硬化等肝癌先兆疾病的發生[13];另外,自然殺傷細胞、自然殺傷T細胞、樹突狀細胞、腫瘤相關巨噬細胞、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髓源性抑制細胞等免疫細胞以及由這些細胞產生的趨化因子共同作用于TME,起著抑制或促進肝癌的發生和進展的作用[14];另一方面,HCC相關炎癥會導致基因組不穩定、癌細胞增殖、抗凋亡途徑增強,最終導致腫瘤擴散[15],而補體系統在HCC相關炎癥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補體成分通過啟動和放大炎癥反應、促進免疫細胞浸潤及調控細胞因子釋放,從而影響HCC的發生和發展[16]。由于補體系統在HCC相關炎癥中的調節作用,補體成分可能成為新的免疫治療靶點,如抑制補體活性可能減少有害的炎癥反應,而促進特定補體成分活性可能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17]。近年來,免疫因子、可溶性效應分子和趨化因子受體作為治療HCC的潛在靶點引起了廣泛關注,當前的免疫療法主要依賴于調節適應性免疫反應,因此,探索涉及先天性免疫的新機制可能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在這方面,補體系統成分的免疫調節已成為肝癌免疫治療領域的重要研究方向。
2.2 補體系統成分調節在HCC中的治療前景
研究[18]表明,補體激活可以通過增強血管生成、保護腫瘤細胞免受免疫監視、增加有絲分裂信號、激活抗凋亡機制和異常細胞增殖、侵襲和遷移來促進HCC。此研究結果提示,補體系統在HCC免疫治療中可能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并為未來利用補體聯合治療HCC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補體聯合治療雖在其他疾病中進行了初步探索,但在HCC治療的研究尚需要深入研究。直到最近,補體系統其中幾種成分在癌癥免疫抑制中的作用引起了研究者們的廣泛關注,而它們在HCC免疫調節中的作用也已經被發現,它們在HCC免疫機制中的作用及其治療前景也已有初步研究成果。
2.2.1 補體固有成分
2.2.1.1 C1q
C1q是補體C1復合物的重要組成部分,負責啟動補體激活的經典途徑[19]。研究[20]表明,C1q和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相關蛋白1(C1q and TNF related 1,C1qTNF1)已被確定為HCC的主要動態網絡生物標志物基因,發揮著抑制HCC侵襲和轉移的核心作用,C1qTNF1通過調節與血小板相關的腫瘤信號傳導途徑,為HCC治療提供了新的治療靶點;另有研究者[21]報道,C1qTNF6在HCC組織中特異性高表達,抑制C1qTNF6表達能夠使Akt信號通路失活,阻止腫瘤細胞的存活、遷移和侵襲,并促進HCC細胞凋亡。C1q能誘導膠原受體盤狀結構域受體1(disidin domain receptor 1,DDR1)的激活和上調,增強HepG2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能力,這與C1q誘導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又名Akt)PI3K/Akt信號的激活,并增加基質金屬蛋白酶-2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的表達相關,強烈提示了C1q-DDR1在促進HCC進展中的作用[22]。目前有研究[23]發現,使用C1q抑制劑可以有效調節β-連環蛋白途徑的激活,預防慢性肝炎患者的腫瘤進展。在用于治療不可切除HCC的免疫藥物中,如納武利尤單抗(nivolumab)和帕博利珠單抗(pembrolizumab),由于它們與補體C1q和Fc受體的親和力,在發揮抗腫瘤作用的同時,還能誘導補體激活,增強免疫反應[24]。美國FDA批準用于治療遺傳性血管性水腫的C1抑制劑已被證明可通過抑制C1q阻斷經典激活途徑,減少過度的補體活化,防止自身免疫反應導致的組織損傷[25]。以上結果提示,利用C1q抑制劑可以調控補體經典途徑的活性,減少炎癥反應,潛在地為HCC的治療提供了一種新的策略,但關于C1q在HCC免疫中的作用還需要更多研究確定其是否具有保護性或致病性。
2.2.1.2 C3
補體系統的核心成分C3在補體激活的經典途徑和旁路途徑中均發揮重要作用[26]。有研究[27]表明,肝星狀細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產生的C3通過影響樹突狀細胞的成熟和擴增腫瘤相關的骨髓來源抑制性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促進HCC的發生及發展。然而,補體C3缺陷的造血干細胞不能誘導MDSCs擴增,這與HSCs衍生因子B和因子D相關,導致C3裂解為iC3b和C3d,iC3b的加入促進了免疫抑制性MDSCs的分化[28]。在HCC中,MDSCs還具有促進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的作用[29]。以上研究為同時靶向C3和MDSCs治療HCC的未來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在細胞內補體C3的激活可顯著抑制CD8+ T細胞的抗腫瘤活性,增強T細胞衰竭,促進M2巨噬細胞的形成,導致腫瘤細胞對抗程序性死亡蛋白配體 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1,PD-L1)治療產生抗性,使這種抗腫瘤免疫療法失效[30]。因此,阻斷腫瘤細胞衍生的C3可通過增強抗PD-L1治療的功效,從而增強抗腫瘤能力,這表明C3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聯合治療將會是HCC的潛在治療策略。
2.2.1.3 甘露糖結合凝集素(mannose-binding lectin,MBL)
MBL是補體激活凝集素途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免疫調節和腫瘤發生中起著關鍵作用[31]。大多數哺乳動物有兩種類型的MBL(MBL1和MBL2),其中MBL2參與先天免疫及其免疫調節[32]。MBL作為肝臟合成和分泌的一種特異性蛋白,它在HCC的發生及發展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Liao等[33]利用GSEA探索了MBL2影響HCC進展的潛在機制發現,MBL2低表達與多種通路激活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包括細胞周期、DNA復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信號通路和癌癥干細胞相關通路,此外,經過體內和體外實驗后證實,MBL2低表達可增強肝癌細胞的致癌能力;另一方面,MBL2高表達水平與抗腫瘤免疫細胞相關,包括自然殺傷細胞和CD8+ T細胞[34]。提示MBL在HCC免疫治療靶點方面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盡管之前有研究者認為,MBL2的基因多態性與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相關性HCC或單純性HCC之間無相關性,但Su等[35]的研究證實了MBL2基因突變是HCC患者的易感因素,而單核苷酸多態性(rs11003123)可能是中國人群發生HCC的潛在危險因素。在HCC小鼠模型研究[36]中,相對于野生型小鼠,MBL遺傳缺失促進了HCC的進展,恢復MBL表達后的小鼠抑制了HCC的進展,這可能與MBL下調ERK/COX-2/PGE2信號通路抑制肝星狀細胞活化有關。以上結果證明了MBL高表達具有抗腫瘤功能,可抑制HCC進展,靶向MBL治療將有助于開發新的策略提高肝癌免疫治療的有效性。
2.2.2 補體調節蛋白
2.2.2.1 補體因子H(complement factor H,CFH)
CFH主要參與調節旁路途徑的補體激活,而旁路途徑中補體的缺失會引起異常炎癥,從而導致腫瘤的發生。有研究[37]發現,CFH缺陷小鼠的肝臟內出現了自發的補體激活,缺乏 CFH 的小鼠會自發發展為HCC,這提示了CFH在控制肝臟補體激活方面具有關鍵作用,并且缺乏CFH可能會促進慢性炎癥和HCC的發展;并且還發現,CFH突變和CFH mRNA水平與HCC患者生存預后相關。Hyang Sook Seol等[38]發現CFH和C7可以刺激淋巴樣增強因子-1(LSF-1)的表達,導致干燥因子上調,最終增加癌癥的干燥程度。然而,C7和CFH促進淋巴樣增強因子-1表達的具體機制尚不清楚,深入研究這種機制有望為HCC治療提供一種逆轉腫瘤耐藥的新方法。另有研究[39]表明,CFH相關蛋白家族補體因子H相關蛋白3(Complement factor H-related 3,CFHR3)是補體調節炎癥反應的關鍵因素,CFHR3的表達調控與Wnt和NOTCH信號通路的激活以及肝癌發生、細胞增殖有關。此外,有較多研究鑒于CFHR3構建了較多相關模型,在優化HCC患者診斷、預后評估和免疫治療選擇方面具有巨大潛力,比如Chen等[40]基于CFHR3等基因構建的干細胞相關模型可以預測HCC患者的預后、免疫基因組表達及對化療藥物的反應,并在高風險模型中觀察到巨噬細胞等免疫細胞及免疫檢查點的比例相較于低風險模型呈顯著增加;同樣Ruan等[41]發現,基于CFHR3等基因所構建的炎性相關鐵死亡預測模型在免疫檢查點抑制治療中有較高的應答率。以上結果提示CFH 和CFHR3表達調控與HCC預后密切相關,可作為HCC新的免疫治療靶點,并且基于CFHR3構建的預測模型在HCC患者的預后、免疫基因組表達及對化療藥物的反應方面具有良好的預測性。
2.2.2.2 C4B
C4B作為C3和C5轉化酶的關鍵組分,在補體系統經典途徑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42]。它不僅參與了補體級聯反應的傳播,而且具有多個輔助因子,如C4BPA和C4BPB,可以通過水解C4B并解離C4B2A復合物以抑制補體激活。一項研究發現,在HCC患者血漿的小細胞外囊泡中,C1QB、C1QC、C4BPA和C4BPB的表達上調,這也表明C1QB、C1QC、C4BPA和C4BPB可能是潛在的治療靶點[43]。作為HCC前兆的HCV感染患者進展為HCC的風險更大,需要一種敏感性更高的特異性生物標志物。Dalal等[44]發現,C4B水平升高是HCV相關終末期肝病患者的可靠標志物。因此,補體C4B直接參與HCC免疫反應的生物學調控,以及作為生物標志物區分患者群體的差異表達能力,表明補體C4B是HCC疾病調節和治療靶向的重要靶點。
2.2.2.3 CD46
CD46是一種在細胞表面表達的膜結合補體調節蛋白,具有抑制補體系統過度激活及保護組織免受損傷的作用;除了作為膜結合補體調節蛋白的作用外,它還在調節T細胞介導的免疫應答中發揮關鍵作用[45]。當肝臟受損時,肝臟會產生纖維化,這些成纖維細胞是由活化的HSCs分化形成的,HSCs從失活狀態到活化狀態的主要調節因子是CD46[46]。Liu等[47]發現,CD46的單核苷酸多態性(rs2796267)通過修飾啟動子活性增加了HCC的易感性和疾病結局的風險,還發現,單核苷酸多態性(rs2796267)的AG/GG基因型與接受切除手術的HCC患者不良預后相關。早有研究發現,HCC細胞系和臨床樣本都表達了高水平的CD46,通過使用靶向CD46、SG635-p53的新型纖維嵌合溶瘤腺病毒,在Hep-3B皮下異種移植肝癌模型中顯示出抗腫瘤活性,顯著抑制了易感小鼠體內的肝癌進展、提高了生存率,并促進了腫瘤的消退[48]。以上結果提示CD46調節腫瘤微環境中T細胞介導的免疫應答,并可激活HSCs,深入了解CD46有助于在HCC腫瘤微環境調控中發現重要作用;此外,深入研究靶向CD46、SG635-p53的新型纖維嵌合溶瘤腺病毒治療HCC的機制將為臨床上HCC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療策略。
2.2.2.4 CD59
CD59是一種細胞膜上的蛋白質,也被稱為細胞膜攻擊復合物(MAC)結合蛋白,可以抑制MAC的形成,保護細胞免受免疫系統的攻擊[49]。一些研究正在探索通過調控CD59表達或功能來治療HCC的方法。例如,通過抑制CD59的表達或功能,可以增強免疫系統對肝癌細胞的殺傷作用,從而提高對HCC的免疫治療效果[50]。Abdel-Latif等[51]在二乙基亞硝胺誘導的HCC大鼠模型中發現CD59的mRNA和蛋白表達增加,并促進了腫瘤的生長,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發現還輔酶Q10可能通過增加脂質含量、降低CD59表達和PLD活性起到抗腫瘤的作用。Lan等人[52]研究表明,CD59可能是HCC潛在的致癌驅動因素,并且發現CD59的高表達與HCC患者較差的總生存率和無病生存率相關。這可能與CD59的缺失通過過量的Smad7形成和Smad2/3磷酸化的消除,損害了體內、外的致瘤性和轉移能力有關。以上結果提示,通過抑制CD59表達可增強抗腫瘤能力而提高對HCC的免疫治療效果,可以作為HCC潛在的治療靶點。
2.2.3 補體受體
補體成分C5是補體級聯末端不可或缺的組成成分。C5激活后產生的C5a是一種過敏毒素和白細胞趨化物質,通過促進癌細胞的轉移在TME中發揮關鍵作用[53]。研究[54]表明,補體C5a受體(C5aR1)的自分泌激活可促進肝癌細胞的侵襲和轉移,導致細胞周期G0/G1期阻滯和細胞凋亡,并抑制增殖細胞核抗原(PCNA)和Ki-67(一種增殖細胞的相關抗原)的表達。在肝癌細胞中,C5a-C5aR1軸通過上調轉錄因子Snail表達以及下調緊密連接蛋白-1(Claudin-1)和鈣粘蛋白E(E-cadherin)表達來誘導上皮細胞-間充質轉化(EMT)[55]。Lin等[56]研究發現C5aR1在HBV相關肝癌細胞中高度表達。通常來說,抗腫瘤治療的最大問題是免疫治療的耐藥性,根據以往的ICIs使用經驗,補體抑制藥物與其他療法聯合使用或許可以解決這一難題。有研究表明,C5aR1抑制劑聯合紫杉醇能夠促進干擾素-γ(IFN-γ)陽性巨噬細胞的重編程,使它從促腫瘤的M2型轉變為抗腫瘤的M1型,增加TME中CXCR3效應細胞和記憶CD8+ T細胞的數量和細胞毒性,從而提高紫杉醇化療的療效和敏感性[57]。另外,C5aR1抑制劑聯合替莫唑胺治療膠質母細胞瘤時可誘導DNA損傷和腫瘤細胞凋亡,增強替莫唑胺化療的敏感性[58]。有研究發現,聯合抑制C5a和PD-L1信號通路可能有助于抗腫瘤治療的協同作用[59],因為聯合阻斷C5a和PD-L1影響TME中MDSCs的數量,降低免疫抑制功能,增加腫瘤浸潤CD8+ T細胞的數量,促進內源性白細胞介素-10(IL-10)的產生,從而增強抗腫瘤功能[60]。這些數據都表明了C5aR1抑制劑在抗腫瘤治療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可作為治療HCC的候選藥物。補體相關療法與其他抗腫瘤免疫治療的聯合應用存在一定的風險和益處,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鑒于補體分子在調節HCC免疫機制中的作用,補體系統的各種分子可被視為HCC患者潛在的免疫治療靶點。
3 總結
補體系統協調著先天性免疫系統和適應性免疫系統,通過激活免疫細胞,在影響HCC免疫發病機制中至關重要。根據目前對各補體成分作為致癌驅動因素的認識,可以獨立開發補體抑制劑等相關靶向治療或者與目前一線和二線HCC免疫治療聯合應用。總之,更深入地了解補體系統在致瘤和抗腫瘤機制中的作用,并結合先進的生物信息學方法,有望促進HCC更加有效的臨床免疫治療設計和開發。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劉校伸負責論文的設計與撰寫;王志鑫負責文獻分析;王灝和杜磊負責數據整理;任利負責論文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