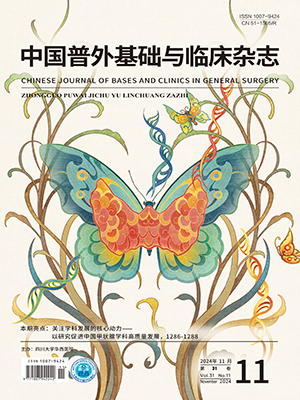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第3大常見惡性腫瘤和第2大癌癥死亡原因[1],在中國,CRC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也在不斷上升,疾病負擔日益沉重[2]。結直腸腺瘤(colorectal adenoma,CRA)被廣泛認可為CRC的一種癌前病變,80%~95%的CRC由CRA發展而來[3-4],其演變為CRC大多以腺瘤-癌序列途徑發展[5],演變時間為5~15年。CRA的發生尚無明確的相關因素和發展機制。因此,深入研究CRA的發生發展機制及其相關因素,對于預防CRC和降低其發病率具有重要意義。
1 CRA的組織分型
結腸息肉是一種生長在結腸黏膜表面的贅生物,組織學主要分為兩大類即非腫瘤性息肉(如錯構瘤性、增生性及炎性息肉)和腫瘤性息肉(如腺瘤性和鋸齒狀病變)。CRA被定義為結直腸黏膜上皮的腫瘤性增生。 根據病理學分型,腺瘤主要包括管狀腺瘤、絨毛狀腺瘤、絨毛-管狀腺瘤和鋸齒狀腺瘤。管狀腺瘤由分支的小管組成,絨毛狀腺瘤包含在葉狀體中排列的指狀絨毛,而絨毛-管狀腺瘤同時含有這兩種成分。鋸齒狀腺瘤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腺瘤,包括傳統的鋸齒狀腺瘤和芽生型鋸齒狀腺瘤。與傳統腺瘤相比,鋸齒狀腺瘤惡變風險概率更高[6]。
2 CRA的發生機制
2.1 炎癥與CRA
炎癥通過細胞信號轉導的改變、間質細胞的活化、炎癥微環境的形成等機制促進CRA的進展[7-8]。在炎癥狀態下,間質細胞和免疫細胞(如巨噬細胞和T淋巴細胞)被激活,釋放多種促炎細胞因子刺激細胞的生長和發展,影響DNA復制和修復機制,從而增加腺瘤細胞突變的可能。如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 NF-κB)和信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因子3,這些免疫因子可能直接導致DNA損傷,并在細胞水平上影響DNA復制和修復機制,進而增加腺瘤細胞突變的可能,誘發腺瘤生長[9]。炎癥引發的微環境變化包括腸道黏膜的屏障功能受損、免疫細胞浸潤增加以及細胞間相互作用的改變,為腺瘤的生長發展提供了一個更適宜的環境。一項Meta分析研究了阿司匹林等非甾體抗炎藥(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預防CRA復發的效果[10]:使用NSAIDs如阿司匹林可能通過抑制炎癥反應來減少腺瘤的復發和進展,特別是低劑量的阿司匹林被發現在某些情況下比高劑量的阿司匹林或選擇性環氧合酶-2抑制劑更有效,這提示了通過調節炎癥反應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抑制腺瘤的發展。因此,研究炎癥與腫瘤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于開發新的治療策略和預防措施具有重要意義。
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是一種參與炎癥反應的多功能細胞因子,調節細胞增殖、分化、遷移及細胞外基質合成和降解。 Tsumuraya等[11]研究揭示了TGFβ在CRA發生中的關鍵作用。其可能機制為:在炎癥條件下,TGFβ被激活并與受體結合,啟動Smad依賴和非依賴信號,激活成纖維細胞和肌成纖維細胞,促進其增殖和遷移,并增加膠原蛋白和纖維連接蛋白的產生,改變腺瘤微環境。此外,TGFβ還能促進巨噬細胞和T淋巴細胞積聚,釋放的細胞因子進一步激活間質細胞,形成促炎和促腫瘤環境。最終,這些變化支持腺瘤的進一步發展和惡性轉變。
2.2 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與CRA
基因突變是CRA發生發展的關鍵驅動因素。這些突變影響控制細胞周期、細胞增殖和凋亡的關鍵基因,如腫瘤抑制基因和原癌基因,從而導致細胞行為異常和腫瘤進展。腺瘤向CRC的發展過程涉及染色體變異,此過程的特征包括K-Ras激活、抑癌基因APC突變和p53的失活,以及18號染色體長臂的雜合性喪失[12-13]。尤其是p53基因的突變加速了腺瘤細胞的增殖,引發細胞周期改變,從而迅速推動了癌變過程[14]。CRA向癌變的過程還涉及染色體不穩定性、微衛星不穩定性、CpG島DNA甲基化等多種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15]。 Abolghasemi Fard等[16]的研究通過深入分析表觀遺傳改變和遺傳路徑,揭示了這些改變在CRC及其前驅病變腺瘤中的作用,特定的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包括DNA甲基化和組蛋白修飾,與CRA的進展密切相關,這些改變通過影響細胞增殖和存活的信號通路,加速了腺瘤細胞向癌變的轉變。
2.3 腸道菌群與CRA
腸道菌群由腸道微生物群及其腸道環境組成,腸道微生物群由至少100萬億個細菌組成,是人類細胞總數的10倍,包含1 000多個物種,數量極其龐大。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生物生態失衡是CRC及其癌前病變發展的關鍵環境因素[17-18]。正常的菌群有助于抗氧化和抗炎機制的平衡,維持黏膜完整性,失調的菌群可能導致這一平衡被破壞,使得腸道內的炎癥和氧化應激水平升高,導致Wnt信號組件的差異表達、黏膜破損、代謝產物異常及致癌物質增加,減緩黏膜細胞修復速度[19],為CRA的發展提供基礎。CRA患者的腸道菌群組成與健康人顯著不同,梭桿菌被認為是CRA相關的重要細菌,其豐度從健康個體到CRA再到CRC逐漸增加,豐度與息肉組織發育不良程度呈正相關[20]。此外,益生菌如雙歧桿菌的減少和潛在致病菌如假單胞菌的增加,也與CRA的發生密切相關[21]。飲食結構的改變、腸道感染、抗生素使用、免疫缺陷和心理壓力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菌群失調[22]。如長期高脂肪和低膳食纖維飲食會降低膽汁分泌,導致菌群失調[23];腸道微生物中芽孢桿菌和梭桿菌會破壞正常腸壁細胞,激活致癌信號通路,產生促瘤代謝物,抑制抗腫瘤免疫反應,直接或間接促進CRA和CRC的發生[24-25]。腸道菌群同時與免疫系統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失調的菌群還可能觸發異常的免疫反應,導致慢性炎癥狀態。這種免疫系統的過度激活可能成為CRA形成的關鍵因素。腸道微生物群失衡導致免疫微環境紊亂,增加CD204+ 腫瘤相關巨噬細胞、Foxp3+ T調節性細胞和恒定自然殺傷T細胞的數量,從而促進腺瘤的發生[26]。此外,腸道微生物群失衡還會導致代謝產物的變化,如短鏈脂肪酸、丁酸、共軛亞油酸和共軛亞麻酸的減少,以及膽汁酸的增加,這些變化都可能促進腺瘤的發生[24]。腺瘤的發生可能反過來導致微生物群失衡,而局部微生物群紊亂繼而反過來促進腺瘤的進展,最終共同促進癌癥的發生。綜上,腸道菌群失衡、炎癥反應、免疫調節等在CRA和CRC的發生發展中相互促進并起關鍵作用。
2.4 脂質代謝與CRA
脂質由脂肪酸、甘油三酯、膽固醇、膽固醇酯、磷脂和鞘脂組成,廣泛分布于細胞中。脂質形成細胞膜并作為細胞的能量來源。脂質還充當第二信使,傳遞信號并介導細胞生長、增殖、凋亡和死亡[27]。一項Meta 分析[28]表明,高水平的血清甘油三酯、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與CRA呈顯著的正相關。 還有研究[29]發現,代謝相關性脂肪性肝病和中心性肥胖與CRA和高危腺瘤的發生及風險增加獨立相關。在探索CRA發展的分子機制中,脂質代謝、肥胖和代謝綜合征通過多種機制共同作用促進腺瘤的發生。這些機制包括代謝重編程、慢性炎癥、胰島素抵抗、腸道微生物群失調等[30]。既往研究顯示[31], CRA細胞通常表現出脂肪酸合成的顯著增加。此外,膽固醇代謝的異常,特別是關鍵酶羥甲基戊二酰輔酶A還原酶的表達增加,也與腺瘤的生長密切相關[32]。短鏈脂肪酸的產生和膽汁酸的轉化,通過調節炎癥反應和細胞增殖途徑如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號通路和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促進或抑制腺瘤的發展[33]。既往還有學者認為,攝入大量飽和脂肪酸可能導致肥胖、代謝相關基因的影響和胰島素抵抗,這可能通過激活Toll 受體 4和脂多糖受體來誘導巨噬細胞NF-κB信號通路以及環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的表達來實現。這一過程促進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 F2,PGF2)的生成,PGF2是促炎介質,進而可能增加CRA的發生風險[34]。因此,針對脂質代謝途徑的干預,包括生活方式的調整和代謝途徑的靶向治療,提示通過調節脂質代謝來干預CRA可能是一個有益的治療策略。
2.5 CRA相關生物標志物
在CRA研究中,其生物分子標志物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Ki-67、p53、活化蛋白C等過表達已被證實與腺瘤細胞增殖和癌變過程密切相關[35]。Ahmed Nor 等[35]研究發現,EGFR和Ki-67在腺瘤中過表達,尤其是絨毛狀成分和高度異常增生的腺瘤,與腺瘤相比,CRC患者EGFR和Ki-67 LI過表達水平更高,且二者在CRC中的表達顯著相關;此外,CRC的組織學分級和浸潤與EGFR和Ki-67過表達密切相關,可能預示患者的轉移風險。Wang等[36]研究通過分析TCGA和GEO數據庫中的基因表達數據,發現了與CRA發展和進展相關的關鍵差異表達基因,發現碳酸酐酶2和11β-羥類固醇脫氫酶2是與CRA進展密切相關的關鍵基因。此外,該研究發現了與CRA相關的生物功能通路,如DNA修復、E2F、MYC、mTORC1、糖酵解和有絲分裂紡錘等,并證實了這些基因的表達水平與結直腸腺瘤的分級和預后的相關性,為進一步理解CRA的發病機制和尋找新的治療靶點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肖博等[37]采用實時定量PCR和免疫組化方法,探討兒茶酚胺氧位甲基轉移酶(catechol O-methyltransferase,COMT)mRNA及其蛋白在CRA及其瘤旁組織和CRC 及其癌旁組織中的表達情況,結果發現COMT在CRA及CRC組織中的表達較相應的瘤(癌)旁組織均升高,其可能在CRC的發生和發展中具有一定作用。綜上,這些生物分子標志物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CRA的病理機制,提高對患者的診斷準確性和治療個體化水平。然而,這些結果仍需在更大樣本量和臨床實踐中進行驗證。
2.6 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與CRA
Hp 是近年來臨床研究的熱點,盡管Hp感染引起CRA的機制尚不清楚,但多項研究表明Hp感染與CRA的發生有顯著關聯。一項Meta分析[38]系統地評估了Hp感染與結直腸息肉及其不同組織學類型之間的相關性,其結果表明,Hp感染與腺瘤、晚期腺瘤和增生性息肉具有獨立相關性,該結果為Hp感染作為結直腸息肉發生的潛在危險因素提供了理論依據。Hp可分泌多種毒力因子,這些毒力因子可作用于黏膜,維持Hp的持續感染,導致組織損傷和慢性炎癥反應。有文獻[39]表明,Hp感染引起的胃泌素分泌增加與CRA有關,胃泌素是一種主要由胃竇和十二指腸的G細胞分泌的胃腸激素,胃泌素不僅可以直接創造適宜的微環境促進腸腺瘤的發生,還可以通過胃泌素受體介導的增殖信號間接促進腸腺瘤的形成。Hp感染可引起腸道內分泌異常,進而誘導血漿胃泌素17和COX-2的表達,從而滋養腸黏膜,刺激腸黏膜增生,促進息肉生長。莊肇朦等[40] 的研究證實了CRA患者腺瘤組織中Hp的富集現象,并揭示了Hp感染與CRA Hp富集之間的相關性,指出Hp富集與腺瘤的臨床、病理特征及生物學行為之間存在關聯,同時提出腸道中的Hp可能是通過上調腺瘤組織內Toll樣受體5蛋白表達來介導促炎反應,從而啟動異常免疫應答,促進CRA的發生。綜上,Hp感染作為CRA發生的潛在危險因素,早期檢測和治療Hp感染可能有助于預防CRA及其進展為CRC。
3 小結與展望
CRA的發生涉及因素包括炎癥、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腸道菌群失調、脂質代謝異常等。這些因素通過不同的機制相互作用共同促進CRA的發生和發展。而一旦CRA演變為CRC,患者的預后明顯惡化,極大地影響了生活質量。在CRC的防治中,早期預防和篩查CRA顯得尤為重要。然而,我國全面普及結腸鏡篩查面臨一系列困難,包括腸道準備不充分、設備水平參差不齊以及醫師主觀判斷的差異,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CRA的檢出率。考慮到很多CRA患者在早期并沒有明顯癥狀,有必要對高危人群進行有針對性的篩查。因此,迫切需要深入研究CRA的分子機制、分子標志物及臨床應用,以便制定更為精準和有效的篩查策略。通過有目的性的結腸鏡檢查和治療,及時干預CRA的發生和發展,有望在早期階段就降低CRC的發病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質量。這一方面需要加強科研,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強公眾健康意識的提升,使更多的人能夠受益于早期篩查和干預。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 李兵、王士旭和劉藝行:主要負責文章的選題、文獻檢索與篩選、數據整理與分析,以及初稿的撰寫與修訂。王朝陽:參與文章的選題、文獻篩選與數據整理工作,對初稿進行了細致的審閱與修改,確保文章內容的準確性和深度。所有作者均對文章內容負責。
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第3大常見惡性腫瘤和第2大癌癥死亡原因[1],在中國,CRC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也在不斷上升,疾病負擔日益沉重[2]。結直腸腺瘤(colorectal adenoma,CRA)被廣泛認可為CRC的一種癌前病變,80%~95%的CRC由CRA發展而來[3-4],其演變為CRC大多以腺瘤-癌序列途徑發展[5],演變時間為5~15年。CRA的發生尚無明確的相關因素和發展機制。因此,深入研究CRA的發生發展機制及其相關因素,對于預防CRC和降低其發病率具有重要意義。
1 CRA的組織分型
結腸息肉是一種生長在結腸黏膜表面的贅生物,組織學主要分為兩大類即非腫瘤性息肉(如錯構瘤性、增生性及炎性息肉)和腫瘤性息肉(如腺瘤性和鋸齒狀病變)。CRA被定義為結直腸黏膜上皮的腫瘤性增生。 根據病理學分型,腺瘤主要包括管狀腺瘤、絨毛狀腺瘤、絨毛-管狀腺瘤和鋸齒狀腺瘤。管狀腺瘤由分支的小管組成,絨毛狀腺瘤包含在葉狀體中排列的指狀絨毛,而絨毛-管狀腺瘤同時含有這兩種成分。鋸齒狀腺瘤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腺瘤,包括傳統的鋸齒狀腺瘤和芽生型鋸齒狀腺瘤。與傳統腺瘤相比,鋸齒狀腺瘤惡變風險概率更高[6]。
2 CRA的發生機制
2.1 炎癥與CRA
炎癥通過細胞信號轉導的改變、間質細胞的活化、炎癥微環境的形成等機制促進CRA的進展[7-8]。在炎癥狀態下,間質細胞和免疫細胞(如巨噬細胞和T淋巴細胞)被激活,釋放多種促炎細胞因子刺激細胞的生長和發展,影響DNA復制和修復機制,從而增加腺瘤細胞突變的可能。如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 NF-κB)和信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因子3,這些免疫因子可能直接導致DNA損傷,并在細胞水平上影響DNA復制和修復機制,進而增加腺瘤細胞突變的可能,誘發腺瘤生長[9]。炎癥引發的微環境變化包括腸道黏膜的屏障功能受損、免疫細胞浸潤增加以及細胞間相互作用的改變,為腺瘤的生長發展提供了一個更適宜的環境。一項Meta分析研究了阿司匹林等非甾體抗炎藥(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預防CRA復發的效果[10]:使用NSAIDs如阿司匹林可能通過抑制炎癥反應來減少腺瘤的復發和進展,特別是低劑量的阿司匹林被發現在某些情況下比高劑量的阿司匹林或選擇性環氧合酶-2抑制劑更有效,這提示了通過調節炎癥反應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抑制腺瘤的發展。因此,研究炎癥與腫瘤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于開發新的治療策略和預防措施具有重要意義。
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是一種參與炎癥反應的多功能細胞因子,調節細胞增殖、分化、遷移及細胞外基質合成和降解。 Tsumuraya等[11]研究揭示了TGFβ在CRA發生中的關鍵作用。其可能機制為:在炎癥條件下,TGFβ被激活并與受體結合,啟動Smad依賴和非依賴信號,激活成纖維細胞和肌成纖維細胞,促進其增殖和遷移,并增加膠原蛋白和纖維連接蛋白的產生,改變腺瘤微環境。此外,TGFβ還能促進巨噬細胞和T淋巴細胞積聚,釋放的細胞因子進一步激活間質細胞,形成促炎和促腫瘤環境。最終,這些變化支持腺瘤的進一步發展和惡性轉變。
2.2 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與CRA
基因突變是CRA發生發展的關鍵驅動因素。這些突變影響控制細胞周期、細胞增殖和凋亡的關鍵基因,如腫瘤抑制基因和原癌基因,從而導致細胞行為異常和腫瘤進展。腺瘤向CRC的發展過程涉及染色體變異,此過程的特征包括K-Ras激活、抑癌基因APC突變和p53的失活,以及18號染色體長臂的雜合性喪失[12-13]。尤其是p53基因的突變加速了腺瘤細胞的增殖,引發細胞周期改變,從而迅速推動了癌變過程[14]。CRA向癌變的過程還涉及染色體不穩定性、微衛星不穩定性、CpG島DNA甲基化等多種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15]。 Abolghasemi Fard等[16]的研究通過深入分析表觀遺傳改變和遺傳路徑,揭示了這些改變在CRC及其前驅病變腺瘤中的作用,特定的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包括DNA甲基化和組蛋白修飾,與CRA的進展密切相關,這些改變通過影響細胞增殖和存活的信號通路,加速了腺瘤細胞向癌變的轉變。
2.3 腸道菌群與CRA
腸道菌群由腸道微生物群及其腸道環境組成,腸道微生物群由至少100萬億個細菌組成,是人類細胞總數的10倍,包含1 000多個物種,數量極其龐大。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微生物生態失衡是CRC及其癌前病變發展的關鍵環境因素[17-18]。正常的菌群有助于抗氧化和抗炎機制的平衡,維持黏膜完整性,失調的菌群可能導致這一平衡被破壞,使得腸道內的炎癥和氧化應激水平升高,導致Wnt信號組件的差異表達、黏膜破損、代謝產物異常及致癌物質增加,減緩黏膜細胞修復速度[19],為CRA的發展提供基礎。CRA患者的腸道菌群組成與健康人顯著不同,梭桿菌被認為是CRA相關的重要細菌,其豐度從健康個體到CRA再到CRC逐漸增加,豐度與息肉組織發育不良程度呈正相關[20]。此外,益生菌如雙歧桿菌的減少和潛在致病菌如假單胞菌的增加,也與CRA的發生密切相關[21]。飲食結構的改變、腸道感染、抗生素使用、免疫缺陷和心理壓力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菌群失調[22]。如長期高脂肪和低膳食纖維飲食會降低膽汁分泌,導致菌群失調[23];腸道微生物中芽孢桿菌和梭桿菌會破壞正常腸壁細胞,激活致癌信號通路,產生促瘤代謝物,抑制抗腫瘤免疫反應,直接或間接促進CRA和CRC的發生[24-25]。腸道菌群同時與免疫系統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失調的菌群還可能觸發異常的免疫反應,導致慢性炎癥狀態。這種免疫系統的過度激活可能成為CRA形成的關鍵因素。腸道微生物群失衡導致免疫微環境紊亂,增加CD204+ 腫瘤相關巨噬細胞、Foxp3+ T調節性細胞和恒定自然殺傷T細胞的數量,從而促進腺瘤的發生[26]。此外,腸道微生物群失衡還會導致代謝產物的變化,如短鏈脂肪酸、丁酸、共軛亞油酸和共軛亞麻酸的減少,以及膽汁酸的增加,這些變化都可能促進腺瘤的發生[24]。腺瘤的發生可能反過來導致微生物群失衡,而局部微生物群紊亂繼而反過來促進腺瘤的進展,最終共同促進癌癥的發生。綜上,腸道菌群失衡、炎癥反應、免疫調節等在CRA和CRC的發生發展中相互促進并起關鍵作用。
2.4 脂質代謝與CRA
脂質由脂肪酸、甘油三酯、膽固醇、膽固醇酯、磷脂和鞘脂組成,廣泛分布于細胞中。脂質形成細胞膜并作為細胞的能量來源。脂質還充當第二信使,傳遞信號并介導細胞生長、增殖、凋亡和死亡[27]。一項Meta 分析[28]表明,高水平的血清甘油三酯、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與CRA呈顯著的正相關。 還有研究[29]發現,代謝相關性脂肪性肝病和中心性肥胖與CRA和高危腺瘤的發生及風險增加獨立相關。在探索CRA發展的分子機制中,脂質代謝、肥胖和代謝綜合征通過多種機制共同作用促進腺瘤的發生。這些機制包括代謝重編程、慢性炎癥、胰島素抵抗、腸道微生物群失調等[30]。既往研究顯示[31], CRA細胞通常表現出脂肪酸合成的顯著增加。此外,膽固醇代謝的異常,特別是關鍵酶羥甲基戊二酰輔酶A還原酶的表達增加,也與腺瘤的生長密切相關[32]。短鏈脂肪酸的產生和膽汁酸的轉化,通過調節炎癥反應和細胞增殖途徑如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號通路和Wnt/β-連環蛋白信號通路,促進或抑制腺瘤的發展[33]。既往還有學者認為,攝入大量飽和脂肪酸可能導致肥胖、代謝相關基因的影響和胰島素抵抗,這可能通過激活Toll 受體 4和脂多糖受體來誘導巨噬細胞NF-κB信號通路以及環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的表達來實現。這一過程促進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 F2,PGF2)的生成,PGF2是促炎介質,進而可能增加CRA的發生風險[34]。因此,針對脂質代謝途徑的干預,包括生活方式的調整和代謝途徑的靶向治療,提示通過調節脂質代謝來干預CRA可能是一個有益的治療策略。
2.5 CRA相關生物標志物
在CRA研究中,其生物分子標志物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Ki-67、p53、活化蛋白C等過表達已被證實與腺瘤細胞增殖和癌變過程密切相關[35]。Ahmed Nor 等[35]研究發現,EGFR和Ki-67在腺瘤中過表達,尤其是絨毛狀成分和高度異常增生的腺瘤,與腺瘤相比,CRC患者EGFR和Ki-67 LI過表達水平更高,且二者在CRC中的表達顯著相關;此外,CRC的組織學分級和浸潤與EGFR和Ki-67過表達密切相關,可能預示患者的轉移風險。Wang等[36]研究通過分析TCGA和GEO數據庫中的基因表達數據,發現了與CRA發展和進展相關的關鍵差異表達基因,發現碳酸酐酶2和11β-羥類固醇脫氫酶2是與CRA進展密切相關的關鍵基因。此外,該研究發現了與CRA相關的生物功能通路,如DNA修復、E2F、MYC、mTORC1、糖酵解和有絲分裂紡錘等,并證實了這些基因的表達水平與結直腸腺瘤的分級和預后的相關性,為進一步理解CRA的發病機制和尋找新的治療靶點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肖博等[37]采用實時定量PCR和免疫組化方法,探討兒茶酚胺氧位甲基轉移酶(catechol O-methyltransferase,COMT)mRNA及其蛋白在CRA及其瘤旁組織和CRC 及其癌旁組織中的表達情況,結果發現COMT在CRA及CRC組織中的表達較相應的瘤(癌)旁組織均升高,其可能在CRC的發生和發展中具有一定作用。綜上,這些生物分子標志物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CRA的病理機制,提高對患者的診斷準確性和治療個體化水平。然而,這些結果仍需在更大樣本量和臨床實踐中進行驗證。
2.6 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與CRA
Hp 是近年來臨床研究的熱點,盡管Hp感染引起CRA的機制尚不清楚,但多項研究表明Hp感染與CRA的發生有顯著關聯。一項Meta分析[38]系統地評估了Hp感染與結直腸息肉及其不同組織學類型之間的相關性,其結果表明,Hp感染與腺瘤、晚期腺瘤和增生性息肉具有獨立相關性,該結果為Hp感染作為結直腸息肉發生的潛在危險因素提供了理論依據。Hp可分泌多種毒力因子,這些毒力因子可作用于黏膜,維持Hp的持續感染,導致組織損傷和慢性炎癥反應。有文獻[39]表明,Hp感染引起的胃泌素分泌增加與CRA有關,胃泌素是一種主要由胃竇和十二指腸的G細胞分泌的胃腸激素,胃泌素不僅可以直接創造適宜的微環境促進腸腺瘤的發生,還可以通過胃泌素受體介導的增殖信號間接促進腸腺瘤的形成。Hp感染可引起腸道內分泌異常,進而誘導血漿胃泌素17和COX-2的表達,從而滋養腸黏膜,刺激腸黏膜增生,促進息肉生長。莊肇朦等[40] 的研究證實了CRA患者腺瘤組織中Hp的富集現象,并揭示了Hp感染與CRA Hp富集之間的相關性,指出Hp富集與腺瘤的臨床、病理特征及生物學行為之間存在關聯,同時提出腸道中的Hp可能是通過上調腺瘤組織內Toll樣受體5蛋白表達來介導促炎反應,從而啟動異常免疫應答,促進CRA的發生。綜上,Hp感染作為CRA發生的潛在危險因素,早期檢測和治療Hp感染可能有助于預防CRA及其進展為CRC。
3 小結與展望
CRA的發生涉及因素包括炎癥、遺傳和表觀遺傳改變、腸道菌群失調、脂質代謝異常等。這些因素通過不同的機制相互作用共同促進CRA的發生和發展。而一旦CRA演變為CRC,患者的預后明顯惡化,極大地影響了生活質量。在CRC的防治中,早期預防和篩查CRA顯得尤為重要。然而,我國全面普及結腸鏡篩查面臨一系列困難,包括腸道準備不充分、設備水平參差不齊以及醫師主觀判斷的差異,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CRA的檢出率。考慮到很多CRA患者在早期并沒有明顯癥狀,有必要對高危人群進行有針對性的篩查。因此,迫切需要深入研究CRA的分子機制、分子標志物及臨床應用,以便制定更為精準和有效的篩查策略。通過有目的性的結腸鏡檢查和治療,及時干預CRA的發生和發展,有望在早期階段就降低CRC的發病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質量。這一方面需要加強科研,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強公眾健康意識的提升,使更多的人能夠受益于早期篩查和干預。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 李兵、王士旭和劉藝行:主要負責文章的選題、文獻檢索與篩選、數據整理與分析,以及初稿的撰寫與修訂。王朝陽:參與文章的選題、文獻篩選與數據整理工作,對初稿進行了細致的審閱與修改,確保文章內容的準確性和深度。所有作者均對文章內容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