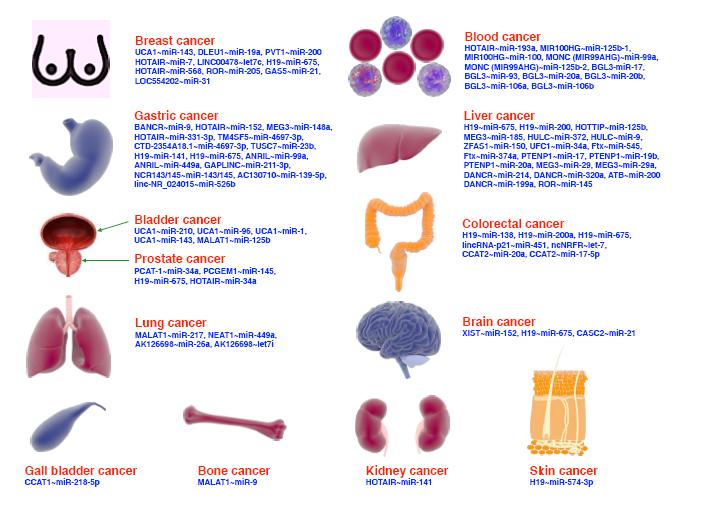肝細胞癌是全球高發的惡性腫瘤之一,盡管手術是患者獲得長期生存的關鍵手段,但多數患者在初次確診時無法進行手術,整體治療效果欠佳。筆者就目前肝細胞癌的治療策略,特別是以手術為核心的綜合治療方案進行了闡述,探討了在多學科診療模式下開展術前轉化、微創手術、術后輔助等綜合治療的現狀和進展。通過合理的綜合治療策略,有望改善肝細胞癌患者的治療效果和生活質量。
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作為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是威脅我國人民健康的嚴重疾病,其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1-2]。目前,HCC的治療策略仍是以外科手術為核心的綜合治療,且手術切除仍是患者獲得長期生存的最佳手段,但大部分患者初次就診時已處于巴塞羅那臨床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B期或C期而被認為不適宜接受手術治療[3]。 雖然在中國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中分期早于Ⅲa期的都被認為仍有潛在手術機會,但事實上大部分初診患者在經過術前評估后未能接受手術治療[4]。因此,非手術治療在HCC綜合治療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其治療策略也從傳統的單一治療模式轉向多學科、多手段的綜合治療,其中以靶向和免疫治療為代表的系統治療方式取得了顯著進展,提高了HCC的手術率及改善了生存預后[5]。筆者回顧了目前HCC治療的現狀和進展,嘗試總結以手術為核心的HCC治療策略。
1 肝臟切除術
1.1 多學科診療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
肝切除術在HCC患者整體5年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和無瘤生存率分別為46%~69.5%和23%~56.3%[6],證明了其治療的有效性。尤其對于肝功能儲備及機體狀態良好的早中期(CNLC Ⅰa、Ⅰb、Ⅱa期)HCC來說,肝切除術有著相較于肝移植更低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以及相較于其他治療方式更好的遠期預后,無疑是治療的首選方案[7]。雖然先進的外科技術仍然是影響HCC肝切除術預后的重要因素,但精細的圍手術期評估和個性化的治療方案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也使MDT的重要性愈加突出[7],體現在:① 手術適應證和禁忌證的術前評估。包括腫瘤的數目、大小和部位是否適合立即手術,需要外科醫師結合影像學專家閱片意見綜合評估;術前營養狀態、全身臟器狀態、基礎疾病等是否能夠耐受手術,在MDT模式下可以避免單一學科在治療時可能出現的細節遺漏。② 手術方案的制定。包括是否進行根治性切除、開腹手術還是微創手術、手術入路選擇、切除方式選擇(一期或二期切除、是否解剖性切除、在體或離體切除)等方面,術者可以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結合不同學科的專業意見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以提高治療的精準性和有效性。③ 術后評估和管理。《中國肝癌多學科綜合治療專家共識》[8]表明,MDT模式可以顯著提高肝腫瘤患者的術后生存率和生活質量,通過多學科的協作,患者可以獲得更加綜合和全面的治療,從而提高術后恢復速度和效果。
1.2 微創手術
是否進行微創切除是術前MDT評估的關鍵環節之一。自從2008年第一屆國際腹腔鏡肝切除共識[9]提出以來,單個、直徑小于5 cm和病變位于肝臟邊緣的腫瘤一直都是我國HCC切除術的良好適應證,其腹腔鏡解剖性肝切除術后 1、3和5 年累積無瘤生存率分別為84.8%、63.2%和52.2%[10]。并且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腹腔鏡肝切除術的適應證正在逐步拓展,包括:① 巨大肝癌。腫瘤大小是影響腹腔鏡手術難度的重要因素,包括HCC質地較軟不能過度擠壓限制了術中操作空間、腫瘤擠壓了周圍管道導致解剖變形及術中操作風險增加、巨大腫瘤導致肝臟切除范圍過大術后恢復風險增加等原因,使得腫瘤大小成為影響術中出血量、中轉開腹率及術后住院時間的重要因素。② 特殊部位肝癌。如緊貼心臟或胃等臟器、位于第一肝門和肝靜脈之間等,導致視野局限、操作空間狹窄、器械無法抵達,增加手術難度。③ 特殊質地肝臟。如肝硬化、重度脂肪肝等病變不僅增加術中出血風險,還對術中麻醉狀態穩定、術后手術應激恢復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然而,2013年我國《腹腔鏡肝切除專家共識與手術操作指南(2013版)》[11]就已將直徑大于10 cm的HCC列為腹腔鏡手術適應證,表明腫瘤體積已不再是腹腔鏡肝切除的絕對禁忌證。同時大量研究[12-14]已表明,在熟練的技術及謹慎的術前評估支持下,特殊部位及肝臟質地對經驗豐富腹腔鏡術者的手術預后并無顯著影響。機器人輔助手術系統是肝切除術的又一微創途徑,通過高度靈活的機械臂能夠完成復雜的手術操作,可顯著提升縫合等手術操作的精準度,它的另一特點是可通過信號傳輸實現遠程手術,但手術費用高昂以及部分特殊病灶區域不利于機械臂操作是目前限制其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15]。
1.3 術后輔助治療
即使經過手術切除, HCC仍有術后復發可能。2023版《肝癌術后輔助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3版)》[16]將HCC術后復發分為早期復發(術后2年內的復發)和晚期復發(2年及之后的復發),其中腫瘤多發、腫瘤長徑 >5 cm、Edmondson 病理分級為Ⅲ~Ⅳ級、微血管或大血管侵犯、淋巴結轉移、術后甲胎蛋白(alpha fetal protein,AFP) 和(或)異常凝血酶原(des-γ-carboxy-prothrombin,DCP)持續異常等與HCC的早期復發有關;慢性病毒性肝炎活動期、HBsAg 陽性、肝硬化程度等與HCC的晚期復發相關。該《共識》[16]認為,對于術后復發高風險人群,在肝功能恢復良好的情況下應該盡快啟動術后輔助治療,除針對肝炎病毒背景的抗病毒治療以及定期隨訪外,術后輔助治療還應包括局部和系統治療等綜合治療措施。肝動脈化療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HCC常用的局部治療方式,該《共識》[16]認為,術后行輔助性TACE可改善合并高危因素患者的無復發生存時間(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并延長OS。有數據[17]表明,TACE對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陽性的術后患者有益;但同時也有研究[18-19]發現,TACE可能對大結節(直徑 >5 cm)的MVI陽性患者更為有效,對于多發結節的MVI陽性患者效果存疑,而對于不存在復發風險的患者TACE甚至可能因為損傷肝臟微環境、形成局部缺氧等原因增加腫瘤復發風險。作為局部治療的另一方式,以FOLFOX方案為基礎的肝動脈灌注化療(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近年在我國中晚期HCC治療中獲得較多進展及認可,也被《共識》[16]認為可以改善合并MVI陽性患者的術后RFS而被推薦。但同時也有多中心研究[20]發現,HAIC僅能改善RFS而對OS并無獲益。因此HAIC在術后輔助治療方面的價值仍有待進一步證實;此外,不同化療方案HAIC在術后預防中的作用價值差異也仍需探索。
在系統性治療方面,靶向、免疫及聯合治療在術后輔助治療中進行了大量探索。盡管有STORM研究[21-22]表明,索拉非尼對根治性HCC切除術后的RFS和OS并無益處且此結果同樣適用于MVI陽性亞組;但也有研究[23]認為,索拉非尼和侖伐替尼均可使HCC患者術后RFS及OS獲益,只是與早期HCC患者相比,合并高危復發因素的HCC患者獲益于術后系統靶向治療的概率可能更高。 雖然已有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單藥因不劣于索拉非尼的治療效果而被納入《中國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24年版)》[24],但在術后輔助治療方面更多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免疫與靶向藥物的聯合治療。《Lancet》發表的前瞻性多中心Ⅲ期臨床研究Imbrave050數據[25]表明,對有高危復發風險因素的手術切除患者應用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的術后輔助治療,其中期分析結果觀察到可延長患者的RFS,但最終結果發現這個獲益在更長時間觀察中卻沒有持續。國內亦有研究[26]發現,聯合TACE、靶向藥物(索拉非尼/侖伐替尼)和其他藥物(華蟾素/槐耳顆粒)對于MVI陽性HCC患者術后RFS和OS優于單用TACE。當然,聯合治療的并發癥可能更重,更多的術后聯合用藥研究也仍在開展當中,其在HCC術后輔助治療中的未來需要更多的探索,但也仍然值得期待。
1.4 術前轉化治療
雖然手術治療效果確切,但根據我國《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24年版)》[24],HCC手術切除的基本原則應包括切除的安全性和徹底性兩方面。如果兩方面要求都符合,評估腫瘤可切除,但為了殺滅潛在轉移病灶、提高R0切除率、降低復發風險、提高生存預期,而在術前接受的局部或系統治療稱為新輔助治療(目前關于HCC是否建議行新輔助治療尚無明確定論);不完全符合要求,為了后續能夠完成序貫手術切除而進行的術前抗腫瘤治療即是轉化治療[27]。對于兩方面條件均不符合的HCC患者,轉化治療的目標應更偏保守,具體治療策略選擇時應由有效性(轉化效率)向安全性更多傾斜,這樣即使轉化失敗也不至于錯失規范化抗腫瘤治療時機。對于單一條件不符合者,則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
不滿足安全性條件的患者,往往是剩余肝臟體積(future liver remnant,FLR)不足、肝功能或全身情況無法耐受手術等導致技術層面即外科學意義上的不可切除。 針對這部分大多為CNLCⅠa、Ⅰb或Ⅱa期的患者,應從內科角度積極糾正改善其全身狀態、提高手術耐受性,同時還應從外科角度嘗試解決FLR不足的問題。《原發性肝癌轉化及圍手術期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版)》[27]建議通過門靜脈栓塞術(portal vein embolization,PVE)或拯救性聯合肝臟分隔和門靜脈結扎的二步肝切除術(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進行FLR 轉化。有數據[28]表明,PVE相較于ALPPS有著更低的并發癥率(5%比38%)以及更低的轉化率(91%比98%),但兩者更關鍵的區別在于轉化等待時間(4~6周比1~2周),PVE較長時間的等待可能導致腫瘤進展,因而《原發性肝癌轉化及圍手術期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版)》[27]建議對預期有功能 FLR 增生時間較長(如較嚴重的肝硬化、年齡較大的患者)、腫瘤進展可能較快的患者,應謹慎使用 PVE。另一方面,雖然ALPPS在技術改良(腹腔鏡微創入路、消融分隔等)支持下降低了術后短期并發癥率,即使與TACE聯合PVE相比也明顯有更高的轉化切除率(97.4%比65.8%)[29],但其是否有長期生存獲益(5年生存率46.8%和64.1%)仍無定論[30]。在此背景下,肝靜脈剝奪術(liver venous deprivation, LVD)作為誘導肝組織增生的新術式,通過聯合應用PVE和肝靜脈栓塞,擁有比PVE更高的增生效率以及比ALPPS更低的并發癥率而獲得了廣泛關注[31]。此外,與PVE相比有著更高轉化率和更低并發癥率的釔-90放射栓塞治療似乎為轉化治療帶來了新的可能[32],其適用于門靜脈癌栓的特性以及增大余肝和縮瘤的效果都值得更多期待,有待相關研究給予更多的數據支持。
不滿足徹底性條件的往往是腫瘤分期較晚的CNLC Ⅱb和Ⅲa期HCC患者,此時直接手術切除可能導致早期復發,手術切除的預后甚至劣于非手術治療,即為腫瘤學意義上的不可切除。對于此類患者的轉化途徑經歷了化療、靶向、免疫、局部以及聯合治療的發展。目前,《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24年版)》[24]中大部分非手術治療方式都可被應用于轉化治療當中,但從數據上看單一治療方式轉化效率均較為有限。包括索拉非尼、侖伐替尼等在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OS方面均顯著有效的靶向藥物,單藥達到轉化效果的報道均僅見于個案報道[33];單一ICI的ORR僅為20%左右,不作為轉化治療的推薦方式[27];TACE局部治療可達到8%~18%的轉化效率[34],以FOLFOX方案為基礎的HAIC雖然缺乏單一治療方式的轉化數據,但已有研究表明其與靶向、免疫治療等方案聯合可顯著提高轉化率和改善遠期預后[35]。總之,更多的數據表明,靶向、免疫及局部治療(TACE或HAIC)的三聯方案雖然不良反應發生率更高,但同時帶來了更為顯著的轉化機會和生存獲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綜合治療的整體方案類似,但治療目的的不同也會導致方案選擇的側重點不同:轉化治療應聚焦腫瘤快速縮小緩解、中晚期HCC治療應強調OS,而術后輔助治療則應同時關注不良反應和患者耐受性,因此MDT模式的重要性再次凸顯。MDT不僅有助于個性化治療方案的選擇,還可對轉化治療的手術時機、術后輔助治療停藥等環節進行調整,以使患者最大程度獲益。
2 肝移植
肝移植作為治療終末期肝病及HCC 的關鍵手段,其效果在符合米蘭標準的BCLC A期患者中尤為顯著,顯示出超過70%的5年生存率[36]。近年來,背馱式、劈離式等肝移植技術的廣泛開展,對改善無肝期循環狀態、緩解供肝不足等問題帶來了福音。此外,隨著醫學研究的深入和臨床實踐的積累,HCC肝移植手術標準也逐漸放寬,大量患者在通過肝移植獲得腫瘤根治的同時也使肝臟基礎病變得到了改善。然而,隨著標準的擴寬,術后生存率以及復發率等數據也在變差,導致整體5年生存率僅為46.8 %,5年累積復發率為 36.7%[37]。目前肝移植標準眾多,上海復旦標準、Kyoto標準、杭州標準等,如何在保證一定生存率的同時讓盡量多的HCC患者獲益于肝移植技術是移植醫生面臨的難題。有學者認為只要達到5年生存率50%的標準就可以盡量擴寬手術指征,但也有觀點認為要達到60%以上才足以保障良性肝病患者的肝移植公平權益[38-39]。無論如何,在具體移植單位落實標準制定時以HCC患者術后生存率為導向、結合自身情況的具體分析是提高肝移植HCC治療效果的重要環節。
另一方面,即使經過嚴格的受體篩選,仍有10%以上的HCC肝移植患者出現了腫瘤復發,如何處理好肝移植術后免疫抑制與預防腫瘤復發之間的矛盾是近年來肝移植臨床研究的另一熱點問題[40]。除既往學者[41]強調盡量減少免疫抑制劑應用的策略外,mTor抑制劑(西羅莫司和依維莫司)藥物的應用可在免疫抑制同時起到抗血管生成等抑制腫瘤的效果,有效降低了肝移植術后的腫瘤復發。此外,靶向免疫藥物的應用進展同樣令人振奮,已有多個中心的數據表明,將包括索拉非尼在內的靶向藥物應用于移植術后可安全且有效地降低HCC復發風險,雖然仍有待更大量的臨床數據支撐,但索拉非尼等靶向藥物聯合mTor免疫抑制藥物似乎是當下最有效的移植術后聯合用藥方案之一[41]。包括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及其配體PD-L1抑制劑在內的ICI是有效的抗腫瘤綜合治療方式之一,但其在肝移植術后的應用合理性和有效性一直備受質疑。最近發布的《中國肝癌肝移植受者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應用專家共識(2024版)》[42]認為,對無遠處轉移、肝功能良好的中晚期肝癌可以在肝移植術前使用ICI,單一ICI藥物在移植術前停藥 ≥30 d情況下的應用是基本安全的,但仍應在充分醫患溝通條件下進行。在術后用藥方面,考慮到引發排斥反應的風險而不建議使用ICI作為預防腫瘤復發的治療;而在術后復發治療時,建議在用藥前對肝臟供體行PD-L1配體檢測以預測ICI用藥的安全性,PD-L1表達陽性者應禁用PD-1或PD-L1單抗[42]。總之,對于HCC患者來說,肝移植仍是其關鍵治療手段之一,而ICI等綜合治療模式的進展將進一步提高HCC肝移植受者的治療獲益。
綜上所述,外科手術仍是當前HCC患者獲得長期生存尤其是無瘤生存的重要手段,但單一治療方式的天花板效應使得非手術綜合治療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靶免時代的到來以及各類技術的不斷發展為HCC的治療帶來了新的期待。相信隨著MDT模式的不斷發展以及更多臨床、基礎的相關研究,HCC患者的長期生存必將得到進一步改善。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游逾、劉作金、龔建平共同完成了文獻檢索和匯總;游逾完成了文章撰寫;龔建平完成了文稿審閱。
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作為全球范圍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是威脅我國人民健康的嚴重疾病,其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1-2]。目前,HCC的治療策略仍是以外科手術為核心的綜合治療,且手術切除仍是患者獲得長期生存的最佳手段,但大部分患者初次就診時已處于巴塞羅那臨床分期(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B期或C期而被認為不適宜接受手術治療[3]。 雖然在中國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中分期早于Ⅲa期的都被認為仍有潛在手術機會,但事實上大部分初診患者在經過術前評估后未能接受手術治療[4]。因此,非手術治療在HCC綜合治療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其治療策略也從傳統的單一治療模式轉向多學科、多手段的綜合治療,其中以靶向和免疫治療為代表的系統治療方式取得了顯著進展,提高了HCC的手術率及改善了生存預后[5]。筆者回顧了目前HCC治療的現狀和進展,嘗試總結以手術為核心的HCC治療策略。
1 肝臟切除術
1.1 多學科診療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
肝切除術在HCC患者整體5年總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和無瘤生存率分別為46%~69.5%和23%~56.3%[6],證明了其治療的有效性。尤其對于肝功能儲備及機體狀態良好的早中期(CNLC Ⅰa、Ⅰb、Ⅱa期)HCC來說,肝切除術有著相較于肝移植更低的術后并發癥發生率以及相較于其他治療方式更好的遠期預后,無疑是治療的首選方案[7]。雖然先進的外科技術仍然是影響HCC肝切除術預后的重要因素,但精細的圍手術期評估和個性化的治療方案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也使MDT的重要性愈加突出[7],體現在:① 手術適應證和禁忌證的術前評估。包括腫瘤的數目、大小和部位是否適合立即手術,需要外科醫師結合影像學專家閱片意見綜合評估;術前營養狀態、全身臟器狀態、基礎疾病等是否能夠耐受手術,在MDT模式下可以避免單一學科在治療時可能出現的細節遺漏。② 手術方案的制定。包括是否進行根治性切除、開腹手術還是微創手術、手術入路選擇、切除方式選擇(一期或二期切除、是否解剖性切除、在體或離體切除)等方面,術者可以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結合不同學科的專業意見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以提高治療的精準性和有效性。③ 術后評估和管理。《中國肝癌多學科綜合治療專家共識》[8]表明,MDT模式可以顯著提高肝腫瘤患者的術后生存率和生活質量,通過多學科的協作,患者可以獲得更加綜合和全面的治療,從而提高術后恢復速度和效果。
1.2 微創手術
是否進行微創切除是術前MDT評估的關鍵環節之一。自從2008年第一屆國際腹腔鏡肝切除共識[9]提出以來,單個、直徑小于5 cm和病變位于肝臟邊緣的腫瘤一直都是我國HCC切除術的良好適應證,其腹腔鏡解剖性肝切除術后 1、3和5 年累積無瘤生存率分別為84.8%、63.2%和52.2%[10]。并且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進步,腹腔鏡肝切除術的適應證正在逐步拓展,包括:① 巨大肝癌。腫瘤大小是影響腹腔鏡手術難度的重要因素,包括HCC質地較軟不能過度擠壓限制了術中操作空間、腫瘤擠壓了周圍管道導致解剖變形及術中操作風險增加、巨大腫瘤導致肝臟切除范圍過大術后恢復風險增加等原因,使得腫瘤大小成為影響術中出血量、中轉開腹率及術后住院時間的重要因素。② 特殊部位肝癌。如緊貼心臟或胃等臟器、位于第一肝門和肝靜脈之間等,導致視野局限、操作空間狹窄、器械無法抵達,增加手術難度。③ 特殊質地肝臟。如肝硬化、重度脂肪肝等病變不僅增加術中出血風險,還對術中麻醉狀態穩定、術后手術應激恢復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然而,2013年我國《腹腔鏡肝切除專家共識與手術操作指南(2013版)》[11]就已將直徑大于10 cm的HCC列為腹腔鏡手術適應證,表明腫瘤體積已不再是腹腔鏡肝切除的絕對禁忌證。同時大量研究[12-14]已表明,在熟練的技術及謹慎的術前評估支持下,特殊部位及肝臟質地對經驗豐富腹腔鏡術者的手術預后并無顯著影響。機器人輔助手術系統是肝切除術的又一微創途徑,通過高度靈活的機械臂能夠完成復雜的手術操作,可顯著提升縫合等手術操作的精準度,它的另一特點是可通過信號傳輸實現遠程手術,但手術費用高昂以及部分特殊病灶區域不利于機械臂操作是目前限制其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因素[15]。
1.3 術后輔助治療
即使經過手術切除, HCC仍有術后復發可能。2023版《肝癌術后輔助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3版)》[16]將HCC術后復發分為早期復發(術后2年內的復發)和晚期復發(2年及之后的復發),其中腫瘤多發、腫瘤長徑 >5 cm、Edmondson 病理分級為Ⅲ~Ⅳ級、微血管或大血管侵犯、淋巴結轉移、術后甲胎蛋白(alpha fetal protein,AFP) 和(或)異常凝血酶原(des-γ-carboxy-prothrombin,DCP)持續異常等與HCC的早期復發有關;慢性病毒性肝炎活動期、HBsAg 陽性、肝硬化程度等與HCC的晚期復發相關。該《共識》[16]認為,對于術后復發高風險人群,在肝功能恢復良好的情況下應該盡快啟動術后輔助治療,除針對肝炎病毒背景的抗病毒治療以及定期隨訪外,術后輔助治療還應包括局部和系統治療等綜合治療措施。肝動脈化療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是HCC常用的局部治療方式,該《共識》[16]認為,術后行輔助性TACE可改善合并高危因素患者的無復發生存時間(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并延長OS。有數據[17]表明,TACE對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陽性的術后患者有益;但同時也有研究[18-19]發現,TACE可能對大結節(直徑 >5 cm)的MVI陽性患者更為有效,對于多發結節的MVI陽性患者效果存疑,而對于不存在復發風險的患者TACE甚至可能因為損傷肝臟微環境、形成局部缺氧等原因增加腫瘤復發風險。作為局部治療的另一方式,以FOLFOX方案為基礎的肝動脈灌注化療(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近年在我國中晚期HCC治療中獲得較多進展及認可,也被《共識》[16]認為可以改善合并MVI陽性患者的術后RFS而被推薦。但同時也有多中心研究[20]發現,HAIC僅能改善RFS而對OS并無獲益。因此HAIC在術后輔助治療方面的價值仍有待進一步證實;此外,不同化療方案HAIC在術后預防中的作用價值差異也仍需探索。
在系統性治療方面,靶向、免疫及聯合治療在術后輔助治療中進行了大量探索。盡管有STORM研究[21-22]表明,索拉非尼對根治性HCC切除術后的RFS和OS并無益處且此結果同樣適用于MVI陽性亞組;但也有研究[23]認為,索拉非尼和侖伐替尼均可使HCC患者術后RFS及OS獲益,只是與早期HCC患者相比,合并高危復發因素的HCC患者獲益于術后系統靶向治療的概率可能更高。 雖然已有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單藥因不劣于索拉非尼的治療效果而被納入《中國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24年版)》[24],但在術后輔助治療方面更多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免疫與靶向藥物的聯合治療。《Lancet》發表的前瞻性多中心Ⅲ期臨床研究Imbrave050數據[25]表明,對有高危復發風險因素的手術切除患者應用阿替利珠單抗聯合貝伐珠單抗的術后輔助治療,其中期分析結果觀察到可延長患者的RFS,但最終結果發現這個獲益在更長時間觀察中卻沒有持續。國內亦有研究[26]發現,聯合TACE、靶向藥物(索拉非尼/侖伐替尼)和其他藥物(華蟾素/槐耳顆粒)對于MVI陽性HCC患者術后RFS和OS優于單用TACE。當然,聯合治療的并發癥可能更重,更多的術后聯合用藥研究也仍在開展當中,其在HCC術后輔助治療中的未來需要更多的探索,但也仍然值得期待。
1.4 術前轉化治療
雖然手術治療效果確切,但根據我國《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24年版)》[24],HCC手術切除的基本原則應包括切除的安全性和徹底性兩方面。如果兩方面要求都符合,評估腫瘤可切除,但為了殺滅潛在轉移病灶、提高R0切除率、降低復發風險、提高生存預期,而在術前接受的局部或系統治療稱為新輔助治療(目前關于HCC是否建議行新輔助治療尚無明確定論);不完全符合要求,為了后續能夠完成序貫手術切除而進行的術前抗腫瘤治療即是轉化治療[27]。對于兩方面條件均不符合的HCC患者,轉化治療的目標應更偏保守,具體治療策略選擇時應由有效性(轉化效率)向安全性更多傾斜,這樣即使轉化失敗也不至于錯失規范化抗腫瘤治療時機。對于單一條件不符合者,則應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
不滿足安全性條件的患者,往往是剩余肝臟體積(future liver remnant,FLR)不足、肝功能或全身情況無法耐受手術等導致技術層面即外科學意義上的不可切除。 針對這部分大多為CNLCⅠa、Ⅰb或Ⅱa期的患者,應從內科角度積極糾正改善其全身狀態、提高手術耐受性,同時還應從外科角度嘗試解決FLR不足的問題。《原發性肝癌轉化及圍手術期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版)》[27]建議通過門靜脈栓塞術(portal vein embolization,PVE)或拯救性聯合肝臟分隔和門靜脈結扎的二步肝切除術(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進行FLR 轉化。有數據[28]表明,PVE相較于ALPPS有著更低的并發癥率(5%比38%)以及更低的轉化率(91%比98%),但兩者更關鍵的區別在于轉化等待時間(4~6周比1~2周),PVE較長時間的等待可能導致腫瘤進展,因而《原發性肝癌轉化及圍手術期治療中國專家共識(2024版)》[27]建議對預期有功能 FLR 增生時間較長(如較嚴重的肝硬化、年齡較大的患者)、腫瘤進展可能較快的患者,應謹慎使用 PVE。另一方面,雖然ALPPS在技術改良(腹腔鏡微創入路、消融分隔等)支持下降低了術后短期并發癥率,即使與TACE聯合PVE相比也明顯有更高的轉化切除率(97.4%比65.8%)[29],但其是否有長期生存獲益(5年生存率46.8%和64.1%)仍無定論[30]。在此背景下,肝靜脈剝奪術(liver venous deprivation, LVD)作為誘導肝組織增生的新術式,通過聯合應用PVE和肝靜脈栓塞,擁有比PVE更高的增生效率以及比ALPPS更低的并發癥率而獲得了廣泛關注[31]。此外,與PVE相比有著更高轉化率和更低并發癥率的釔-90放射栓塞治療似乎為轉化治療帶來了新的可能[32],其適用于門靜脈癌栓的特性以及增大余肝和縮瘤的效果都值得更多期待,有待相關研究給予更多的數據支持。
不滿足徹底性條件的往往是腫瘤分期較晚的CNLC Ⅱb和Ⅲa期HCC患者,此時直接手術切除可能導致早期復發,手術切除的預后甚至劣于非手術治療,即為腫瘤學意義上的不可切除。對于此類患者的轉化途徑經歷了化療、靶向、免疫、局部以及聯合治療的發展。目前,《原發性肝癌診療指南(2024年版)》[24]中大部分非手術治療方式都可被應用于轉化治療當中,但從數據上看單一治療方式轉化效率均較為有限。包括索拉非尼、侖伐替尼等在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OS方面均顯著有效的靶向藥物,單藥達到轉化效果的報道均僅見于個案報道[33];單一ICI的ORR僅為20%左右,不作為轉化治療的推薦方式[27];TACE局部治療可達到8%~18%的轉化效率[34],以FOLFOX方案為基礎的HAIC雖然缺乏單一治療方式的轉化數據,但已有研究表明其與靶向、免疫治療等方案聯合可顯著提高轉化率和改善遠期預后[35]。總之,更多的數據表明,靶向、免疫及局部治療(TACE或HAIC)的三聯方案雖然不良反應發生率更高,但同時帶來了更為顯著的轉化機會和生存獲益。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綜合治療的整體方案類似,但治療目的的不同也會導致方案選擇的側重點不同:轉化治療應聚焦腫瘤快速縮小緩解、中晚期HCC治療應強調OS,而術后輔助治療則應同時關注不良反應和患者耐受性,因此MDT模式的重要性再次凸顯。MDT不僅有助于個性化治療方案的選擇,還可對轉化治療的手術時機、術后輔助治療停藥等環節進行調整,以使患者最大程度獲益。
2 肝移植
肝移植作為治療終末期肝病及HCC 的關鍵手段,其效果在符合米蘭標準的BCLC A期患者中尤為顯著,顯示出超過70%的5年生存率[36]。近年來,背馱式、劈離式等肝移植技術的廣泛開展,對改善無肝期循環狀態、緩解供肝不足等問題帶來了福音。此外,隨著醫學研究的深入和臨床實踐的積累,HCC肝移植手術標準也逐漸放寬,大量患者在通過肝移植獲得腫瘤根治的同時也使肝臟基礎病變得到了改善。然而,隨著標準的擴寬,術后生存率以及復發率等數據也在變差,導致整體5年生存率僅為46.8 %,5年累積復發率為 36.7%[37]。目前肝移植標準眾多,上海復旦標準、Kyoto標準、杭州標準等,如何在保證一定生存率的同時讓盡量多的HCC患者獲益于肝移植技術是移植醫生面臨的難題。有學者認為只要達到5年生存率50%的標準就可以盡量擴寬手術指征,但也有觀點認為要達到60%以上才足以保障良性肝病患者的肝移植公平權益[38-39]。無論如何,在具體移植單位落實標準制定時以HCC患者術后生存率為導向、結合自身情況的具體分析是提高肝移植HCC治療效果的重要環節。
另一方面,即使經過嚴格的受體篩選,仍有10%以上的HCC肝移植患者出現了腫瘤復發,如何處理好肝移植術后免疫抑制與預防腫瘤復發之間的矛盾是近年來肝移植臨床研究的另一熱點問題[40]。除既往學者[41]強調盡量減少免疫抑制劑應用的策略外,mTor抑制劑(西羅莫司和依維莫司)藥物的應用可在免疫抑制同時起到抗血管生成等抑制腫瘤的效果,有效降低了肝移植術后的腫瘤復發。此外,靶向免疫藥物的應用進展同樣令人振奮,已有多個中心的數據表明,將包括索拉非尼在內的靶向藥物應用于移植術后可安全且有效地降低HCC復發風險,雖然仍有待更大量的臨床數據支撐,但索拉非尼等靶向藥物聯合mTor免疫抑制藥物似乎是當下最有效的移植術后聯合用藥方案之一[41]。包括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death-1,PD-1)及其配體PD-L1抑制劑在內的ICI是有效的抗腫瘤綜合治療方式之一,但其在肝移植術后的應用合理性和有效性一直備受質疑。最近發布的《中國肝癌肝移植受者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應用專家共識(2024版)》[42]認為,對無遠處轉移、肝功能良好的中晚期肝癌可以在肝移植術前使用ICI,單一ICI藥物在移植術前停藥 ≥30 d情況下的應用是基本安全的,但仍應在充分醫患溝通條件下進行。在術后用藥方面,考慮到引發排斥反應的風險而不建議使用ICI作為預防腫瘤復發的治療;而在術后復發治療時,建議在用藥前對肝臟供體行PD-L1配體檢測以預測ICI用藥的安全性,PD-L1表達陽性者應禁用PD-1或PD-L1單抗[42]。總之,對于HCC患者來說,肝移植仍是其關鍵治療手段之一,而ICI等綜合治療模式的進展將進一步提高HCC肝移植受者的治療獲益。
綜上所述,外科手術仍是當前HCC患者獲得長期生存尤其是無瘤生存的重要手段,但單一治療方式的天花板效應使得非手術綜合治療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靶免時代的到來以及各類技術的不斷發展為HCC的治療帶來了新的期待。相信隨著MDT模式的不斷發展以及更多臨床、基礎的相關研究,HCC患者的長期生存必將得到進一步改善。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游逾、劉作金、龔建平共同完成了文獻檢索和匯總;游逾完成了文章撰寫;龔建平完成了文稿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