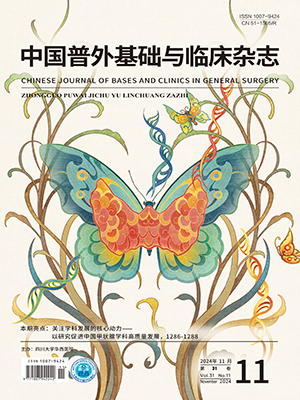2022年中國原發性肝癌發病人數36.77萬,死亡人數31.65萬。射頻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是肝癌的根治性治療方式之一,具有療效確切、微創、價廉等特點,在早期肝癌患者中療效與手術切除相似。精準外科理念的提出和實踐為提高RFA療效提供了新思路。筆者團隊基于萬余例RFA治療經驗,開展原發性肝癌精準消融治療研究,現筆者將結合現有文獻及團隊經驗,論述精準外科理念在RFA治療中的應用與前景。
根據中國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數據,2022年全國原發性肝癌(以下簡稱肝癌)發病人數36.77萬(位居各種癌癥的第4位),因肝癌死亡人數31.65 萬(位居各種癌癥的第2位)。國內外最新的肝癌治療指南把消融治療與肝切除和肝移植同列為根治性治療小肝癌的治療方式,其中消融治療又以射頻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最為常見[1-2]。消融治療有療效確切、微創價廉、對肝功能影響小和并發癥少的特點,具有更廣泛的適應證,其在早期肝癌患者中可獲得與手術切除類似的療效。但是,也有研究[3]指出肝癌患者行RFA后的局部復發率顯著高于手術切除。近年來,以“確定性、預見性、可控性、規范化、個體化、系統化”為核心要素的精準外科理念的提出和實踐[4],為我們提高RFA 治療肝癌的療效提供了新思路。筆者團隊在原有1萬余例次的RFA治療經驗基礎上,積極開展肝癌的精準消融治療相關研究,現筆者將結合現有文獻及團隊經驗,論述精準外科理念在肝癌RFA治療中的應用與前景。
1 在精準治療理念指導下規范化選擇RFA的適應證
近年來,公眾健康意識不斷提升以及體檢覆蓋范圍日益廣泛,同時醫療技術的飛速發展,尤其是肝癌篩查與監測技術的顯著進步,如甲胎蛋白異質體3、異常凝血酶原、高爾基體蛋白73、骨橋蛋白等新型標志物和包括循環微小核糖核酸、循環腫瘤DNA以及循環腫瘤細胞在內的液體活檢技術[5],以及以釓塞酸二鈉增強的MR和超聲成像為代表的影像學技術的進步[6-7],不僅提高了檢測的敏感度和特異度,還使得微小病灶的識別成為可能,肝癌患者在早期便能被準確診斷。在此大背景下,肝癌患者的早期精確診斷不僅提高了患者的預后、改善患者術后生活質量,還為醫生爭取到了選擇更加精準化治療方案的時間窗口,從而以更加微創的方式來治療肝癌。
RFA作為肝癌的微創治療手段,是在影像技術的引導下,將治療電極精準穿刺至病灶內部,通過電極釋放的高頻電磁波引發局部離子振蕩摩擦產生高溫,促使穿刺點及其周邊癌組織發生凝固性壞死。然而,受限于當前技術水平和患者的耐受性,同時為了降低穿刺相關并發癥的風險,穿刺電極的直徑通常不超過2 mm,且單次消融所能覆蓋的病灶直徑一般不超過3 cm。研究[8]表明,病灶大小對RFA實現完全消融的效果有顯著影響,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一是病灶周圍血管的血流會帶走熱量(熱沉降效應),從而影響消融的溫度,繼而影響消融效果;二是傳統RFA通常在二維超聲或(和)CT引導下操作,消融電極可能無法精確置于病灶的三維中心,導致其他平面的消融不足;三是每次消融過程中產生的水蒸汽會妨礙即時觀察消融后病灶內是否殘留癌組織;四是病灶形態的不規則性。因此,若病灶的直徑大于3 cm,RFA往往難以消融完全。
故對于肝癌行RFA的適應證,最新的指南[1]指出:單個腫瘤、直徑 ≤5 cm,或2~ 3個腫瘤、 最大直徑 ≤3 cm可行RFA。對于直徑3~7 cm由于各種原因不可切除的單發腫瘤或多發腫瘤,可以先行肝動脈化療栓塞術后再行RFA。另外,當病灶位于膽囊或第一肝門附近且間距小于5 mm時,通常會縮短消融時間以避免高溫對膽管及膽囊的破壞,但是這也會影響對病灶的完全消融。RFA的療效不僅受病灶大小的影響,還對患者自身的健康狀況、肝功能狀態及凝血功能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患者在過去6個月內若發生過食管胃底靜脈曲張并發破裂出血,則必須在接受止血措施之后,方可考慮進行 RFA 治療,否則可能引發再次出血的風險[9]。
2 在精準治療理念指導下個體化進行RFA術前準備及評估
近年來,傳統經驗外科的治療理念正向現代精準外科轉變。其中,精準肝膽外科要求實現雙重目標:一方面,需精準且徹底地移除目標病灶,并確保手術切緣的安全性,以預防復發;另一方面,必須確保剩余肝臟的解剖完整性,并最大化其功能性體積,從而在保證手術效果的同時,減少手術對機體的損傷。整個手術過程中,需嚴格控制創傷范圍,有效管理出血情況,力求將并發癥的發生降至最低,最終使手術患者能夠獲得最為理想的治療效果與術后恢復[10]。
相較于在寬闊視野下進行機械性手術切除肝癌,RFA需要在影像技術引導下將治療電極經皮穿刺入肝癌病灶內。因此要在RFA過程中貫徹精準治療的理念,術前對肝癌組織的精準定位非常重要,并且需對患者進行全面嚴格的術前評估。
首先,常規RFA全程是在超聲或(和)CT引導下進行的。以超聲引導為例,術前進行肝臟超聲造影檢查對癌灶進行定位是有必要的。此外,為了進一步提升診斷的精確性,尤其是針對直徑1 cm以下的微小病灶,術前采用釓塞酸二鈉增強的MRI檢查也同樣重要。在行釓塞酸二鈉增強 MRI后,在該圖像的提示下再做超聲造影檢查以確保對病灶的精準定位和量化評估,從而保證手術的順利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釓塞酸二鈉增強的MRI在檢測極小病灶(直徑小于1 cm)方面存在假陽性的風險。因此,在實際診斷過程中,需要結合多種影像學檢查結果進行綜合分析與判斷[6,11]。
然而,由于常規的RFA操作只在二維超聲引導下進行,不能提供癌灶在多個平面上的形態信息,這有可能導致進針位置不理想、腫瘤消融邊緣不足等最終導致局部腫瘤的殘留。為克服二維超聲的局限性,有研究團隊[12]引入三維超聲融合成像,通過實時超聲和三維超聲融合成像,在確保5 mm的消融邊緣前提下放置消融針,實現對癌灶的完全消融,以降低術后的局部進展率。但是肝癌具有高侵襲性,其主要病理學上的傳播方式是沿著門靜脈流域進行擴散,這也是術后復發及發生肝內轉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只在三維層面完成癌灶的消融,并不能有效應對癌灶沿門靜脈流域播散的風險。為了實現肝癌治療的腫瘤學獲益,幕內雅敏教授提出了門靜脈流域解剖性肝切除(anatomic resection based on portal territory, PT-AR)理論[13],其核心是以門靜脈流域所劃分的肝段或亞段為基本解剖單位,在對含有腫瘤的亞肝段進行系統性切除手術的同時,應確保完整切除亞肝段對應的門靜脈流域的Glisson系統(包含肝動脈、門靜脈和膽管)。因此,術前行CT血管成像、肝臟分區及脈管系統三維重建,以評估腫瘤占位與相應亞肝段門靜脈流域間的解剖關系,這對于指導手術進行十分有必要。受此啟發,我們在行RFA時,也要追求在三維層面實現病灶的完全消融的同時,還要實現對癌灶所在肝亞段以及癌灶供血血管的解剖性消融。 這就需要我們在術前對患者進行個性化的肝臟脈管系統三維重建,以便我們在術前對癌灶進行精準定位,從而為術中精準穿刺、實現亞段的解剖性RFA做好準備。
除此之外,還需評估患者是否存在以下合并癥。① 食管胃底靜脈曲張:術前需行胃鏡檢查,以準確評估靜脈曲張的嚴重程度,從而充分預防其可能出現的破裂出血情況。② 心血管疾病且正在應用抗凝藥物:各消融操作規范中并未嚴格規定術前必須停用抗凝藥物,只要凝血功能及血小板計數維持在手術可接受范圍內,便不構成手術禁忌。然而我們觀察到,此類患者使用抗凝藥物后,盡管檢測指標仍處于手術安全區間內,出血風險卻有所上升。因此我們建議請心內科醫生會診排除相關風險后,于RFA術前3 d暫停使用抗凝藥物,來降低由穿刺操作可能帶來的出血風險。③ 膽腸吻合術后:肝內膽管內的菌群生態平衡在膽腸吻合術后遭到破壞,導致大量革蘭陰性細菌在膽管定植。這些細菌可利用RFA后壞死的肝臟組織作為培養基進行繁殖增生,故術后在消融區域易形成感染或膿腫。因此為降低感染風險,建議在行RFA前后針對革蘭陰性菌使用抗生素進行預防。
3 在精準治療理念指導下系統化開展RFA治療
正如精準外科理念指導肝癌手術切除治療以提升療效,要實現RFA在治療肝癌中的最佳效果,同樣需要立足于規范化、個性化及系統化的手術操作與治療方案,致力于增加治療的確定性、預見性和可管理性[14]。
3.1 精準消融
為實現精準消融治療,術者需遵循精準肝臟外科的指導原則進行腫瘤消融,具體策略如下:① 消融區域應至少覆蓋腫瘤組織外1 cm的安全邊緣。據相關研究[15]證實,擴大消融范圍能顯著減少腫瘤局部復發的風險,并延長患者的生存期。② 當條件允許,尤其是針對單發小肝癌的治療時,應優先考慮采用“不接觸式”消融技術即“No Touch”技術進行操作。我們的研究成果[16]顯示,該技術的應用能有效降低腫瘤局部復發的概率。③ 通過術前三維成像,分析肝亞段與腫瘤的位置關系,合理選擇進針位置、進針數量及消融范圍,以實現亞肝段的解剖性消融[17]。
3.2 術后復查與隨訪
術后要及時復查了解消融效果。有研究[18]顯示,RFA術后15 min即可借助超聲造影技術對治療效果及安全性進行即時評估。我們的標準操作流程是:在消融術后20~30 min,行延遲超聲造影復查。首先檢查肝臟周邊是否存在積液或其他出血表現;然后通過造影進一步確認毀損病灶的完整性、是否存在殘留病灶及安全邊界是否充分。術后當晚(約消融術后9 h)在床旁行超聲檢查,以監測胸腹部是否存在積液等出血表現。術后次日,再次行超聲造影或增強CT檢查,以重新評估病灶的消融狀態,若情況穩定,患者可在術后第3天出院。消融術后1個月,還需行釓塞酸二鈉增強MRI檢查進行第3次消融效果評估。只有當消融后的病灶未表現強化并具備充足的安全邊緣時,方可判定實現了完全消融。 以后每3個月復查1次相關實驗室指標及影像學檢查,以評估治療效果。
3.3 RFA綜合治療
聯合免疫及靶向藥物進行綜合治療。近年來肝癌靶向和免疫藥物的不斷更新迭代,為RFA綜合治療肝癌提供了更系統化的選擇[19]。研究[20]發現,應用針對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藥物能有效降低肝癌組織的血供,進而減弱熱沉降效應,增加單次消融的體積范圍,并且在術后還能起到控制殘余癌細胞增殖的作用。另有研究[21-22]顯示,將抗腫瘤免疫治療與局部治療(如RFA)相結合可提高治療效果。具體而言,RFA引發的炎癥因子大量釋放及新的腫瘤抗原暴露,可有助于重塑腫瘤組織的免疫微環境,從而增強免疫藥物的抗腫瘤效果。我們的一項研究[23]表明, 采用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與RFA聯合治療,能顯著改善RFA的療效,提高患者的遠期生存率。此外,在探索RFA與免疫藥物聯合應用的研究[20]中,我們也驗證了消融術聯合程序性死亡受體1單抗能夠減少消融后的腫瘤復發,進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4 總結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民眾健康意識的顯著提升,尤其是高危群體對于定期體檢的重視度不斷加強,小肝癌在肝癌總體病例中的占比預計將呈現上升趨勢。在此背景下,消融技術、影像學手段以及綜合治療策略的快速發展,正極大地促進著消融治療的效果提升。以下這些技術的發展為我們對消融療法能夠逐步替代或作為手術切除治療小肝癌的重要補充手段,增添了更多信心與期待。① 靶向免疫藥物的更新迭代: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肝癌治療藥物涌現出來,如索拉非尼、瑞戈非尼、侖伐替尼、卡博替尼、雷莫蘆單克隆抗體、納武利尤單克隆抗體、帕博利珠單克隆抗體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靶向及免疫治療藥物,顯著延長了中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24]。② 3D成像技術在圍術期的應用:該技術在肝癌RFA圍術期的應用極大地提升了手術的精準度和治療效果,其不僅可在術前規劃中明確腫瘤位置與大小、評估肝臟血管結構、計算殘肝體積,在術中指導實時定位腫瘤、監測消融范圍、引導手術操作,還可在術后評估消融效果、預測復發風險。③ 消融新技術的發展:如不可逆電穿孔技術,利用高壓電脈沖在細胞膜上打出納米級不可逆孔隙,導致腫瘤細胞凋亡,區別于傳統冷熱消融技術,在有效消融腫瘤的同時不易損傷血管、膽管、神經等重要結構,減少消融術后嚴重并發癥的產生[25]。
綜上,要做到肝癌的精準消融治療,應從精準外科理念出發,規范化選擇肝癌行RFA的適應證,個體化進行RFA術前準備及評估,系統化開展RFA治療。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閆煜政負責檢索、閱讀及分析相關文獻并撰寫論文;肖嗣傑負責檢索相關文獻、完善并總結要點;馬寬生提出論文撰寫思路,并審閱文章及提出修改意見。
根據中國國家癌癥中心發布的數據,2022年全國原發性肝癌(以下簡稱肝癌)發病人數36.77萬(位居各種癌癥的第4位),因肝癌死亡人數31.65 萬(位居各種癌癥的第2位)。國內外最新的肝癌治療指南把消融治療與肝切除和肝移植同列為根治性治療小肝癌的治療方式,其中消融治療又以射頻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最為常見[1-2]。消融治療有療效確切、微創價廉、對肝功能影響小和并發癥少的特點,具有更廣泛的適應證,其在早期肝癌患者中可獲得與手術切除類似的療效。但是,也有研究[3]指出肝癌患者行RFA后的局部復發率顯著高于手術切除。近年來,以“確定性、預見性、可控性、規范化、個體化、系統化”為核心要素的精準外科理念的提出和實踐[4],為我們提高RFA 治療肝癌的療效提供了新思路。筆者團隊在原有1萬余例次的RFA治療經驗基礎上,積極開展肝癌的精準消融治療相關研究,現筆者將結合現有文獻及團隊經驗,論述精準外科理念在肝癌RFA治療中的應用與前景。
1 在精準治療理念指導下規范化選擇RFA的適應證
近年來,公眾健康意識不斷提升以及體檢覆蓋范圍日益廣泛,同時醫療技術的飛速發展,尤其是肝癌篩查與監測技術的顯著進步,如甲胎蛋白異質體3、異常凝血酶原、高爾基體蛋白73、骨橋蛋白等新型標志物和包括循環微小核糖核酸、循環腫瘤DNA以及循環腫瘤細胞在內的液體活檢技術[5],以及以釓塞酸二鈉增強的MR和超聲成像為代表的影像學技術的進步[6-7],不僅提高了檢測的敏感度和特異度,還使得微小病灶的識別成為可能,肝癌患者在早期便能被準確診斷。在此大背景下,肝癌患者的早期精確診斷不僅提高了患者的預后、改善患者術后生活質量,還為醫生爭取到了選擇更加精準化治療方案的時間窗口,從而以更加微創的方式來治療肝癌。
RFA作為肝癌的微創治療手段,是在影像技術的引導下,將治療電極精準穿刺至病灶內部,通過電極釋放的高頻電磁波引發局部離子振蕩摩擦產生高溫,促使穿刺點及其周邊癌組織發生凝固性壞死。然而,受限于當前技術水平和患者的耐受性,同時為了降低穿刺相關并發癥的風險,穿刺電極的直徑通常不超過2 mm,且單次消融所能覆蓋的病灶直徑一般不超過3 cm。研究[8]表明,病灶大小對RFA實現完全消融的效果有顯著影響,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一是病灶周圍血管的血流會帶走熱量(熱沉降效應),從而影響消融的溫度,繼而影響消融效果;二是傳統RFA通常在二維超聲或(和)CT引導下操作,消融電極可能無法精確置于病灶的三維中心,導致其他平面的消融不足;三是每次消融過程中產生的水蒸汽會妨礙即時觀察消融后病灶內是否殘留癌組織;四是病灶形態的不規則性。因此,若病灶的直徑大于3 cm,RFA往往難以消融完全。
故對于肝癌行RFA的適應證,最新的指南[1]指出:單個腫瘤、直徑 ≤5 cm,或2~ 3個腫瘤、 最大直徑 ≤3 cm可行RFA。對于直徑3~7 cm由于各種原因不可切除的單發腫瘤或多發腫瘤,可以先行肝動脈化療栓塞術后再行RFA。另外,當病灶位于膽囊或第一肝門附近且間距小于5 mm時,通常會縮短消融時間以避免高溫對膽管及膽囊的破壞,但是這也會影響對病灶的完全消融。RFA的療效不僅受病灶大小的影響,還對患者自身的健康狀況、肝功能狀態及凝血功能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患者在過去6個月內若發生過食管胃底靜脈曲張并發破裂出血,則必須在接受止血措施之后,方可考慮進行 RFA 治療,否則可能引發再次出血的風險[9]。
2 在精準治療理念指導下個體化進行RFA術前準備及評估
近年來,傳統經驗外科的治療理念正向現代精準外科轉變。其中,精準肝膽外科要求實現雙重目標:一方面,需精準且徹底地移除目標病灶,并確保手術切緣的安全性,以預防復發;另一方面,必須確保剩余肝臟的解剖完整性,并最大化其功能性體積,從而在保證手術效果的同時,減少手術對機體的損傷。整個手術過程中,需嚴格控制創傷范圍,有效管理出血情況,力求將并發癥的發生降至最低,最終使手術患者能夠獲得最為理想的治療效果與術后恢復[10]。
相較于在寬闊視野下進行機械性手術切除肝癌,RFA需要在影像技術引導下將治療電極經皮穿刺入肝癌病灶內。因此要在RFA過程中貫徹精準治療的理念,術前對肝癌組織的精準定位非常重要,并且需對患者進行全面嚴格的術前評估。
首先,常規RFA全程是在超聲或(和)CT引導下進行的。以超聲引導為例,術前進行肝臟超聲造影檢查對癌灶進行定位是有必要的。此外,為了進一步提升診斷的精確性,尤其是針對直徑1 cm以下的微小病灶,術前采用釓塞酸二鈉增強的MRI檢查也同樣重要。在行釓塞酸二鈉增強 MRI后,在該圖像的提示下再做超聲造影檢查以確保對病灶的精準定位和量化評估,從而保證手術的順利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釓塞酸二鈉增強的MRI在檢測極小病灶(直徑小于1 cm)方面存在假陽性的風險。因此,在實際診斷過程中,需要結合多種影像學檢查結果進行綜合分析與判斷[6,11]。
然而,由于常規的RFA操作只在二維超聲引導下進行,不能提供癌灶在多個平面上的形態信息,這有可能導致進針位置不理想、腫瘤消融邊緣不足等最終導致局部腫瘤的殘留。為克服二維超聲的局限性,有研究團隊[12]引入三維超聲融合成像,通過實時超聲和三維超聲融合成像,在確保5 mm的消融邊緣前提下放置消融針,實現對癌灶的完全消融,以降低術后的局部進展率。但是肝癌具有高侵襲性,其主要病理學上的傳播方式是沿著門靜脈流域進行擴散,這也是術后復發及發生肝內轉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只在三維層面完成癌灶的消融,并不能有效應對癌灶沿門靜脈流域播散的風險。為了實現肝癌治療的腫瘤學獲益,幕內雅敏教授提出了門靜脈流域解剖性肝切除(anatomic resection based on portal territory, PT-AR)理論[13],其核心是以門靜脈流域所劃分的肝段或亞段為基本解剖單位,在對含有腫瘤的亞肝段進行系統性切除手術的同時,應確保完整切除亞肝段對應的門靜脈流域的Glisson系統(包含肝動脈、門靜脈和膽管)。因此,術前行CT血管成像、肝臟分區及脈管系統三維重建,以評估腫瘤占位與相應亞肝段門靜脈流域間的解剖關系,這對于指導手術進行十分有必要。受此啟發,我們在行RFA時,也要追求在三維層面實現病灶的完全消融的同時,還要實現對癌灶所在肝亞段以及癌灶供血血管的解剖性消融。 這就需要我們在術前對患者進行個性化的肝臟脈管系統三維重建,以便我們在術前對癌灶進行精準定位,從而為術中精準穿刺、實現亞段的解剖性RFA做好準備。
除此之外,還需評估患者是否存在以下合并癥。① 食管胃底靜脈曲張:術前需行胃鏡檢查,以準確評估靜脈曲張的嚴重程度,從而充分預防其可能出現的破裂出血情況。② 心血管疾病且正在應用抗凝藥物:各消融操作規范中并未嚴格規定術前必須停用抗凝藥物,只要凝血功能及血小板計數維持在手術可接受范圍內,便不構成手術禁忌。然而我們觀察到,此類患者使用抗凝藥物后,盡管檢測指標仍處于手術安全區間內,出血風險卻有所上升。因此我們建議請心內科醫生會診排除相關風險后,于RFA術前3 d暫停使用抗凝藥物,來降低由穿刺操作可能帶來的出血風險。③ 膽腸吻合術后:肝內膽管內的菌群生態平衡在膽腸吻合術后遭到破壞,導致大量革蘭陰性細菌在膽管定植。這些細菌可利用RFA后壞死的肝臟組織作為培養基進行繁殖增生,故術后在消融區域易形成感染或膿腫。因此為降低感染風險,建議在行RFA前后針對革蘭陰性菌使用抗生素進行預防。
3 在精準治療理念指導下系統化開展RFA治療
正如精準外科理念指導肝癌手術切除治療以提升療效,要實現RFA在治療肝癌中的最佳效果,同樣需要立足于規范化、個性化及系統化的手術操作與治療方案,致力于增加治療的確定性、預見性和可管理性[14]。
3.1 精準消融
為實現精準消融治療,術者需遵循精準肝臟外科的指導原則進行腫瘤消融,具體策略如下:① 消融區域應至少覆蓋腫瘤組織外1 cm的安全邊緣。據相關研究[15]證實,擴大消融范圍能顯著減少腫瘤局部復發的風險,并延長患者的生存期。② 當條件允許,尤其是針對單發小肝癌的治療時,應優先考慮采用“不接觸式”消融技術即“No Touch”技術進行操作。我們的研究成果[16]顯示,該技術的應用能有效降低腫瘤局部復發的概率。③ 通過術前三維成像,分析肝亞段與腫瘤的位置關系,合理選擇進針位置、進針數量及消融范圍,以實現亞肝段的解剖性消融[17]。
3.2 術后復查與隨訪
術后要及時復查了解消融效果。有研究[18]顯示,RFA術后15 min即可借助超聲造影技術對治療效果及安全性進行即時評估。我們的標準操作流程是:在消融術后20~30 min,行延遲超聲造影復查。首先檢查肝臟周邊是否存在積液或其他出血表現;然后通過造影進一步確認毀損病灶的完整性、是否存在殘留病灶及安全邊界是否充分。術后當晚(約消融術后9 h)在床旁行超聲檢查,以監測胸腹部是否存在積液等出血表現。術后次日,再次行超聲造影或增強CT檢查,以重新評估病灶的消融狀態,若情況穩定,患者可在術后第3天出院。消融術后1個月,還需行釓塞酸二鈉增強MRI檢查進行第3次消融效果評估。只有當消融后的病灶未表現強化并具備充足的安全邊緣時,方可判定實現了完全消融。 以后每3個月復查1次相關實驗室指標及影像學檢查,以評估治療效果。
3.3 RFA綜合治療
聯合免疫及靶向藥物進行綜合治療。近年來肝癌靶向和免疫藥物的不斷更新迭代,為RFA綜合治療肝癌提供了更系統化的選擇[19]。研究[20]發現,應用針對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藥物能有效降低肝癌組織的血供,進而減弱熱沉降效應,增加單次消融的體積范圍,并且在術后還能起到控制殘余癌細胞增殖的作用。另有研究[21-22]顯示,將抗腫瘤免疫治療與局部治療(如RFA)相結合可提高治療效果。具體而言,RFA引發的炎癥因子大量釋放及新的腫瘤抗原暴露,可有助于重塑腫瘤組織的免疫微環境,從而增強免疫藥物的抗腫瘤效果。我們的一項研究[23]表明, 采用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與RFA聯合治療,能顯著改善RFA的療效,提高患者的遠期生存率。此外,在探索RFA與免疫藥物聯合應用的研究[20]中,我們也驗證了消融術聯合程序性死亡受體1單抗能夠減少消融后的腫瘤復發,進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4 總結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民眾健康意識的顯著提升,尤其是高危群體對于定期體檢的重視度不斷加強,小肝癌在肝癌總體病例中的占比預計將呈現上升趨勢。在此背景下,消融技術、影像學手段以及綜合治療策略的快速發展,正極大地促進著消融治療的效果提升。以下這些技術的發展為我們對消融療法能夠逐步替代或作為手術切除治療小肝癌的重要補充手段,增添了更多信心與期待。① 靶向免疫藥物的更新迭代: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肝癌治療藥物涌現出來,如索拉非尼、瑞戈非尼、侖伐替尼、卡博替尼、雷莫蘆單克隆抗體、納武利尤單克隆抗體、帕博利珠單克隆抗體等為代表的一系列靶向及免疫治療藥物,顯著延長了中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24]。② 3D成像技術在圍術期的應用:該技術在肝癌RFA圍術期的應用極大地提升了手術的精準度和治療效果,其不僅可在術前規劃中明確腫瘤位置與大小、評估肝臟血管結構、計算殘肝體積,在術中指導實時定位腫瘤、監測消融范圍、引導手術操作,還可在術后評估消融效果、預測復發風險。③ 消融新技術的發展:如不可逆電穿孔技術,利用高壓電脈沖在細胞膜上打出納米級不可逆孔隙,導致腫瘤細胞凋亡,區別于傳統冷熱消融技術,在有效消融腫瘤的同時不易損傷血管、膽管、神經等重要結構,減少消融術后嚴重并發癥的產生[25]。
綜上,要做到肝癌的精準消融治療,應從精準外科理念出發,規范化選擇肝癌行RFA的適應證,個體化進行RFA術前準備及評估,系統化開展RFA治療。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全體作者閱讀并理解了《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的政策聲明,我們沒有相互競爭的利益。
作者貢獻聲明:閆煜政負責檢索、閱讀及分析相關文獻并撰寫論文;肖嗣傑負責檢索相關文獻、完善并總結要點;馬寬生提出論文撰寫思路,并審閱文章及提出修改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