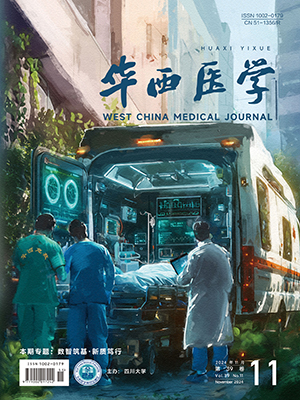引用本文: 文穎燕, 陳俊珊, 詹偉杰, 簡小云, 李家春. 多西環素用于喹諾酮類治療失敗的大環內酯類耐藥肺炎支原體肺炎一例. 華西醫學, 2024, 39(8): 1333-1334. doi: 10.7507/1002-0179.202402199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病例介紹 患者,女,31 歲,因“反復發熱、咳嗽 2 周余”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被收入廣州中醫藥大學第八臨床醫學院即佛山市中醫院(以下簡稱“我院”)呼吸內科治療。入院 2 周前患者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熱峰為 39℃,伴有咳嗽、咳白黏痰,遂至外院急診科就診,血清肺炎支原體(Mycoplasma pneumoniae, MP)抗體檢測結果呈陰性,胸片未見明顯異常,予 1 周抗感染(口服左氧氟沙星 0.5 g/次、1 次/d)、退熱等處理后發熱緩解,但仍反復咳嗽。入院 1 周前患者再次出現發熱,熱峰為 39.9℃,于當地醫院就診,血清 MP 抗體檢測結果呈陰性,予 1 周抗感染(經驗性口服阿奇霉素 0.5 g/次、1 次/d 聯合口服莫西沙星 0.4 g/次、1 次/d)及復方甲氧那明膠囊、洛索洛芬鈉片止咳、退熱處理。患者仍反復發熱及咳嗽咳痰,遂至我院就診,9 月 20 日胸部 CT 提示右肺下葉背段炎癥(圖1a),門診查血清 MP 抗體仍為陰性,患者為求進一步系統診治,由門診以“社區獲得性肺炎”收入呼吸內科。
 圖1
患者胸部 CT 圖像
圖1
患者胸部 CT 圖像
a. 入院前(2023-09-20);b. 出院后復診時(2023-10-27)
入院體格檢查:體溫 38.5℃,心率 78 次/min,呼吸頻率 16 次/min,血壓 116/72 mm Hg(1 mm Hg=0.133 kPa)。全身未見皮疹,雙側呼吸對稱,叩診清音,雙肺呼吸音稍粗,右下肺可聞及少許濕啰音,無胸膜摩擦音,語音共振雙側對稱,余無異常。患者訴近期消瘦 2 kg。患者既往史、家族史、個人史無特殊。入院當天查炎癥標志物示紅細胞沉降率輕微升高(38 mm/h);血常規、降鈣素原、超敏 C 反應蛋白、淀粉樣蛋白、凝血功能、心肝腎功能、尿糞常規、傳染病檢查等均無異常。患者雖門診血清 MP 抗體呈陰性,但無法排除其可能處于抗體窗口期,故入院后予 MP RNA 病原學檢測(咽拭子),結果為陰性。因患者反復發熱,持續存在咳嗽和消瘦,胸部 CT 病灶位于右肺下葉背段,尚不能完全排除結核感染可能,予行結核感染 T 細胞檢測、結核菌素試驗、痰培養、結核菌痰涂片等檢查,結果均為陰性。在治療上因暫未能排除肺結核感染可能,根據 2016 年版中國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指南[1]建議,入院當天即予靜脈滴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4.5 g/次、每 8 小時 1 次抗感染。入院治療 72 h 后患者仍反復發熱,咳嗽咳痰癥狀無緩解。為明確病原體和進一步指導臨床用藥,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后,計劃行電子支氣管鏡檢查留取肺泡灌洗液予宏基因組學第二代測序(metagenomic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入院第 4 天,行電子支氣管鏡檢查留取右下肺背段肺泡灌洗液并送 mNGS 檢測。入院第 5 天,患者肺泡灌洗液 mNGS 結果提示標本中 MP 濃度為 5×104 拷貝/mL,基因測序信號強度強,并檢測到該 MP 存在對大環內酯類耐藥的基因突變點(23S rRNA 區域的 2063A 點突變)。根據檢測結果,考慮患者為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肺炎(MP pneumonia, MPP),予調整用藥方案,于入院第 5 天停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改為口服多西環素首劑 0.2 mg,后 0.1 mg/次、2 次/d 抗 MP 感染。用藥 72 h 后再評估顯示,患者發熱緩解,咳嗽咳痰等癥狀明顯改善,病情好轉穩定,于第 9 天出院。出院當天予復查血清 MP 抗體仍為陰性。出院后予多西環素繼續治療,周期為 7 d,患者多西環素抗 MP 療程總共為 14 d。患者出院后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至我院門診復診,已無發熱、咳嗽咳痰,復查胸部 CT 提示右下肺背段炎癥病灶已完全吸收(圖1b)。
討論 MPP 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良性的自限性疾病,但其亦存在導致各種肺外并發癥并進展為重癥肺炎的可能[2]。雖然目前尚無足夠的證據表明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感染可加重 MPP 病情,但有研究提示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感染者的發熱時間和抗感染所需時間均延長,且其肺部影像學改變更重[2-3],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被認為可能是導致難治性 MPP的重要原因[4]。因此,臨床上對于 MPP 的早期診斷、對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早期識別和診斷以及針對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抗微生物藥的選擇十分重要。
在 MPP 診斷上,專家共識指出病原學檢測與血清學聯合是目前首選推薦的診斷策略,而 MP RNA 檢測聯合 MP 血清抗體檢測是診斷 MP 感染的一級推薦方法[5]。回顧本病例診斷過程,患者多次查血清 MP 抗體均為陰性。血清 MP 抗體檢測具有特異度高、不受抗微生物藥影響的優點,但抗體的產生有時間窗和個體差異,臨床上需要結合患者病程、基礎情況以及年齡等因素綜合考慮,如免疫功能低下和免疫缺陷者都存在不產生或產生低滴度抗體的可能[5],故不排除本病例血清抗體出現假陰性的可能。本病例入院后也進行了 MP RNA 檢測,結果也為陰性。MP RNA 檢測陽性常提示 MP 近期感染而非既往感染,被認為是目前早期快速診斷、判斷療效的最好方法之一,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血清 MP 抗體檢測存在窗口期的缺陷[5-6]。但其局限性在于 RNA 只存在活菌體中,當病程長或存在免疫缺陷時可能會導致其活性下降或裂解而不易被檢測到。有研究顯示,短病程(1~3 d)的 MP RNA 陽性率明顯高于長病程(8~14 d),其陽性率分別是 95.2%和 75.8%[7]。而檢測前是否使用過大環內酯類藥物對 MP RNA 的檢測準確性也有影響,未使用過大環內酯類藥物時陽性率更高[7]。本病例病程較長,且使用了大環內酯類藥物,故可能導致 MP RNA 檢測出現假陰性,提示即使 MP RNA 檢測和 MP 血清抗體檢測均為陰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MP 感染。
本病例經過多種常規檢測方法仍未明確病原體,經治療后癥狀無好轉,故采用電子支氣管鏡下留取肺泡灌洗液送 mNGS 檢測,結果發現高濃度 MP,且該 MP 存在對大環內酯類藥物耐藥的基因突變點,最終確診為大環內酯類耐藥 MPP,在更換為多西環素治療后患者病情迅速好轉。mNGS 檢測技術具有耗時短、檢測范圍廣、靈敏度高的特點,當臨床上出現不明原因的感染性疾病,傳統檢測方法無法明確病原體且經驗性用藥后患者病情仍遷延不愈時,可將 mNGS 作為首選的輔助檢測手段[8]。
在治療上,我國 2016 年版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與治療指南[1]中已將四環素類和喹諾酮類藥物作為 MPP 的首選用藥,大環內酯類則退居二線,但亦補充稱在支原體耐藥率較低的地區仍可選用大環內酯類藥物,但該指南中暫未具體說明耐藥的分布區域及地區耐藥情況。故 MPP 成人患者若在初始治療時選用大環內酯類藥物,則可根據我國成人 MPP 診治專家共識[9]中的建議,即關注患者 72 h 內癥狀是否有改善,若無明顯改善,應考慮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可能,并及早更換為其他抗微生物藥。
盡管四環素類和喹諾酮類藥物被認為是 MPP 的首選用藥,但上述指南中并未指出何者更優,究竟首選四環素類還是喹諾酮類尚無一致意見。本病例曾外院口服莫西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各 1 周抗感染治療,仍無好轉。而在使用多西環素后,于 72 h 后即見癥狀明顯改善,出院后復查影像學顯示感染完全吸收,兩類藥物的療效在本案例中存在較大差異,不能排除 MP 對喹諾酮類耐藥的可能。已有報道指出生殖支原體對氟喹諾酮類藥物存在臨床耐藥,其耐藥基因位點是 A2071G/G285C[10];生殖支原體又是一種在發育進展上與 MP 極接近的泌尿生殖系統支原體,其耐藥機制與 MP 相似[11],故不排除 MP 對喹諾酮類藥物也存在臨床耐藥的可能。另外,在藥理作用上,有研究指出四環素類藥物如米諾環素和多西環素對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抗菌后效應高于氟喹諾酮類藥物如托西酸托氟沙星,且多西環素及米諾環素在 24 h 內實現退熱的情況優于托西酸托氟沙星,在其用藥 3~5 d 后聚合酶鏈反應復查結果顯示 MP DNA 拷貝數亦明顯優于托西酸托氟沙星[12]。因此,結合本病例,我們認為對于大環內酯類耐藥的成人 MP 感染治療,或可優先選擇四環素類如多西環素進行抗 MP 治療,其抗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效果可能比喹諾酮類藥物更佳。
綜上,雖指南推薦以 MP RNA 檢測與血清 MP 特異性抗體相結合更有利于 MPP 的早期診斷,但臨床上出現兩者同時陰性時亦不能完全排除 MPP。在傳統檢測方法無法明確病原體且經驗性治療后患者病情仍遷延不愈時,可將 mNGS 作為首選的輔助檢測手段,并可予同步行耐藥基因檢測,能夠快速且精準地指導臨床醫師優化用藥方案。而在大環內酯類耐藥的成人 MP 感染的治療上,多西環素等四環素類藥物可能比喹諾酮類藥物療效更優,必要時可優先選擇,但本病例經驗的推廣仍需更多的臨床數據來驗證。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病例介紹 患者,女,31 歲,因“反復發熱、咳嗽 2 周余”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被收入廣州中醫藥大學第八臨床醫學院即佛山市中醫院(以下簡稱“我院”)呼吸內科治療。入院 2 周前患者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熱峰為 39℃,伴有咳嗽、咳白黏痰,遂至外院急診科就診,血清肺炎支原體(Mycoplasma pneumoniae, MP)抗體檢測結果呈陰性,胸片未見明顯異常,予 1 周抗感染(口服左氧氟沙星 0.5 g/次、1 次/d)、退熱等處理后發熱緩解,但仍反復咳嗽。入院 1 周前患者再次出現發熱,熱峰為 39.9℃,于當地醫院就診,血清 MP 抗體檢測結果呈陰性,予 1 周抗感染(經驗性口服阿奇霉素 0.5 g/次、1 次/d 聯合口服莫西沙星 0.4 g/次、1 次/d)及復方甲氧那明膠囊、洛索洛芬鈉片止咳、退熱處理。患者仍反復發熱及咳嗽咳痰,遂至我院就診,9 月 20 日胸部 CT 提示右肺下葉背段炎癥(圖1a),門診查血清 MP 抗體仍為陰性,患者為求進一步系統診治,由門診以“社區獲得性肺炎”收入呼吸內科。
 圖1
患者胸部 CT 圖像
圖1
患者胸部 CT 圖像
a. 入院前(2023-09-20);b. 出院后復診時(2023-10-27)
入院體格檢查:體溫 38.5℃,心率 78 次/min,呼吸頻率 16 次/min,血壓 116/72 mm Hg(1 mm Hg=0.133 kPa)。全身未見皮疹,雙側呼吸對稱,叩診清音,雙肺呼吸音稍粗,右下肺可聞及少許濕啰音,無胸膜摩擦音,語音共振雙側對稱,余無異常。患者訴近期消瘦 2 kg。患者既往史、家族史、個人史無特殊。入院當天查炎癥標志物示紅細胞沉降率輕微升高(38 mm/h);血常規、降鈣素原、超敏 C 反應蛋白、淀粉樣蛋白、凝血功能、心肝腎功能、尿糞常規、傳染病檢查等均無異常。患者雖門診血清 MP 抗體呈陰性,但無法排除其可能處于抗體窗口期,故入院后予 MP RNA 病原學檢測(咽拭子),結果為陰性。因患者反復發熱,持續存在咳嗽和消瘦,胸部 CT 病灶位于右肺下葉背段,尚不能完全排除結核感染可能,予行結核感染 T 細胞檢測、結核菌素試驗、痰培養、結核菌痰涂片等檢查,結果均為陰性。在治療上因暫未能排除肺結核感染可能,根據 2016 年版中國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指南[1]建議,入院當天即予靜脈滴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4.5 g/次、每 8 小時 1 次抗感染。入院治療 72 h 后患者仍反復發熱,咳嗽咳痰癥狀無緩解。為明確病原體和進一步指導臨床用藥,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后,計劃行電子支氣管鏡檢查留取肺泡灌洗液予宏基因組學第二代測序(metagenomic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mNGS)。入院第 4 天,行電子支氣管鏡檢查留取右下肺背段肺泡灌洗液并送 mNGS 檢測。入院第 5 天,患者肺泡灌洗液 mNGS 結果提示標本中 MP 濃度為 5×104 拷貝/mL,基因測序信號強度強,并檢測到該 MP 存在對大環內酯類耐藥的基因突變點(23S rRNA 區域的 2063A 點突變)。根據檢測結果,考慮患者為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肺炎(MP pneumonia, MPP),予調整用藥方案,于入院第 5 天停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改為口服多西環素首劑 0.2 mg,后 0.1 mg/次、2 次/d 抗 MP 感染。用藥 72 h 后再評估顯示,患者發熱緩解,咳嗽咳痰等癥狀明顯改善,病情好轉穩定,于第 9 天出院。出院當天予復查血清 MP 抗體仍為陰性。出院后予多西環素繼續治療,周期為 7 d,患者多西環素抗 MP 療程總共為 14 d。患者出院后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至我院門診復診,已無發熱、咳嗽咳痰,復查胸部 CT 提示右下肺背段炎癥病灶已完全吸收(圖1b)。
討論 MPP 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良性的自限性疾病,但其亦存在導致各種肺外并發癥并進展為重癥肺炎的可能[2]。雖然目前尚無足夠的證據表明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感染可加重 MPP 病情,但有研究提示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感染者的發熱時間和抗感染所需時間均延長,且其肺部影像學改變更重[2-3],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被認為可能是導致難治性 MPP的重要原因[4]。因此,臨床上對于 MPP 的早期診斷、對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早期識別和診斷以及針對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抗微生物藥的選擇十分重要。
在 MPP 診斷上,專家共識指出病原學檢測與血清學聯合是目前首選推薦的診斷策略,而 MP RNA 檢測聯合 MP 血清抗體檢測是診斷 MP 感染的一級推薦方法[5]。回顧本病例診斷過程,患者多次查血清 MP 抗體均為陰性。血清 MP 抗體檢測具有特異度高、不受抗微生物藥影響的優點,但抗體的產生有時間窗和個體差異,臨床上需要結合患者病程、基礎情況以及年齡等因素綜合考慮,如免疫功能低下和免疫缺陷者都存在不產生或產生低滴度抗體的可能[5],故不排除本病例血清抗體出現假陰性的可能。本病例入院后也進行了 MP RNA 檢測,結果也為陰性。MP RNA 檢測陽性常提示 MP 近期感染而非既往感染,被認為是目前早期快速診斷、判斷療效的最好方法之一,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血清 MP 抗體檢測存在窗口期的缺陷[5-6]。但其局限性在于 RNA 只存在活菌體中,當病程長或存在免疫缺陷時可能會導致其活性下降或裂解而不易被檢測到。有研究顯示,短病程(1~3 d)的 MP RNA 陽性率明顯高于長病程(8~14 d),其陽性率分別是 95.2%和 75.8%[7]。而檢測前是否使用過大環內酯類藥物對 MP RNA 的檢測準確性也有影響,未使用過大環內酯類藥物時陽性率更高[7]。本病例病程較長,且使用了大環內酯類藥物,故可能導致 MP RNA 檢測出現假陰性,提示即使 MP RNA 檢測和 MP 血清抗體檢測均為陰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MP 感染。
本病例經過多種常規檢測方法仍未明確病原體,經治療后癥狀無好轉,故采用電子支氣管鏡下留取肺泡灌洗液送 mNGS 檢測,結果發現高濃度 MP,且該 MP 存在對大環內酯類藥物耐藥的基因突變點,最終確診為大環內酯類耐藥 MPP,在更換為多西環素治療后患者病情迅速好轉。mNGS 檢測技術具有耗時短、檢測范圍廣、靈敏度高的特點,當臨床上出現不明原因的感染性疾病,傳統檢測方法無法明確病原體且經驗性用藥后患者病情仍遷延不愈時,可將 mNGS 作為首選的輔助檢測手段[8]。
在治療上,我國 2016 年版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與治療指南[1]中已將四環素類和喹諾酮類藥物作為 MPP 的首選用藥,大環內酯類則退居二線,但亦補充稱在支原體耐藥率較低的地區仍可選用大環內酯類藥物,但該指南中暫未具體說明耐藥的分布區域及地區耐藥情況。故 MPP 成人患者若在初始治療時選用大環內酯類藥物,則可根據我國成人 MPP 診治專家共識[9]中的建議,即關注患者 72 h 內癥狀是否有改善,若無明顯改善,應考慮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可能,并及早更換為其他抗微生物藥。
盡管四環素類和喹諾酮類藥物被認為是 MPP 的首選用藥,但上述指南中并未指出何者更優,究竟首選四環素類還是喹諾酮類尚無一致意見。本病例曾外院口服莫西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各 1 周抗感染治療,仍無好轉。而在使用多西環素后,于 72 h 后即見癥狀明顯改善,出院后復查影像學顯示感染完全吸收,兩類藥物的療效在本案例中存在較大差異,不能排除 MP 對喹諾酮類耐藥的可能。已有報道指出生殖支原體對氟喹諾酮類藥物存在臨床耐藥,其耐藥基因位點是 A2071G/G285C[10];生殖支原體又是一種在發育進展上與 MP 極接近的泌尿生殖系統支原體,其耐藥機制與 MP 相似[11],故不排除 MP 對喹諾酮類藥物也存在臨床耐藥的可能。另外,在藥理作用上,有研究指出四環素類藥物如米諾環素和多西環素對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抗菌后效應高于氟喹諾酮類藥物如托西酸托氟沙星,且多西環素及米諾環素在 24 h 內實現退熱的情況優于托西酸托氟沙星,在其用藥 3~5 d 后聚合酶鏈反應復查結果顯示 MP DNA 拷貝數亦明顯優于托西酸托氟沙星[12]。因此,結合本病例,我們認為對于大環內酯類耐藥的成人 MP 感染治療,或可優先選擇四環素類如多西環素進行抗 MP 治療,其抗大環內酯類耐藥 MP 的效果可能比喹諾酮類藥物更佳。
綜上,雖指南推薦以 MP RNA 檢測與血清 MP 特異性抗體相結合更有利于 MPP 的早期診斷,但臨床上出現兩者同時陰性時亦不能完全排除 MPP。在傳統檢測方法無法明確病原體且經驗性治療后患者病情仍遷延不愈時,可將 mNGS 作為首選的輔助檢測手段,并可予同步行耐藥基因檢測,能夠快速且精準地指導臨床醫師優化用藥方案。而在大環內酯類耐藥的成人 MP 感染的治療上,多西環素等四環素類藥物可能比喹諾酮類藥物療效更優,必要時可優先選擇,但本病例經驗的推廣仍需更多的臨床數據來驗證。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