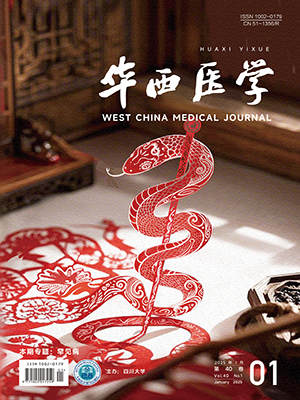急性筋膜間隙綜合征(acute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是蛇咬傷的嚴重并發癥之一,嚴重時可導致截肢甚至死亡。如何早期診斷和治療 ACS 仍是目前主要難題。該文聚焦 ACS 早期診斷的最新研究趨勢,重點闡述了新興監測技術在室間隔壓力測量、氧合監測、灌注監測等關鍵領域的應用,并綜合分析了手術和保守治療在內的多元化治療策略,旨在為臨床工作者提供更為精準的診療依據。
引用本文: 宋亞蘭, 馬增文, 許樹云, 錢微微, 周越, 童嘉樂. 蛇咬傷致急性筋膜間隙綜合征的研究進展. 華西醫學, 2024, 39(11): 1797-1801. doi: 10.7507/1002-0179.202406266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全球每年約有 540 萬起毒蛇咬傷事件,我國每年的毒蛇咬傷人數為 10 萬~30 萬,致殘率為 25%~30%,病死率達 5%[1]。急性筋膜間隙綜合征(acute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是毒蛇咬傷的嚴重并發癥之一,雖然發病率很低,但其輕者可能導致功能障礙,重者可導致截肢甚至死亡。目前,蛇咬傷致 ACS 的診斷主要依賴于醫生對病史和癥狀的識別、臨床經驗以及壓力監測等輔助檢查手段。ACS 的臨床典型癥狀為“6P”表現,即疼痛增加(increasing pain)、無脈(pulselessness)、感覺異常(paresthesia)、麻痹(paralysis)、蒼白(pallor)和異常溫度(poikilothermia)。然而,疼痛作為主觀性癥狀,受意識、神經麻痹、合作程度等多種因素影響,甚至有一些罕見的病例可能缺乏明顯疼痛。其他癥狀則屬于長時間缺血缺氧導致的晚期神經和血管損傷的表現[2]。盡管這些典型癥狀具有一定的診斷意義,但缺乏特異性和敏感性,僅憑癥狀進行診斷是不可靠的,可能導致漏診和治療延誤。因此,ACS 的早期診斷、及時治療和外科手術干預至關重要,對患肢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綜合分析近年來關于該疾病輔助診斷及治療策略的研究進展,旨在為臨床實踐提供更為精準的指導。
1 臨床診斷方法
1.1 室間隔壓力測量
室間隔壓力測量是診斷 ACS 的重要輔助方法,對于有 ACS 風險的患者,均應持續監測組織壓力[3]。目前尚未確立一個權威的壓力數值作為 ACS 診斷標準,普遍認為,當間隔內壓力高于 30~4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壓力差 ΔP(舒張壓減去室筋膜壓)≤30 mm Hg 時,可以診斷 ACS。Whitesides 法、Matsen 的連續監測技術、Rorabeck 的側孔針和裂縫導管測量法等傳統測量方法通過針頭或導管插入筋膜室內直接測量筋膜內壓力值,此類技術使用方法簡單,容易操作,一度成為測量壓力的“金標準”[4]。然而,研究發現 ACS 在筋膜室內的壓力分布并不均勻,且壓力測量易受操作者技術和測量部位的影響[5]。呂林等[6]采用改良 Whiteside 法在超聲引導下行骨筋膜室穿刺測壓,利用超聲進行定位,以減少操作帶來的影響,且無不良預后事件發生。盡管技術不斷改進,傳統方法仍無法改變可能會引起過度治療、創傷大、不易連續監測等問題,因此不推薦這些有創操作[7]。
近年來,隨著高科技的快速發展,ACS 的壓力檢測技術也取得了顯著進步。MY01 為已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醫療器械,是一種基于微機電系統技術的高精度可植入壓力傳感器,通過穿刺放置在肌肉組織內部,便能以 0.1 mm Hg 的精確度測量腔室壓力,能跟蹤壓力變化,并將壓力數據實時上傳至云存儲數據庫和手機應用程序。據相關案例報道,當 MY01 顯示壓力急劇上升且臨床癥狀輕微時,及時對患者進行筋膜切開手術,均預后良好[8-9]。Merle 等[8]以小鼠腹部腔室綜合征模擬肢體 ACS,發現 MY01 設備在精確度上比快速壓力 Stryker 監測儀、Synthes 腔室壓力監測系統設備至少提高了 670%。該技術操作簡單,不受操作技術及患者體溫、位置變化影響,有望成為早期診斷 ACS 的重要方法。然而也有研究報告認為壓力監測缺乏診斷特異性,僅憑壓力測量診斷 ACS 的假陽性率較高,不可將其作為唯一診斷標準[10-11]。因此,未來深入探究該方法的可靠性至關重要。
1.2 局部氧合監測
組織氧合水平下降是 ACS 的早期表現,能夠直接反映組織缺氧程度,比筋膜室壓力測量更具特異性[12]。近紅外光譜利用近紅外光穿透組織,通過測量血紅蛋白和肌紅蛋白等血紅素化合物的氧合狀態來評估肌肉組織的氧合、血流以及血管功能情況[13]。近紅外光譜具有區分不同隔室的優勢,但使用時需同時對比對側肢體的相同分室,以控制個體差異和時間變化;同時組織穿透深度有限,不能穿透小腿深后室,皮膚顏色和皮下淤血/血腫也可能影響讀數[14]。Westman 等[15]介紹了一種新型的經皮植入式無線肌肉內近紅外光譜設備直接測量肌肉氧飽和度,避免了傳統近紅外光譜設備的局限性,并具有無線連接、遠程監控、方便使用、成本更低等優點;研究結果表明,該設備檢測到肌肉氧飽和度隨著間隔壓力的升高和灌注壓的降低而下降,并在減壓后恢復,顯示出在監測 ACS 方面的潛力。
便攜式光纖肌肉內氧氣測量基于熒光猝滅原理,熒光強度與氧氣分壓成反比,可通過微控制器控制,智能手機直接讀取數據,實現實時監測肌肉內氧氣變化。Witthauer 等[16]在建立豬的模型實驗中分別使用針頭版和導管版研究,結果顯示,針頭版靈活性高,適合進行單點測量;導管版可長時間留置在組織中,能連續測量氧分壓趨勢,此外,可以通過在網格中空間布置額外的傳感器,或者沿著探針縱向布置,以獲取區域性組織氧分壓地圖,從而更好地了解氧分壓的分布。該傳感器能監測到生理范圍內的氧分壓變化(0~80 mm Hg),直接反映組織缺氧情況,實現了對生理氧分壓范圍內氧氣變化的快速、準確監測。目前該設備還處于實驗階段,旨在開發更高靈敏度的磷光分子,提高氧氣的擴散和檢測效率,從而消除磷光分子光漂白的影響,進一步提高傳感器的穩定性。
1.3 局部灌注監測
在 ACS 發生早期,組織灌注不足先于臨床癥狀出現,此時肌肉內壓增加,導致肌肉微循環血流顯著下降。超聲多普勒技術通過檢測動脈血流頻譜變化,觀察受壓區域動脈的情況,以識別是否存在舒張期逆流動脈血流(diastolic retrograde arterial flow, DRAF),來反映筋膜室內壓力的變化。研究發現,當脛骨前筋膜室的內壓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動脈血流可能沒有明顯變化,但靜脈回流會受到嚴重影響[17]。因此 Hou 等[18]認為當超聲檢查發現動脈出現 DRAF 和受影響肢體的呈鵝卵石樣外觀時,提示目標動脈受壓,是蛇咬傷致 ACS 的早期征象。此外,超聲波技術也被用于評估與壓力相關的筋膜間隔的幾何形狀和回聲性變化,以及評估筋膜間隔的彈性。位移脈沖相鎖定環路超聲波技術能夠檢測動脈脈沖的微小運動,隨著間隔壓力的升高,動脈脈沖的幅度和灌注會逐漸減小,從而反映出間隔內壓力的變化。但該技術在低血壓受試者中的靈敏度可能會明顯降低,且結果的準確性受操作者經驗、儀器設備等因素影響[19]。
光電容積脈搏波描記法是一種通過光探測器監測反射光的衰減程度的方法,用于評估血液流量變化。Shalabi 等[20]在早期 ACS 模擬中使用綠光反射式光電容積脈搏波傳感器發現,該傳感器能夠在壓力<20 mm Hg 期間檢測出血流的顯著減少。盡管光電容積脈搏波描記法技術在血液流動監測方面顯示出潛力,但該技術目前處于模擬實驗階段,且易受體位、膚色影響,在診斷 ACS 方面需進一步研究。
1.4 局部代謝分析
磷-31 磁共振波譜(31-phosphorus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31P-MRS)通過 9.4 T 的 MRI 儀得到 31P-MRS 譜圖,可以定量分析磷酸肌酸(phosphocreatine, PCr)、無機磷酸(inorganic phosphate, Pi)和腺苷三磷酸的濃度和變化。Ohta 等[21]對 6 只 ACS 模型大鼠進行了連續的 31P-MRS 掃描,結果顯示,缺血后 PCr/(Pi+PCr)比率顯著下降,而肌酸激酶水平沒有顯著變化,同時細胞內和動脈 pH 值也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此外,該研究還通過 1H-MR 圖像可以確定大鼠后肢間隙的水腫位置,T2 加權圖像在再灌注階段的相對信號強度升高表明細胞外空間水含量增加,與肌肉損傷和水腫癥狀一致。該實驗結果表明骨骼肌高能磷酸鹽代謝的改變發生在 ACS 病理生理學的早期階段,能比肌酸激酶更快、更靈敏地檢測到代謝變化。
Y?ld?r?m 等[22]在建立的 ACS 模型中使用自動測量方法(Rel Assay Diagnostics 試劑盒)和 Erel 比色法分別計算血清中的總氧化狀態(total oxidant status, TOS),在該實驗中,對照組大鼠不升高室壓,而實驗組通過注射鹽水將室壓升高至 30~40 mm Hg,并分別維持 45 min 和 90 min;結果顯示,在缺血的早期階段,總氧化狀態易受肢體肌肉缺血的影響,與對照組(TOS:41.8 μmol/L)相比,實驗組在缺血 45 min 時 TOS 值上升至 52.80 μmol/L,90 min 時高達 127.30 μmol/L,而此時尚未出現組織病理學改變。TOS 的這種在早期可逆缺血階段的檢測能力,使其成為 ACS 早期診斷的重要生物標志物。
2 手術治療
筋膜切開減壓是治療 ACS 的重要手段,但目前關于 ACS 筋膜切開減壓的時機存在不同意見。一些研究提出,當間隔內壓力達到 30~40 mm Hg(或 ΔP≤30 mm Hg)時,可以考慮進行筋膜切開減壓手術[2-3, 23]。而另一些研究則建議,間隔壓力達到 30 mm Hg 時,應持續監測壓力變化,當室間隔內壓力達到 50~55 mm Hg 時,進行手術減壓治療 ACS 最為有效,且并發癥較少[24]。在使用 ΔP 作為評估標準時,研究建議應將 ΔP<20 mm Hg 作為確定手術指征,<30 mm Hg 作為相對手術指征[25-26]。不同間隔具有不同的壓力閾值,且這些閾值可能受到個體差異、年齡和血壓等因素的影響[27]。因此,當 ΔP≤30 mm Hg 時,也應考慮筋膜切開手術,但這并不意味著必須進行手術,特別是在臨床檢查顯示改善的情況下。如果嚴格遵循這一閾值,可能會導致許多不必要的手術[3, 5, 10, 28]。
在蛇咬傷引起的 ACS 中,發病后的 8~12 h 被視為治療的“黃金期”。如果發病后 12 h 以上才進行筋膜切開術,患者的預后明顯較差,只有 8% 的患者達到正常功能,而早期進行筋膜切開術的患者中則有 68% 達到正常功能[24]。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過早進行筋膜切開雖然阻止了室間隔壓力的升高,但它增加了局部肌壞死和感染的風險,并且不能改善已惡化的肌肉損傷[29]。因此有學者認為治療 ACS 時,應通過增加抗蛇毒血清的用量并聯合使用甘露醇,同時密切監測患者的局部和全身反應至少 2 h,在壓力持續升高或癥狀不緩解的情況下再考慮使用筋膜切開減壓手術[30-31]。對行筋膜切開減壓的患者應聯合使用負壓吸引技術,以減少傷口閉合所需的時間和皮膚移植的需求[3]。此外,謝振興等[32]研究顯示,持續負壓吸引值為 –250 mm Hg 時效果最佳,創面的血流量最多,創面愈合速度最快,創面細菌數量最少。目前具備智能化負壓調節系統的新一代負壓封閉引流裝置,能夠實時監測并自動調整負壓值,以適應創面愈合的具體情況,從而提升治療的簡便性和效率。此外,新型生物醫用材料,例如納米銀和殼聚糖,不僅增強了負壓封閉引流的抗菌效果,還有助于促進傷口愈合。
值得注意的是,因骨筋膜室綜合征與蛇咬傷癥狀相似,曾被認為是蛇咬傷并發癥的普遍診斷標準,但這種診斷并不完全準確,特別是對于手和足等沒有筋膜室的部位。同時有研究提出,蛇咬傷引起的所謂“骨筋膜室綜合征”實際上與筋膜的限制性作用無關,而是蛇毒的直接作用導致了肌肉壞死,筋膜切開術在這種情況下應主要用于觀察病理變化,而不是作為主要治療手段[33]。因此在處理蛇咬傷引起的 ACS 時,應慎重評估患者的具體情況,不僅要考慮壓力閾值,還要結合患者的臨床癥狀和體征,作出綜合判斷,避免過度醫療,減少對患者可能造成的不可逆損傷。
3 保守治療
抗蛇毒血清作為蛇咬傷的首選治療藥物,應遵守早期、足量、同種專一、異種聯合的使用原則,使用至中毒癥狀消失[34]。聯合甘露醇、抬高患肢等多種措施能有效減輕患肢腫脹。然而,對于已經吸收的蛇毒則應使用血液灌流技術,通過吸附作用有效清除血液中的毒素,與抗蛇毒血清聯合使用,能發揮協同作用,提高治療效果[35]。此外,陳冰冰等[36]將持續緩慢低效血液透析串聯血液灌流療法聯合綜合護理模式應用于蝮蛇咬傷患者,明顯改善了肝腎功能,并有效清除了血液毒性物質。高壓氧輔助治療能預防再灌注損傷、減少組織水腫和逆轉亞致死性組織損傷[37-38]。彭清生等[39]使用藍光照射治療有效緩解患肢腫脹和疼痛癥狀,減輕全身炎癥反應。這些綜合治療方法的應用,能夠有效改善蛇咬傷患者的預后,提高治療效果,減輕患者的痛苦。
近年來,中醫藥在治療蛇咬傷上采用辨證施治原則,綜合運用內服和外敷中藥、針灸、拔罐、艾灸等多種方法進行內外兼治,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李國強等[40]通過針刺和刺血拔罐法為毒邪提供排出途徑,聯合季德勝蛇藥片外敷解毒,在減輕肢體腫脹、疼痛和改善血液酶學指標方面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任金平等[41]研究顯示,運用鄔氏清熱解毒方能夠明顯減輕患者肢體腫脹程度,縮短肢體腫脹消退時間,提高臨床療效。陳俊[42]運用 717 解毒合劑,有效減少了肢體腫脹、疼痛,并縮短了瘀斑消退及疾病治愈時間,為進一步研究中藥復方抗蛇傷的臨床實踐提供了新思路。這些研究表明,中醫藥在蛇咬傷治療中的獨特優勢,值得在臨床上推廣應用。
綜上,根據患者病情采用中西醫治療為主,血液灌流、高壓氧等多種方法為輔的治療方法,將大大提高治療效果,降低患者的致殘率和死亡率,改善整體預后。
4 展望
近年來,新技術和新方法的應用使得原本難以診斷的疾病變得更易識別,一些技術已經獲得臨床應用許可并顯示出良好效果。盡管部分技術仍處于實驗階段,但它們具有重大意義和廣闊應用前景。同時,我們需要深入研究蛇咬傷導致 ACS 的發病機制,并可能需要重新定義蛇咬傷引起的“骨筋膜室綜合征”,因為這可能代表一種新的綜合征。未來的研究應包括發病機制、診斷技術和治療方法,并以實時、無創和遠程醫療技術作為發展的關鍵方向。這不僅有助于提高診斷的準確性,也有助于開發更有效的治療策略,以改善患者的預后。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全球每年約有 540 萬起毒蛇咬傷事件,我國每年的毒蛇咬傷人數為 10 萬~30 萬,致殘率為 25%~30%,病死率達 5%[1]。急性筋膜間隙綜合征(acute compartment syndrome, ACS)是毒蛇咬傷的嚴重并發癥之一,雖然發病率很低,但其輕者可能導致功能障礙,重者可導致截肢甚至死亡。目前,蛇咬傷致 ACS 的診斷主要依賴于醫生對病史和癥狀的識別、臨床經驗以及壓力監測等輔助檢查手段。ACS 的臨床典型癥狀為“6P”表現,即疼痛增加(increasing pain)、無脈(pulselessness)、感覺異常(paresthesia)、麻痹(paralysis)、蒼白(pallor)和異常溫度(poikilothermia)。然而,疼痛作為主觀性癥狀,受意識、神經麻痹、合作程度等多種因素影響,甚至有一些罕見的病例可能缺乏明顯疼痛。其他癥狀則屬于長時間缺血缺氧導致的晚期神經和血管損傷的表現[2]。盡管這些典型癥狀具有一定的診斷意義,但缺乏特異性和敏感性,僅憑癥狀進行診斷是不可靠的,可能導致漏診和治療延誤。因此,ACS 的早期診斷、及時治療和外科手術干預至關重要,對患肢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綜合分析近年來關于該疾病輔助診斷及治療策略的研究進展,旨在為臨床實踐提供更為精準的指導。
1 臨床診斷方法
1.1 室間隔壓力測量
室間隔壓力測量是診斷 ACS 的重要輔助方法,對于有 ACS 風險的患者,均應持續監測組織壓力[3]。目前尚未確立一個權威的壓力數值作為 ACS 診斷標準,普遍認為,當間隔內壓力高于 30~4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壓力差 ΔP(舒張壓減去室筋膜壓)≤30 mm Hg 時,可以診斷 ACS。Whitesides 法、Matsen 的連續監測技術、Rorabeck 的側孔針和裂縫導管測量法等傳統測量方法通過針頭或導管插入筋膜室內直接測量筋膜內壓力值,此類技術使用方法簡單,容易操作,一度成為測量壓力的“金標準”[4]。然而,研究發現 ACS 在筋膜室內的壓力分布并不均勻,且壓力測量易受操作者技術和測量部位的影響[5]。呂林等[6]采用改良 Whiteside 法在超聲引導下行骨筋膜室穿刺測壓,利用超聲進行定位,以減少操作帶來的影響,且無不良預后事件發生。盡管技術不斷改進,傳統方法仍無法改變可能會引起過度治療、創傷大、不易連續監測等問題,因此不推薦這些有創操作[7]。
近年來,隨著高科技的快速發展,ACS 的壓力檢測技術也取得了顯著進步。MY01 為已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醫療器械,是一種基于微機電系統技術的高精度可植入壓力傳感器,通過穿刺放置在肌肉組織內部,便能以 0.1 mm Hg 的精確度測量腔室壓力,能跟蹤壓力變化,并將壓力數據實時上傳至云存儲數據庫和手機應用程序。據相關案例報道,當 MY01 顯示壓力急劇上升且臨床癥狀輕微時,及時對患者進行筋膜切開手術,均預后良好[8-9]。Merle 等[8]以小鼠腹部腔室綜合征模擬肢體 ACS,發現 MY01 設備在精確度上比快速壓力 Stryker 監測儀、Synthes 腔室壓力監測系統設備至少提高了 670%。該技術操作簡單,不受操作技術及患者體溫、位置變化影響,有望成為早期診斷 ACS 的重要方法。然而也有研究報告認為壓力監測缺乏診斷特異性,僅憑壓力測量診斷 ACS 的假陽性率較高,不可將其作為唯一診斷標準[10-11]。因此,未來深入探究該方法的可靠性至關重要。
1.2 局部氧合監測
組織氧合水平下降是 ACS 的早期表現,能夠直接反映組織缺氧程度,比筋膜室壓力測量更具特異性[12]。近紅外光譜利用近紅外光穿透組織,通過測量血紅蛋白和肌紅蛋白等血紅素化合物的氧合狀態來評估肌肉組織的氧合、血流以及血管功能情況[13]。近紅外光譜具有區分不同隔室的優勢,但使用時需同時對比對側肢體的相同分室,以控制個體差異和時間變化;同時組織穿透深度有限,不能穿透小腿深后室,皮膚顏色和皮下淤血/血腫也可能影響讀數[14]。Westman 等[15]介紹了一種新型的經皮植入式無線肌肉內近紅外光譜設備直接測量肌肉氧飽和度,避免了傳統近紅外光譜設備的局限性,并具有無線連接、遠程監控、方便使用、成本更低等優點;研究結果表明,該設備檢測到肌肉氧飽和度隨著間隔壓力的升高和灌注壓的降低而下降,并在減壓后恢復,顯示出在監測 ACS 方面的潛力。
便攜式光纖肌肉內氧氣測量基于熒光猝滅原理,熒光強度與氧氣分壓成反比,可通過微控制器控制,智能手機直接讀取數據,實現實時監測肌肉內氧氣變化。Witthauer 等[16]在建立豬的模型實驗中分別使用針頭版和導管版研究,結果顯示,針頭版靈活性高,適合進行單點測量;導管版可長時間留置在組織中,能連續測量氧分壓趨勢,此外,可以通過在網格中空間布置額外的傳感器,或者沿著探針縱向布置,以獲取區域性組織氧分壓地圖,從而更好地了解氧分壓的分布。該傳感器能監測到生理范圍內的氧分壓變化(0~80 mm Hg),直接反映組織缺氧情況,實現了對生理氧分壓范圍內氧氣變化的快速、準確監測。目前該設備還處于實驗階段,旨在開發更高靈敏度的磷光分子,提高氧氣的擴散和檢測效率,從而消除磷光分子光漂白的影響,進一步提高傳感器的穩定性。
1.3 局部灌注監測
在 ACS 發生早期,組織灌注不足先于臨床癥狀出現,此時肌肉內壓增加,導致肌肉微循環血流顯著下降。超聲多普勒技術通過檢測動脈血流頻譜變化,觀察受壓區域動脈的情況,以識別是否存在舒張期逆流動脈血流(diastolic retrograde arterial flow, DRAF),來反映筋膜室內壓力的變化。研究發現,當脛骨前筋膜室的內壓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動脈血流可能沒有明顯變化,但靜脈回流會受到嚴重影響[17]。因此 Hou 等[18]認為當超聲檢查發現動脈出現 DRAF 和受影響肢體的呈鵝卵石樣外觀時,提示目標動脈受壓,是蛇咬傷致 ACS 的早期征象。此外,超聲波技術也被用于評估與壓力相關的筋膜間隔的幾何形狀和回聲性變化,以及評估筋膜間隔的彈性。位移脈沖相鎖定環路超聲波技術能夠檢測動脈脈沖的微小運動,隨著間隔壓力的升高,動脈脈沖的幅度和灌注會逐漸減小,從而反映出間隔內壓力的變化。但該技術在低血壓受試者中的靈敏度可能會明顯降低,且結果的準確性受操作者經驗、儀器設備等因素影響[19]。
光電容積脈搏波描記法是一種通過光探測器監測反射光的衰減程度的方法,用于評估血液流量變化。Shalabi 等[20]在早期 ACS 模擬中使用綠光反射式光電容積脈搏波傳感器發現,該傳感器能夠在壓力<20 mm Hg 期間檢測出血流的顯著減少。盡管光電容積脈搏波描記法技術在血液流動監測方面顯示出潛力,但該技術目前處于模擬實驗階段,且易受體位、膚色影響,在診斷 ACS 方面需進一步研究。
1.4 局部代謝分析
磷-31 磁共振波譜(31-phosphorus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31P-MRS)通過 9.4 T 的 MRI 儀得到 31P-MRS 譜圖,可以定量分析磷酸肌酸(phosphocreatine, PCr)、無機磷酸(inorganic phosphate, Pi)和腺苷三磷酸的濃度和變化。Ohta 等[21]對 6 只 ACS 模型大鼠進行了連續的 31P-MRS 掃描,結果顯示,缺血后 PCr/(Pi+PCr)比率顯著下降,而肌酸激酶水平沒有顯著變化,同時細胞內和動脈 pH 值也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此外,該研究還通過 1H-MR 圖像可以確定大鼠后肢間隙的水腫位置,T2 加權圖像在再灌注階段的相對信號強度升高表明細胞外空間水含量增加,與肌肉損傷和水腫癥狀一致。該實驗結果表明骨骼肌高能磷酸鹽代謝的改變發生在 ACS 病理生理學的早期階段,能比肌酸激酶更快、更靈敏地檢測到代謝變化。
Y?ld?r?m 等[22]在建立的 ACS 模型中使用自動測量方法(Rel Assay Diagnostics 試劑盒)和 Erel 比色法分別計算血清中的總氧化狀態(total oxidant status, TOS),在該實驗中,對照組大鼠不升高室壓,而實驗組通過注射鹽水將室壓升高至 30~40 mm Hg,并分別維持 45 min 和 90 min;結果顯示,在缺血的早期階段,總氧化狀態易受肢體肌肉缺血的影響,與對照組(TOS:41.8 μmol/L)相比,實驗組在缺血 45 min 時 TOS 值上升至 52.80 μmol/L,90 min 時高達 127.30 μmol/L,而此時尚未出現組織病理學改變。TOS 的這種在早期可逆缺血階段的檢測能力,使其成為 ACS 早期診斷的重要生物標志物。
2 手術治療
筋膜切開減壓是治療 ACS 的重要手段,但目前關于 ACS 筋膜切開減壓的時機存在不同意見。一些研究提出,當間隔內壓力達到 30~40 mm Hg(或 ΔP≤30 mm Hg)時,可以考慮進行筋膜切開減壓手術[2-3, 23]。而另一些研究則建議,間隔壓力達到 30 mm Hg 時,應持續監測壓力變化,當室間隔內壓力達到 50~55 mm Hg 時,進行手術減壓治療 ACS 最為有效,且并發癥較少[24]。在使用 ΔP 作為評估標準時,研究建議應將 ΔP<20 mm Hg 作為確定手術指征,<30 mm Hg 作為相對手術指征[25-26]。不同間隔具有不同的壓力閾值,且這些閾值可能受到個體差異、年齡和血壓等因素的影響[27]。因此,當 ΔP≤30 mm Hg 時,也應考慮筋膜切開手術,但這并不意味著必須進行手術,特別是在臨床檢查顯示改善的情況下。如果嚴格遵循這一閾值,可能會導致許多不必要的手術[3, 5, 10, 28]。
在蛇咬傷引起的 ACS 中,發病后的 8~12 h 被視為治療的“黃金期”。如果發病后 12 h 以上才進行筋膜切開術,患者的預后明顯較差,只有 8% 的患者達到正常功能,而早期進行筋膜切開術的患者中則有 68% 達到正常功能[24]。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過早進行筋膜切開雖然阻止了室間隔壓力的升高,但它增加了局部肌壞死和感染的風險,并且不能改善已惡化的肌肉損傷[29]。因此有學者認為治療 ACS 時,應通過增加抗蛇毒血清的用量并聯合使用甘露醇,同時密切監測患者的局部和全身反應至少 2 h,在壓力持續升高或癥狀不緩解的情況下再考慮使用筋膜切開減壓手術[30-31]。對行筋膜切開減壓的患者應聯合使用負壓吸引技術,以減少傷口閉合所需的時間和皮膚移植的需求[3]。此外,謝振興等[32]研究顯示,持續負壓吸引值為 –250 mm Hg 時效果最佳,創面的血流量最多,創面愈合速度最快,創面細菌數量最少。目前具備智能化負壓調節系統的新一代負壓封閉引流裝置,能夠實時監測并自動調整負壓值,以適應創面愈合的具體情況,從而提升治療的簡便性和效率。此外,新型生物醫用材料,例如納米銀和殼聚糖,不僅增強了負壓封閉引流的抗菌效果,還有助于促進傷口愈合。
值得注意的是,因骨筋膜室綜合征與蛇咬傷癥狀相似,曾被認為是蛇咬傷并發癥的普遍診斷標準,但這種診斷并不完全準確,特別是對于手和足等沒有筋膜室的部位。同時有研究提出,蛇咬傷引起的所謂“骨筋膜室綜合征”實際上與筋膜的限制性作用無關,而是蛇毒的直接作用導致了肌肉壞死,筋膜切開術在這種情況下應主要用于觀察病理變化,而不是作為主要治療手段[33]。因此在處理蛇咬傷引起的 ACS 時,應慎重評估患者的具體情況,不僅要考慮壓力閾值,還要結合患者的臨床癥狀和體征,作出綜合判斷,避免過度醫療,減少對患者可能造成的不可逆損傷。
3 保守治療
抗蛇毒血清作為蛇咬傷的首選治療藥物,應遵守早期、足量、同種專一、異種聯合的使用原則,使用至中毒癥狀消失[34]。聯合甘露醇、抬高患肢等多種措施能有效減輕患肢腫脹。然而,對于已經吸收的蛇毒則應使用血液灌流技術,通過吸附作用有效清除血液中的毒素,與抗蛇毒血清聯合使用,能發揮協同作用,提高治療效果[35]。此外,陳冰冰等[36]將持續緩慢低效血液透析串聯血液灌流療法聯合綜合護理模式應用于蝮蛇咬傷患者,明顯改善了肝腎功能,并有效清除了血液毒性物質。高壓氧輔助治療能預防再灌注損傷、減少組織水腫和逆轉亞致死性組織損傷[37-38]。彭清生等[39]使用藍光照射治療有效緩解患肢腫脹和疼痛癥狀,減輕全身炎癥反應。這些綜合治療方法的應用,能夠有效改善蛇咬傷患者的預后,提高治療效果,減輕患者的痛苦。
近年來,中醫藥在治療蛇咬傷上采用辨證施治原則,綜合運用內服和外敷中藥、針灸、拔罐、艾灸等多種方法進行內外兼治,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李國強等[40]通過針刺和刺血拔罐法為毒邪提供排出途徑,聯合季德勝蛇藥片外敷解毒,在減輕肢體腫脹、疼痛和改善血液酶學指標方面具有較好的臨床療效。任金平等[41]研究顯示,運用鄔氏清熱解毒方能夠明顯減輕患者肢體腫脹程度,縮短肢體腫脹消退時間,提高臨床療效。陳俊[42]運用 717 解毒合劑,有效減少了肢體腫脹、疼痛,并縮短了瘀斑消退及疾病治愈時間,為進一步研究中藥復方抗蛇傷的臨床實踐提供了新思路。這些研究表明,中醫藥在蛇咬傷治療中的獨特優勢,值得在臨床上推廣應用。
綜上,根據患者病情采用中西醫治療為主,血液灌流、高壓氧等多種方法為輔的治療方法,將大大提高治療效果,降低患者的致殘率和死亡率,改善整體預后。
4 展望
近年來,新技術和新方法的應用使得原本難以診斷的疾病變得更易識別,一些技術已經獲得臨床應用許可并顯示出良好效果。盡管部分技術仍處于實驗階段,但它們具有重大意義和廣闊應用前景。同時,我們需要深入研究蛇咬傷導致 ACS 的發病機制,并可能需要重新定義蛇咬傷引起的“骨筋膜室綜合征”,因為這可能代表一種新的綜合征。未來的研究應包括發病機制、診斷技術和治療方法,并以實時、無創和遠程醫療技術作為發展的關鍵方向。這不僅有助于提高診斷的準確性,也有助于開發更有效的治療策略,以改善患者的預后。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