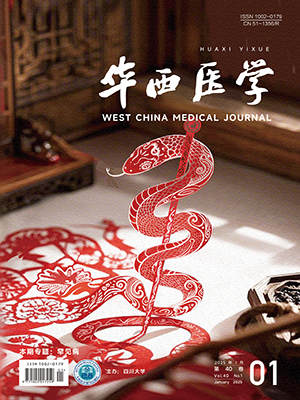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是由于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積累而導致動脈硬化和收縮功能障礙的一種疾病。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 9 能夠使血漿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升高,這一過程加速了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該文擬對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 9 的生物學特性和功能機制進行綜述,闡明其對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的影響,為此類疾病的診治和改善患者預后提供研究文獻支持。
引用本文: 周楊楊, 魏薇. 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 9 在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華西醫學, 2024, 39(11): 1792-1796. doi: 10.7507/1002-0179.202409217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華西醫學》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是一大類以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 AS)為病理基礎的疾病總稱,包括冠狀動脈 AS、腦 AS、頸 AS以及外周 AS 等[1]。基于 ASCVD 基礎上發生的心腦血管急危重癥是我國城鄉居民的重要死亡原因,占死因構成的 40%以上[2]。AS 是一種由于脂質沉積引起的慢性炎癥性血管病變。在病變形成早期,內皮細胞激活并表達黏附分子,引起中性粒細胞滲出。進入內皮細胞下層的單核細胞吞噬脂質,形成泡沫細胞啟動 AS 病變。積聚的低密度脂蛋白促進 AS 炎癥細胞(主要是 T 細胞和巨噬細胞)浸潤病變并參與斑塊的進展和血栓形成,進而導致 ASCVD[3]。
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 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是由人類 1 號染色體上的 PCSK9 基因編碼的一種酶[4]。它是前蛋白轉化酶家族中的第 9 個成員,在內質網中進行加工[5],并在肝臟、腸道、腎臟、皮膚和中樞神經系統中表達[6]。影響 PCSK9 分泌的具體機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其中分揀蛋白、雌激素及許多種類的轉錄因子(如固醇反應元件結合蛋白、過氧化物酶體增殖激活受體、肝臟 X 受體、組蛋白核因子 P)等[7-8]參與其調控。PCSK9 血漿濃度升高是 ASCVD 發生發展的因素之一。PCSK9 可以改變血漿脂質水平,增加血小板活化,促進炎癥反應,影響凝血系統,從而引起AS。這一過程可能導致包括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 MI)在內的晚期心血管事件的發生。因此,本綜述旨在總結 PCSK9 促進 ASCVD 發生發展的多種機制及途徑,進而為后續診治和改善患者預后提供參考。
1 PCSK9 的血脂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ASCVD 是由于動脈壁中富含脂質的AS斑塊的積累而導致動脈硬化和收縮功能障礙的一種疾病。AS 主要是由高膽固醇血癥引起。當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在動脈內膜中積聚并激活內皮時,AS過程開始啟動。隨后單核細胞和 T 細胞募集,白細胞黏附分子和趨化因子促進這一過程[9-10]。血漿 LDL-C 水平與 ASCVD 風險增加密切相關[11]。下調 LDL-C 濃度有助于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12]。PCSK9 的功能獲得性突變會導致高脂血癥和 ASVCD 的風險增加,而 PCSK9 的功能喪失性突變會降低血漿 LDL-C 水平和 ASVCD 的風險[13]。
1.1 PCSK9 對 LDL-C 的調節作用
在生理條件下,血漿 LDL-C 與肝細胞表面的低密度脂蛋白受體(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LDL-R)結合形成 LDL-C-LDL-R 二聚體,然后轉移到細胞內[14]。LDL-C 隨后與 LDL-R 分離,并在溶酶體中降解[15]。細胞內游離的 LDL-R 到達細胞表面,參與新一輪的 LDL-C 轉運和降解[15]。PCSK9 主要功能是與 LDL-R 結合。PCSK9 與 LDL-R 結合形成復合物,隨后在溶酶體內體降解,抑制了 LDL-R 的循環再利用,導致血漿 LDL-C 濃度增加。
1.2 PCSK9 對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的調節作用
PCSK9 不僅調節 LDL-C 水平,還能調節其他脂質代謝(如 TG、脂蛋白等)。PCSK9 與富含 TG 的脂蛋白代謝間存在聯系的首要表現是血漿 PCSK9 水平與血漿 TG 水平呈正相關[16]。這一現象不僅存在于普通健康人群,在某些特定疾病狀態下,研究者也發現血漿 PCSK9 水平與 TG 水平呈正相關。患有蛋白尿的慢性腎臟病 2 期和 3 期患者[17],以及接受血液透析的慢性腎臟病 5 期患者[18],PCSK9 水平與 TG 水平均呈正相關[17]。攜帶與高膽固醇血癥相關的 PCSK9 突變人群的 TG 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但仍在參考范圍內)[19],這表明 PCSK9 可能會影響富含 TG 的脂蛋白代謝。關于 PCSK9 與 TG 間的相互調節作用機制,目前尚未得出確切統一的模型。
1.3 PCSK9 對載脂蛋白 B(apolipoprotein B, ApoB)的調節作用
各種細胞和動物模型研究已證明,PCSK9 與肝臟中 ApoB 分泌之間存在聯系。過度表達 GOFD374Y-PCSK9 突變體的大鼠肝癌細胞(McArdle-7777)表現出含 ApoB 的脂蛋白分泌增加[20]。同樣,轉基因載體過度表達 PCSK9 的小鼠血漿中,ApoB-100 和 ApoB-48 以及 TG 的水平較高,并且這種影響與 LDL-R 無關[21]。一些關于 PCSK9 對 ApoB 作用的人體研究也已逐步開展。穩定同位素動力學研究表明,攜帶 PCSK9GOFS127R 突變的患者會過量產生 ApoB-100(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3 倍),同時期過量產生極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3 倍)、中間密度低蛋白水平(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3 倍)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5 倍)均增高[22]。此外,在一項研究了近 6 000 例中年受試者樣本的研究中[23],發現血清 PCSK9 與 ApoB 之間存在相關性。
2 PCSK9 對血小板活化和血栓形成的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血小板活化和血栓是 ASCVD 的重要誘發因素,而血小板活化涉及極其復雜的病理生理機制。CD36,又稱為血小板反應蛋白受體,是一種高度糖基化的單鏈跨膜蛋白,在血小板、內皮細胞、脂肪細胞、肌細胞、單核吞噬細胞、肝細胞和一些上皮細胞均有表達[24]。PCSK9 通過與血小板表面的 CD36 相互作用,激活酪氨酸激酶、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 5 和 c-JunN 端激酶。這一過程會導致活性氧的產生增加,并激活 p38 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胞質磷脂酶 A2/環加氧酶 1/血栓素胺 A2,促進血小板聚集、活化、擴散和血栓形成[25]。在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癥患者中,研究人員發現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ox-LDL)通過激活 CD36、血凝素樣氧化LDL-R1 和 NADPH 氧化酶 2 誘導血小板活化[24]。PCSK9 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正向調制的作用[26]。在病理條件下,如高脂血癥、高血糖、AS 等,LDL-C 水平升高與血小板活化增強和血栓素的產生有關[27]。許多因素參與了這一過程的調控,目前尚未完全明細所有調控機制。
研究發現,冠心病患者血小板活化后釋放的分揀蛋白能夠促進 PCSK9 的分泌[28]。在動物MI模型中,研究者觀察到急性MI時血漿 PCSK9濃度較正常水平短暫性升高[29]。在一項關于PCSK9 抑制劑對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癥患者血小板功能的影響的研究中,發現患者使用 PCSK9 抑制劑 2~12 個月后,血小板活化和聚集減少[30]。在一項關于誘導小鼠頸動脈損傷來評估 PCSK9對動脈血栓形成的影響的實驗中,其結果發現PCSK9-/- 小鼠頸動脈血栓比 PCSK9+/+ 小鼠形成減少,且多為不穩定的非阻塞性血栓[31]。上述研究結果表明,PCSK9 可能通過增強血小板的活化和聚集,參與血栓形成。血小板活化后分泌的分揀蛋白又能夠促進PCSK9的分泌,這種相互促進效應的惡性循環可能促進了心血管事件的發生和發展。
3 PCSK9 對炎癥反應的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炎癥反應在 AS 的開始和進展直至斑塊破裂和侵蝕過程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直至發生 ASCVD。一些研究已經明確了 PCSK9 與炎癥之間存在聯系[32-36]。這些研究評估了 PCSK9 與一些關鍵炎癥標志物的關聯,如白細胞、纖維蛋白原和超敏 C 反應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等。白細胞計數是傳統的炎癥標志物。在不同基線風險水平的人群中,包括無癥狀和有癥狀的冠狀動脈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患者,它已被證明與早期和晚期 AS 相關。在一項針對中國 CAD 患者的單中心研究中,血漿 PCSK9 水平與白細胞計數亞群、淋巴細胞計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在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中呈獨立正相關[32]。但其相關的分子機制尚不清楚。
纖維蛋白原是一種由肝臟合成的凝血糖蛋白,也是一類重要的炎癥標志物,在炎癥狀態下會明顯增高。纖維蛋白原通過刺激斑塊生長和/或誘導白細胞和血小板黏附到血管壁,加速 AS 和臨床 CAD 的進展。此外,血漿纖維蛋白原水平升高還與 CAD 發病率、AS 嚴重程度和 CAD 死亡率增加有關。一項針對經血管造影證實的穩定型 CAD 患者的橫斷面研究表明,循環 PCSK9 水平與纖維蛋白原水平呈正相關,且這種關聯在機制上獨立于一些潛在的混雜因素(如血脂指數和 hs-CRP)[33]。因此,PCSK 9 和纖維蛋白原之間的相互作用被認為是 AS 進展的潛在機制之一。
hs-CRP 是一種急性期炎癥介質,被認為是全身性炎癥的敏感但非特異性生物標志物。hs-CRP 可以增加巨噬細胞對低密度脂蛋白的攝取,導致 AS 發展過程中泡沫細胞的形成。因此,它被認為是 AS 的危險標志和危險因素。在穩定型 CAD 患者中,PCSK9 水平與 hs-CRP 水平呈正相關[34]。在 FOURIER 試驗中,27 564 例穩定型 ASCVD 且 LDL-C≥70 mg/dL 的患者被隨機分配到伊洛尤單抗組(PCSK9 抑制劑)和安慰劑組。然后根據基線 hs-CRP(<1、1~3 和>3 mg/dL)的水平將兩者分為 3 個亞組[35]。hs-CRP 較高的患者發生主要終點事件和關鍵次要終點事件的風險更高,炎癥可能是 ASCVD 的獨立危險因素[36],且在 hs-CRP 較高的患者中,伊洛尤單抗組絕對風險的降低比安慰劑組更顯著。因此,伊洛尤單抗對 ASCVD 患者的保護作用,至少部分依賴于其抗炎功能。這些發現表明,PCSK9 水平與 ASCVD 期間的炎癥反應存在相關性,抑制 PCSK9 水平,也減輕對炎癥反應水平,降低 CAD 的發病率和嚴重程度。
4 PCSK9 對細胞凋亡、自噬和焦亡的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PCSK9 與細胞凋亡有關。在 AS 的發展過程中,ox-LDL 是引起內皮細胞功能障礙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內皮細胞凋亡的主要促進因子。ox-LDL 通過上調凋亡相關因子 Bcl2-associated X(Bax)、caspase- 3、caspase -9 以及下調抗凋亡因子 Bcl2 發揮作用[37]。在針對 ox-LDL 誘導人臍靜脈內皮細胞凋亡的研究發現,PCSK9 是其中的關鍵介質;ox-LDL 促凋亡功能主要依賴于 PCSK9 表達的上調及其下游 MAPK 信號通路的激活,尤其是 c-JunN 端激酶(JNK)和 p38 的磷酸化上調的 PCSK9 促進 AS 病變中內皮細胞的凋亡;用 shRNA-PCSK9 靶向敲除 PCSK9,可抑制 ox-LDL 誘導的 p38 和 JNK 磷酸化,下調 Bax 與 Bcl2 的比例,從而抑制內皮細胞的凋亡[38]。
此外,PCSK9 與自噬和焦亡有關[39]。自噬能夠清除受損的線粒體,這對維持細胞存活和正常功能有很大的作用[40]。從自噬中逃逸的線粒體 DNA 可導致炎癥和心力衰竭的發生[41]。當使用 3-甲基腺嘌呤抑制自噬時,PCSK9 在細胞質中積累,提示其可能與自噬有關。炎癥條件下,PCSK9 升高破壞線粒體 DNA,促進平滑肌細胞中線粒體活性氧的形成,進而促進 PCSK9 和血凝素樣氧化LDL-R1 的上調[42]。與野生小鼠相比,當進行 PCSK9 敲除或使用 PCSK9 抑制劑 Pep2-8 治療的小鼠發生 MI 時,梗死面積更小,自噬減少[39]。在慢性心肌缺血過程中,上調的 PCSK9 誘導線粒體 DNA 損傷,激活 NLRP3 炎性小體信號傳導,促進 caspase 1 依賴性焦亡[43]。在 PCSK9 基因敲除小鼠中,缺血心臟中 NLRP3 的激活和氮端 Gasdermin D 的上調被抑制[42]。因此,PCSK9 能夠抑制自噬,但促進細胞凋亡和焦亡,這對 ASCVD 的預后會產生不利影響。
5 小結
PCSK9 通過包括調節脂質代謝、促進炎癥反應、促進血小板活化、促進血栓形成、促進細胞凋亡、促進焦亡、抑制自噬等在內的多種機制影響 ASCVD 的發生和發展。隨著對 ASCVD 患者的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研究結果發現 PCSK9 已成為他汀類藥物不耐受或最大劑量他汀類藥物治療后未能達到血脂目標的 ASCVD 患者新的治療靶點。但對于 PCSK9 在 ASCVD 的作用機制和路徑尚未完全明晰,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更加精準改善 ASCVD 患者的預后。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CVD)是一大類以動脈粥樣硬化(atherosclerosis, AS)為病理基礎的疾病總稱,包括冠狀動脈 AS、腦 AS、頸 AS以及外周 AS 等[1]。基于 ASCVD 基礎上發生的心腦血管急危重癥是我國城鄉居民的重要死亡原因,占死因構成的 40%以上[2]。AS 是一種由于脂質沉積引起的慢性炎癥性血管病變。在病變形成早期,內皮細胞激活并表達黏附分子,引起中性粒細胞滲出。進入內皮細胞下層的單核細胞吞噬脂質,形成泡沫細胞啟動 AS 病變。積聚的低密度脂蛋白促進 AS 炎癥細胞(主要是 T 細胞和巨噬細胞)浸潤病變并參與斑塊的進展和血栓形成,進而導致 ASCVD[3]。
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 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是由人類 1 號染色體上的 PCSK9 基因編碼的一種酶[4]。它是前蛋白轉化酶家族中的第 9 個成員,在內質網中進行加工[5],并在肝臟、腸道、腎臟、皮膚和中樞神經系統中表達[6]。影響 PCSK9 分泌的具體機制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其中分揀蛋白、雌激素及許多種類的轉錄因子(如固醇反應元件結合蛋白、過氧化物酶體增殖激活受體、肝臟 X 受體、組蛋白核因子 P)等[7-8]參與其調控。PCSK9 血漿濃度升高是 ASCVD 發生發展的因素之一。PCSK9 可以改變血漿脂質水平,增加血小板活化,促進炎癥反應,影響凝血系統,從而引起AS。這一過程可能導致包括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 MI)在內的晚期心血管事件的發生。因此,本綜述旨在總結 PCSK9 促進 ASCVD 發生發展的多種機制及途徑,進而為后續診治和改善患者預后提供參考。
1 PCSK9 的血脂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ASCVD 是由于動脈壁中富含脂質的AS斑塊的積累而導致動脈硬化和收縮功能障礙的一種疾病。AS 主要是由高膽固醇血癥引起。當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在動脈內膜中積聚并激活內皮時,AS過程開始啟動。隨后單核細胞和 T 細胞募集,白細胞黏附分子和趨化因子促進這一過程[9-10]。血漿 LDL-C 水平與 ASCVD 風險增加密切相關[11]。下調 LDL-C 濃度有助于降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12]。PCSK9 的功能獲得性突變會導致高脂血癥和 ASVCD 的風險增加,而 PCSK9 的功能喪失性突變會降低血漿 LDL-C 水平和 ASVCD 的風險[13]。
1.1 PCSK9 對 LDL-C 的調節作用
在生理條件下,血漿 LDL-C 與肝細胞表面的低密度脂蛋白受體(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LDL-R)結合形成 LDL-C-LDL-R 二聚體,然后轉移到細胞內[14]。LDL-C 隨后與 LDL-R 分離,并在溶酶體中降解[15]。細胞內游離的 LDL-R 到達細胞表面,參與新一輪的 LDL-C 轉運和降解[15]。PCSK9 主要功能是與 LDL-R 結合。PCSK9 與 LDL-R 結合形成復合物,隨后在溶酶體內體降解,抑制了 LDL-R 的循環再利用,導致血漿 LDL-C 濃度增加。
1.2 PCSK9 對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的調節作用
PCSK9 不僅調節 LDL-C 水平,還能調節其他脂質代謝(如 TG、脂蛋白等)。PCSK9 與富含 TG 的脂蛋白代謝間存在聯系的首要表現是血漿 PCSK9 水平與血漿 TG 水平呈正相關[16]。這一現象不僅存在于普通健康人群,在某些特定疾病狀態下,研究者也發現血漿 PCSK9 水平與 TG 水平呈正相關。患有蛋白尿的慢性腎臟病 2 期和 3 期患者[17],以及接受血液透析的慢性腎臟病 5 期患者[18],PCSK9 水平與 TG 水平均呈正相關[17]。攜帶與高膽固醇血癥相關的 PCSK9 突變人群的 TG 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但仍在參考范圍內)[19],這表明 PCSK9 可能會影響富含 TG 的脂蛋白代謝。關于 PCSK9 與 TG 間的相互調節作用機制,目前尚未得出確切統一的模型。
1.3 PCSK9 對載脂蛋白 B(apolipoprotein B, ApoB)的調節作用
各種細胞和動物模型研究已證明,PCSK9 與肝臟中 ApoB 分泌之間存在聯系。過度表達 GOFD374Y-PCSK9 突變體的大鼠肝癌細胞(McArdle-7777)表現出含 ApoB 的脂蛋白分泌增加[20]。同樣,轉基因載體過度表達 PCSK9 的小鼠血漿中,ApoB-100 和 ApoB-48 以及 TG 的水平較高,并且這種影響與 LDL-R 無關[21]。一些關于 PCSK9 對 ApoB 作用的人體研究也已逐步開展。穩定同位素動力學研究表明,攜帶 PCSK9GOFS127R 突變的患者會過量產生 ApoB-100(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3 倍),同時期過量產生極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3 倍)、中間密度低蛋白水平(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3 倍)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約為普通健康人群的 5 倍)均增高[22]。此外,在一項研究了近 6 000 例中年受試者樣本的研究中[23],發現血清 PCSK9 與 ApoB 之間存在相關性。
2 PCSK9 對血小板活化和血栓形成的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血小板活化和血栓是 ASCVD 的重要誘發因素,而血小板活化涉及極其復雜的病理生理機制。CD36,又稱為血小板反應蛋白受體,是一種高度糖基化的單鏈跨膜蛋白,在血小板、內皮細胞、脂肪細胞、肌細胞、單核吞噬細胞、肝細胞和一些上皮細胞均有表達[24]。PCSK9 通過與血小板表面的 CD36 相互作用,激活酪氨酸激酶、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 5 和 c-JunN 端激酶。這一過程會導致活性氧的產生增加,并激活 p38 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胞質磷脂酶 A2/環加氧酶 1/血栓素胺 A2,促進血小板聚集、活化、擴散和血栓形成[25]。在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癥患者中,研究人員發現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ox-LDL)通過激活 CD36、血凝素樣氧化LDL-R1 和 NADPH 氧化酶 2 誘導血小板活化[24]。PCSK9 在這個過程中起到正向調制的作用[26]。在病理條件下,如高脂血癥、高血糖、AS 等,LDL-C 水平升高與血小板活化增強和血栓素的產生有關[27]。許多因素參與了這一過程的調控,目前尚未完全明細所有調控機制。
研究發現,冠心病患者血小板活化后釋放的分揀蛋白能夠促進 PCSK9 的分泌[28]。在動物MI模型中,研究者觀察到急性MI時血漿 PCSK9濃度較正常水平短暫性升高[29]。在一項關于PCSK9 抑制劑對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癥患者血小板功能的影響的研究中,發現患者使用 PCSK9 抑制劑 2~12 個月后,血小板活化和聚集減少[30]。在一項關于誘導小鼠頸動脈損傷來評估 PCSK9對動脈血栓形成的影響的實驗中,其結果發現PCSK9-/- 小鼠頸動脈血栓比 PCSK9+/+ 小鼠形成減少,且多為不穩定的非阻塞性血栓[31]。上述研究結果表明,PCSK9 可能通過增強血小板的活化和聚集,參與血栓形成。血小板活化后分泌的分揀蛋白又能夠促進PCSK9的分泌,這種相互促進效應的惡性循環可能促進了心血管事件的發生和發展。
3 PCSK9 對炎癥反應的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炎癥反應在 AS 的開始和進展直至斑塊破裂和侵蝕過程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直至發生 ASCVD。一些研究已經明確了 PCSK9 與炎癥之間存在聯系[32-36]。這些研究評估了 PCSK9 與一些關鍵炎癥標志物的關聯,如白細胞、纖維蛋白原和超敏 C 反應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等。白細胞計數是傳統的炎癥標志物。在不同基線風險水平的人群中,包括無癥狀和有癥狀的冠狀動脈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患者,它已被證明與早期和晚期 AS 相關。在一項針對中國 CAD 患者的單中心研究中,血漿 PCSK9 水平與白細胞計數亞群、淋巴細胞計數和中性粒細胞計數在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中呈獨立正相關[32]。但其相關的分子機制尚不清楚。
纖維蛋白原是一種由肝臟合成的凝血糖蛋白,也是一類重要的炎癥標志物,在炎癥狀態下會明顯增高。纖維蛋白原通過刺激斑塊生長和/或誘導白細胞和血小板黏附到血管壁,加速 AS 和臨床 CAD 的進展。此外,血漿纖維蛋白原水平升高還與 CAD 發病率、AS 嚴重程度和 CAD 死亡率增加有關。一項針對經血管造影證實的穩定型 CAD 患者的橫斷面研究表明,循環 PCSK9 水平與纖維蛋白原水平呈正相關,且這種關聯在機制上獨立于一些潛在的混雜因素(如血脂指數和 hs-CRP)[33]。因此,PCSK 9 和纖維蛋白原之間的相互作用被認為是 AS 進展的潛在機制之一。
hs-CRP 是一種急性期炎癥介質,被認為是全身性炎癥的敏感但非特異性生物標志物。hs-CRP 可以增加巨噬細胞對低密度脂蛋白的攝取,導致 AS 發展過程中泡沫細胞的形成。因此,它被認為是 AS 的危險標志和危險因素。在穩定型 CAD 患者中,PCSK9 水平與 hs-CRP 水平呈正相關[34]。在 FOURIER 試驗中,27 564 例穩定型 ASCVD 且 LDL-C≥70 mg/dL 的患者被隨機分配到伊洛尤單抗組(PCSK9 抑制劑)和安慰劑組。然后根據基線 hs-CRP(<1、1~3 和>3 mg/dL)的水平將兩者分為 3 個亞組[35]。hs-CRP 較高的患者發生主要終點事件和關鍵次要終點事件的風險更高,炎癥可能是 ASCVD 的獨立危險因素[36],且在 hs-CRP 較高的患者中,伊洛尤單抗組絕對風險的降低比安慰劑組更顯著。因此,伊洛尤單抗對 ASCVD 患者的保護作用,至少部分依賴于其抗炎功能。這些發現表明,PCSK9 水平與 ASCVD 期間的炎癥反應存在相關性,抑制 PCSK9 水平,也減輕對炎癥反應水平,降低 CAD 的發病率和嚴重程度。
4 PCSK9 對細胞凋亡、自噬和焦亡的調節作用對 ASCVD 的影響
PCSK9 與細胞凋亡有關。在 AS 的發展過程中,ox-LDL 是引起內皮細胞功能障礙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內皮細胞凋亡的主要促進因子。ox-LDL 通過上調凋亡相關因子 Bcl2-associated X(Bax)、caspase- 3、caspase -9 以及下調抗凋亡因子 Bcl2 發揮作用[37]。在針對 ox-LDL 誘導人臍靜脈內皮細胞凋亡的研究發現,PCSK9 是其中的關鍵介質;ox-LDL 促凋亡功能主要依賴于 PCSK9 表達的上調及其下游 MAPK 信號通路的激活,尤其是 c-JunN 端激酶(JNK)和 p38 的磷酸化上調的 PCSK9 促進 AS 病變中內皮細胞的凋亡;用 shRNA-PCSK9 靶向敲除 PCSK9,可抑制 ox-LDL 誘導的 p38 和 JNK 磷酸化,下調 Bax 與 Bcl2 的比例,從而抑制內皮細胞的凋亡[38]。
此外,PCSK9 與自噬和焦亡有關[39]。自噬能夠清除受損的線粒體,這對維持細胞存活和正常功能有很大的作用[40]。從自噬中逃逸的線粒體 DNA 可導致炎癥和心力衰竭的發生[41]。當使用 3-甲基腺嘌呤抑制自噬時,PCSK9 在細胞質中積累,提示其可能與自噬有關。炎癥條件下,PCSK9 升高破壞線粒體 DNA,促進平滑肌細胞中線粒體活性氧的形成,進而促進 PCSK9 和血凝素樣氧化LDL-R1 的上調[42]。與野生小鼠相比,當進行 PCSK9 敲除或使用 PCSK9 抑制劑 Pep2-8 治療的小鼠發生 MI 時,梗死面積更小,自噬減少[39]。在慢性心肌缺血過程中,上調的 PCSK9 誘導線粒體 DNA 損傷,激活 NLRP3 炎性小體信號傳導,促進 caspase 1 依賴性焦亡[43]。在 PCSK9 基因敲除小鼠中,缺血心臟中 NLRP3 的激活和氮端 Gasdermin D 的上調被抑制[42]。因此,PCSK9 能夠抑制自噬,但促進細胞凋亡和焦亡,這對 ASCVD 的預后會產生不利影響。
5 小結
PCSK9 通過包括調節脂質代謝、促進炎癥反應、促進血小板活化、促進血栓形成、促進細胞凋亡、促進焦亡、抑制自噬等在內的多種機制影響 ASCVD 的發生和發展。隨著對 ASCVD 患者的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研究結果發現 PCSK9 已成為他汀類藥物不耐受或最大劑量他汀類藥物治療后未能達到血脂目標的 ASCVD 患者新的治療靶點。但對于 PCSK9 在 ASCVD 的作用機制和路徑尚未完全明晰,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更加精準改善 ASCVD 患者的預后。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