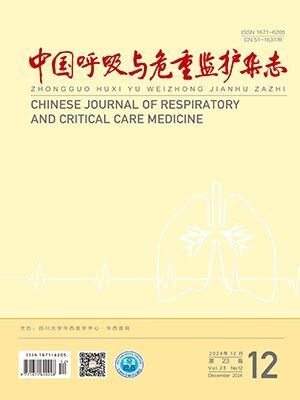引用本文: 梁穎, 王曉, 繆黃泰, 左惠娟, 聶紹平. 肺栓塞快速反應團隊(PERT)模式對急性肺栓塞患者治療策略和遠期預后的影響—PERT實施一年研究結果.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3, 22(11): 782-788. doi: 10.7507/1671-6205.202309039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是心血管死亡的第三大原因[1],但全球公眾認知度較低。其早期表現復雜多樣且多無典型癥狀,容易漏診、誤診和延誤診斷。鑒于疾病復雜性和治療多樣化,美國在2012年成立了全球第一支多個學科參加的肺栓塞救治團隊(Pulmonary Embolism Response Team,PERT)。該模式能迅速匯集不同學科專家,為病情危重的APE患者進行快速診斷和治療決策。2017年7月,我國第一支PERT團隊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成立,開啟了中國急性肺栓塞多學科團隊救治的新時代[2-3]。但中國首個PERT的運行情況、治療策略和遠期預后還缺少評價。因此,有必要對本醫療中心PERT實施后的數據進行總結和進一步研究。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以PERT正式啟動為節點,通過醫院電子病歷系統回顧性收集2016年7月5日—2018年7月4日期間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就診的APE患者,其中2016年7月5日—2017年7月4日PERT實施前接受傳統治療的APE患者為對照組(Pre-PERT組),2017年7月5日—2018年7月4日啟動PERT模式救治的APE患者為干預組(Post-PERT組)。納入標準:(1)所有入選的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患者均符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制定的《肺血栓栓塞癥診治與預防指南》[4]標準,患者均通過CT肺動脈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和(或)肺通氣灌注掃描確診為APE;(2)年齡≥18歲。排除標準:住院臨床資料不完整的患者。本研究經過北京安貞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2023020X)。
1.2 隨訪信息
對患者出院1年時的情況進行評估。制定統一的信息采集表(表1),通過電話、門診面對面訪談及門診電子病歷系統獲取隨訪信息,主要內容包括:抗凝藥物使用、是否抗凝達標、抗凝時長、是否規律隨訪和接受醫生出院后指導,結局事件(出血事件、肺栓塞再住院、死亡)。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分類變量以頻率(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的差異采用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中位數(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兩組差異的比較中采用Wilcoxon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了研究對象210例,平均年齡(63.3±13.7)歲,女102例(48.6%)。Pre-PERT組患者108例,Post-PERT組患者102例。兩組APE患者年齡和性別構成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比較,其臨床表現、PE易患因素、腦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氨基末端腦鈉肽前體(N terminal pro B 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和肌鈣蛋白I(troponin I,TnI)陽性率、PE危險分層、PE阻塞部位以及超聲心動圖特點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結果見表2。
在創立PERT(Post-PERT)之后,啟動PERT的科室來源于急診科、門診和住院病房。其中,外院醫療中心轉來的PE患者占2.9%。從患者來源上,和創立PERT之前無顯著差異。結果見表3。
2.2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兩組患者臨床治療方案比較
Post-PERT組患者和Pre-PERT組患者抗凝治療率、導管定向治療(catheter-directed treatment,CDT)、下腔靜脈濾器(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s,IVCF)、外科血栓切除術(surgical embolectomy,SE)、全身溶栓(systemic thrombolysis,ST)治療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患者都沒有使用體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進行循環支持治療的病例。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患者使用抗凝以及抗血小板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結果見表4。
2.3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兩組患者出院隨訪情況比較
兩組210例患者中157例接受電話隨訪,隨訪率為74.8%。其中,Post-PERT組隨訪79例,占77.5%;Pre-PERT組隨訪78例,占72.2%。無應答原因主要為所留電話無效、電話無人接聽和拒絕接受電話隨訪,Post-PERT組患者分別為13例(3.0%)、15例(65.2%)和5例(21.7%);Pre-PERT組患者分別為9例(30.0%)、11例(36.7%)和10例(33.3%)。
Post-PERT組使用華法林、利伐沙班和低分子肝素比率與Pre-PERT組相比,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Post-PERT組抗凝達標率和Pre-PERT組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抗凝時長Post-PERT組平均為11.9個月,顯著高于Pre-PERT組(10.3個月;t=–4.490,P<0.001)。結果見表5。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規律隨訪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接受醫生微信管理的患者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ost-PERT組和Pre-PERT組隨訪1年全因死亡率、出血事件發生率、因PE再住院率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結果見表5。兩組均未見因肺栓塞死亡的患者,兩組患者死亡原因均為惡性腫瘤和其他疾病原因。隨訪兩組患者未見大出血事件,出血均為臨床相關的非大出血。結果見表6。
3 討論
PE是一種隱匿性高致死性疾病,發病率逐年上升。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全世界每年約有1 000萬例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患者,APE患者30天病死率高達30%,30%的PE患者10年內復發VTE,50%的VTE會發展為血栓后綜合征[5]。2019年我國PE與肺血管病防治協作組共收集了全國90家醫院105 723例以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VTE和PE為主要診斷的患者,對2007—2016年患者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PE人群患病率從2007年1.2/10萬人上升到2016年7.1/10萬人,住院患者中APE比例從1.1‰上升至6.3‰[6]。PE已經成為一種嚴重的疾病負擔和世界性的健康問題。
最近十年以來,肺血管疾病領域進展迅速,新的治療方法不斷涌現,隨著研究證據不斷積累,PE的診療模式發生了較大改變。為了進一步提高APE的救治水平,Kenneth Rosenfield教授于2015年成立了PERT聯盟,目的在于指導PERT團隊的建設與發展,提高危重肺栓塞的診斷與救治水平。繼2017年7月5日我國第一個PERT成立之后,同年10月又成立了我國首家PERT聯盟,旨在為更多PE患者提供及時診斷和有效的治療[3]。但是,世界上不同醫療中心的關于PERT的研究數據非常有限并且研究結果不一致,也迫切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來評價。
APE治療手段日趨廣泛,包括抗凝治療以及近年逐漸興起的高級別治療手段如ST、CDT、SE和ECMO等。其中,抗凝治療仍是APE治療的基礎和核心,對降低PE復發率及改善患者預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旦確診PE并且無禁忌證的情況下,應該盡快啟動抗凝治療策略。對于高危APE患者,因ST治療方法可迅速地溶解血栓,恢復肺組織再灌注,可顯著降低PE患者的病死率和復發率,也是目前醫療中心首選的再灌注治療手段。對于血流動力學進一步惡化的APE患者,2019年PE指南推薦進行補救性溶栓治療(Ⅰ/B,原為Ⅱa級證據)[7]。另有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對于院外心臟驟停后確診PE患者,在心肺復蘇過程中采用ST顯著改善30天生存率[8]。盡管如此,在世界范圍內溶栓治療應用的比例仍較低。一項德國的住院PE數據顯示,ST的比例從2005年的3.1%升至2015年的4.4%,臨床醫師往往對ST所致的大出血或顱內出血風險心存顧慮,急性高危PE治療不足的現象普遍存在[9]。本研究比較了兩組間單純抗凝和其他高級別治療方法的比率,結果表明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患者抗凝治療的比率最高,分別為87.3% 和81.5%,可見抗凝治療仍是目前這兩組患者的主要治療方案;CDT治療的患者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分別為3.9%和2.8%,在PERT實施的第1年呈現擴大的趨勢,但兩組相比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近年來雖然先進的治療手段不斷出現,但仍只有少數患者進行這樣的治療。PE高級別治療水平參差不齊,和國外研究相比,對于高危APE患者的再灌注治療比率仍比較低[10]。
近年來,鑒于PE抗凝和溶栓治療方法的局限性,高級別治療手段如CDT逐漸興起,由于其顯著減少溶栓藥物總劑量并可在血栓處定向釋放,有望達到或超過ST的效果并顯著降低大出血發生率。但CDT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證據多是小規模、單中心研究[11]。來自麻省總醫院的數據顯示,與實施PERT之前相比, PERT實施后更多中-高危PE患者得到評估和治療(49%比32%),接受CDT的比率兩組相近(1.9%比2.0%)或任何高級別治療(8.3%比7.8%)[12]。一項由24個國家325家醫院組成的大型注冊研究結果顯示,3.5%的PE患者血流動力學不穩定。與其他PE患者相比,這些APE患者的預后明顯較差,但是只有20%的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PE患者接受了高級別的治療[13]。這些發現表明改善不穩定PE患者的管理還有很大的潛力。此外,一項納入28項研究的Meta分析結果也顯示,對于高危或中-高危的APE患者,超聲輔助CDT可使肺動脈收縮壓和平均壓分別下降16.69 mm Hg和12.13 mm Hg,右心室/左心室直徑比降低0.35[14],但目前尚無CDT治療改善臨床預后的證據。
SE治療可迅速取出PE患者新鮮血栓,因此對于溶栓有禁忌證或溶栓失敗的PE患者仍不失為一種理想治療選擇。與ST相比,SE的大出血發生率較低,且再發PE的比例較低。2019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頒布的PE指南對于有溶栓禁忌或治療失敗的高危PE患者推薦應用SE(Ⅰ/C)。美國胸外科醫師學會成人心臟外科數據庫的統計資料顯示,在2011—2015年,全美1 144家醫學中心1 075例SE治療患者病死率為16%[15]。本研究結果表明,Post-PERT組比Pre-PERT組患者SE比率均有增加趨勢(2.0%比0.9%),但兩組PE患者相比沒有顯著差異。此外,本研究結果還顯示IVCF使用率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分別為1.0%和1.9%,兩組均沒有使用ECMO治療。總之,本中心在急性高危、復雜PE救治方面,高級別治療手段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研究所截取的時間段較短,僅是對PERT實施1年的部分數據進行總結,因此對于這項技術的近期和遠期療效有待于更多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來進一步評估。
PERT模式救治APE非常強調患者的隨訪管理。文獻報道APE發作后最初幾個月,大多數患者肺動脈恢復通暢,很多患者仍持續性呼吸困難或運動受限,約1.0%~3.8%患者進展為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16]。一項大型回顧性研究納入7 068例診斷為PE因各種原因院內進行隨訪的患者,發現大多數患者在PE后仍有癥狀包括呼吸困難、疲乏、頭重腳輕或下肢水腫等,但在2年的隨訪中僅61%的患者進行了與CTEPH相關的檢查如CTPA、肺通氣灌注掃描和心電圖[17]。此外,也有研究表明APE患者有較高的栓塞復發率,早期識別APE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對制定個體化的抗凝方案、改善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18]。因此,需要對PE患者進行定期隨訪,可通過建立PERT門診,完善PE患者的隨訪數據庫,及早發現PE患者更多與診斷、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相關的信息,討論制定長期管理計劃,更好地預防肺栓塞再發,減少致殘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目前,抗凝治療方面,新型口服抗凝藥(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s,NOACs)正逐漸成為APE患者口服抗凝首選的治療策略。近年來,國外多項大型隨機對照試驗已證實直接口服抗凝藥(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DOACs)在急性PE急性期抗凝治療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由于起效迅速、半衰期短、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明確、劑量固定和較少的藥物相互作用,DOACs對于低危PE患者已成為一線治療,而對于中高危PE患者在臨床穩定或高級別治療完成后也應考慮應用。2019年ESC發布的APE診斷和管理指南中,DOACs在低中危患者中獲優先推薦,一旦需要啟動口服抗凝治療,如無禁忌,應優先使用NOACs治療而非華法林(Ⅰ/A)[7]。本研究隨訪數據顯示,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在出院后使用華法林、利伐沙班和低分子肝素比例分別為24例(43.6%)、30例(54.5%)和1例(1.8%),以及49例(59.0%),27例(32.5%)和4例(4.8%);華法林改利伐沙班3例(3.6%)。結果顯示,Post-PERT組使用利伐沙班比Pre-PERT組患者比例增多,而使用華法林患者比例逐漸減少,Post-PERT組抗凝時長比Pre-PERT組長,平均療程接近1年,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ost-PERT組患者抗凝治療依從性比Pre-PERT組好,抗凝時間更充分,這可能與PERT制定的隨訪計劃,以及利伐沙班抗凝簡單、易于維持、藥物食物相互作用少、無需注射、單藥治療、依從性好有關系。但是,每個國家和地區根據可獲得藥品的資源來確定使用哪種新型口服抗凝藥,而且抗凝療程依照患者具體情況而定[4,7]。隨訪1年后兩組病死率、出血事件發生率和因肺栓塞再住院率相比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兩組患者死亡原因多為惡性腫瘤和非肺栓塞相關的其他疾病導致的死亡,出血事件發生均為臨床相關的非大出血,比如眼睛出血、消化道出血、皮膚瘀斑、紫癜、牙齦出血、鼻出血等。研究也表明,雖然APE先進的手術治療手段在1年里有增加趨勢,但全因死亡率以及出血事件并沒有呈現增加趨勢。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受近年來新冠疫情的影響,APE收治流程跟隨國家政策和北京市政府防疫管理要求做相應變化,因此未能連續納入自PERT建立以來收治的所有APE患者;本研究只對比了PERT成立前后1年的數據,納入樣本量較少;此外,部分患者電子病歷記錄不完整,長期隨訪受到限制也造成研究對象的偏倚。
綜上所述,PERT模式雖然在中國迅速發展,但是與西方國家相比,具有先進療法的專業參與度相對較低,高級別治療方法較少,仍處于PERT發展的初級階段。在本醫療中心PERT運行的早期階段,APE治療仍以抗凝為主,開展高級治療較少,不穩定PE患者高級別治療方法的實施還有很大的空間。隨訪發現APE患者對于新型口服抗凝藥依從性更好,更好規范化管理出院的PE患者。此外,PERT患者隨訪率低而且隨訪數據記錄不完善,需要進一步完善PERT隨訪體系和數據庫建設,加強肺栓塞患者自我管理意識,減少出血和死亡等不良事件。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是心血管死亡的第三大原因[1],但全球公眾認知度較低。其早期表現復雜多樣且多無典型癥狀,容易漏診、誤診和延誤診斷。鑒于疾病復雜性和治療多樣化,美國在2012年成立了全球第一支多個學科參加的肺栓塞救治團隊(Pulmonary Embolism Response Team,PERT)。該模式能迅速匯集不同學科專家,為病情危重的APE患者進行快速診斷和治療決策。2017年7月,我國第一支PERT團隊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成立,開啟了中國急性肺栓塞多學科團隊救治的新時代[2-3]。但中國首個PERT的運行情況、治療策略和遠期預后還缺少評價。因此,有必要對本醫療中心PERT實施后的數據進行總結和進一步研究。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以PERT正式啟動為節點,通過醫院電子病歷系統回顧性收集2016年7月5日—2018年7月4日期間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就診的APE患者,其中2016年7月5日—2017年7月4日PERT實施前接受傳統治療的APE患者為對照組(Pre-PERT組),2017年7月5日—2018年7月4日啟動PERT模式救治的APE患者為干預組(Post-PERT組)。納入標準:(1)所有入選的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患者均符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制定的《肺血栓栓塞癥診治與預防指南》[4]標準,患者均通過CT肺動脈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和(或)肺通氣灌注掃描確診為APE;(2)年齡≥18歲。排除標準:住院臨床資料不完整的患者。本研究經過北京安貞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2023020X)。
1.2 隨訪信息
對患者出院1年時的情況進行評估。制定統一的信息采集表(表1),通過電話、門診面對面訪談及門診電子病歷系統獲取隨訪信息,主要內容包括:抗凝藥物使用、是否抗凝達標、抗凝時長、是否規律隨訪和接受醫生出院后指導,結局事件(出血事件、肺栓塞再住院、死亡)。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分類變量以頻率(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的差異采用兩獨立樣本的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中位數(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兩組差異的比較中采用Wilcoxon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本研究共納入了研究對象210例,平均年齡(63.3±13.7)歲,女102例(48.6%)。Pre-PERT組患者108例,Post-PERT組患者102例。兩組APE患者年齡和性別構成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比較,其臨床表現、PE易患因素、腦鈉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BNP)/氨基末端腦鈉肽前體(N terminal pro B 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和肌鈣蛋白I(troponin I,TnI)陽性率、PE危險分層、PE阻塞部位以及超聲心動圖特點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結果見表2。
在創立PERT(Post-PERT)之后,啟動PERT的科室來源于急診科、門診和住院病房。其中,外院醫療中心轉來的PE患者占2.9%。從患者來源上,和創立PERT之前無顯著差異。結果見表3。
2.2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兩組患者臨床治療方案比較
Post-PERT組患者和Pre-PERT組患者抗凝治療率、導管定向治療(catheter-directed treatment,CDT)、下腔靜脈濾器(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s,IVCF)、外科血栓切除術(surgical embolectomy,SE)、全身溶栓(systemic thrombolysis,ST)治療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患者都沒有使用體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進行循環支持治療的病例。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患者使用抗凝以及抗血小板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結果見表4。
2.3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兩組患者出院隨訪情況比較
兩組210例患者中157例接受電話隨訪,隨訪率為74.8%。其中,Post-PERT組隨訪79例,占77.5%;Pre-PERT組隨訪78例,占72.2%。無應答原因主要為所留電話無效、電話無人接聽和拒絕接受電話隨訪,Post-PERT組患者分別為13例(3.0%)、15例(65.2%)和5例(21.7%);Pre-PERT組患者分別為9例(30.0%)、11例(36.7%)和10例(33.3%)。
Post-PERT組使用華法林、利伐沙班和低分子肝素比率與Pre-PERT組相比,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Post-PERT組抗凝達標率和Pre-PERT組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抗凝時長Post-PERT組平均為11.9個月,顯著高于Pre-PERT組(10.3個月;t=–4.490,P<0.001)。結果見表5。
Post-PERT組和Pre-PERT組規律隨訪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接受醫生微信管理的患者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ost-PERT組和Pre-PERT組隨訪1年全因死亡率、出血事件發生率、因PE再住院率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結果見表5。兩組均未見因肺栓塞死亡的患者,兩組患者死亡原因均為惡性腫瘤和其他疾病原因。隨訪兩組患者未見大出血事件,出血均為臨床相關的非大出血。結果見表6。
3 討論
PE是一種隱匿性高致死性疾病,發病率逐年上升。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全世界每年約有1 000萬例靜脈血栓栓塞癥(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患者,APE患者30天病死率高達30%,30%的PE患者10年內復發VTE,50%的VTE會發展為血栓后綜合征[5]。2019年我國PE與肺血管病防治協作組共收集了全國90家醫院105 723例以深靜脈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VTE和PE為主要診斷的患者,對2007—2016年患者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PE人群患病率從2007年1.2/10萬人上升到2016年7.1/10萬人,住院患者中APE比例從1.1‰上升至6.3‰[6]。PE已經成為一種嚴重的疾病負擔和世界性的健康問題。
最近十年以來,肺血管疾病領域進展迅速,新的治療方法不斷涌現,隨著研究證據不斷積累,PE的診療模式發生了較大改變。為了進一步提高APE的救治水平,Kenneth Rosenfield教授于2015年成立了PERT聯盟,目的在于指導PERT團隊的建設與發展,提高危重肺栓塞的診斷與救治水平。繼2017年7月5日我國第一個PERT成立之后,同年10月又成立了我國首家PERT聯盟,旨在為更多PE患者提供及時診斷和有效的治療[3]。但是,世界上不同醫療中心的關于PERT的研究數據非常有限并且研究結果不一致,也迫切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來評價。
APE治療手段日趨廣泛,包括抗凝治療以及近年逐漸興起的高級別治療手段如ST、CDT、SE和ECMO等。其中,抗凝治療仍是APE治療的基礎和核心,對降低PE復發率及改善患者預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旦確診PE并且無禁忌證的情況下,應該盡快啟動抗凝治療策略。對于高危APE患者,因ST治療方法可迅速地溶解血栓,恢復肺組織再灌注,可顯著降低PE患者的病死率和復發率,也是目前醫療中心首選的再灌注治療手段。對于血流動力學進一步惡化的APE患者,2019年PE指南推薦進行補救性溶栓治療(Ⅰ/B,原為Ⅱa級證據)[7]。另有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對于院外心臟驟停后確診PE患者,在心肺復蘇過程中采用ST顯著改善30天生存率[8]。盡管如此,在世界范圍內溶栓治療應用的比例仍較低。一項德國的住院PE數據顯示,ST的比例從2005年的3.1%升至2015年的4.4%,臨床醫師往往對ST所致的大出血或顱內出血風險心存顧慮,急性高危PE治療不足的現象普遍存在[9]。本研究比較了兩組間單純抗凝和其他高級別治療方法的比率,結果表明Post-PERT組和Pre-PERT組患者抗凝治療的比率最高,分別為87.3% 和81.5%,可見抗凝治療仍是目前這兩組患者的主要治療方案;CDT治療的患者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分別為3.9%和2.8%,在PERT實施的第1年呈現擴大的趨勢,但兩組相比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近年來雖然先進的治療手段不斷出現,但仍只有少數患者進行這樣的治療。PE高級別治療水平參差不齊,和國外研究相比,對于高危APE患者的再灌注治療比率仍比較低[10]。
近年來,鑒于PE抗凝和溶栓治療方法的局限性,高級別治療手段如CDT逐漸興起,由于其顯著減少溶栓藥物總劑量并可在血栓處定向釋放,有望達到或超過ST的效果并顯著降低大出血發生率。但CDT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證據多是小規模、單中心研究[11]。來自麻省總醫院的數據顯示,與實施PERT之前相比, PERT實施后更多中-高危PE患者得到評估和治療(49%比32%),接受CDT的比率兩組相近(1.9%比2.0%)或任何高級別治療(8.3%比7.8%)[12]。一項由24個國家325家醫院組成的大型注冊研究結果顯示,3.5%的PE患者血流動力學不穩定。與其他PE患者相比,這些APE患者的預后明顯較差,但是只有20%的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的PE患者接受了高級別的治療[13]。這些發現表明改善不穩定PE患者的管理還有很大的潛力。此外,一項納入28項研究的Meta分析結果也顯示,對于高危或中-高危的APE患者,超聲輔助CDT可使肺動脈收縮壓和平均壓分別下降16.69 mm Hg和12.13 mm Hg,右心室/左心室直徑比降低0.35[14],但目前尚無CDT治療改善臨床預后的證據。
SE治療可迅速取出PE患者新鮮血栓,因此對于溶栓有禁忌證或溶栓失敗的PE患者仍不失為一種理想治療選擇。與ST相比,SE的大出血發生率較低,且再發PE的比例較低。2019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ESC)頒布的PE指南對于有溶栓禁忌或治療失敗的高危PE患者推薦應用SE(Ⅰ/C)。美國胸外科醫師學會成人心臟外科數據庫的統計資料顯示,在2011—2015年,全美1 144家醫學中心1 075例SE治療患者病死率為16%[15]。本研究結果表明,Post-PERT組比Pre-PERT組患者SE比率均有增加趨勢(2.0%比0.9%),但兩組PE患者相比沒有顯著差異。此外,本研究結果還顯示IVCF使用率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分別為1.0%和1.9%,兩組均沒有使用ECMO治療。總之,本中心在急性高危、復雜PE救治方面,高級別治療手段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本研究所截取的時間段較短,僅是對PERT實施1年的部分數據進行總結,因此對于這項技術的近期和遠期療效有待于更多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來進一步評估。
PERT模式救治APE非常強調患者的隨訪管理。文獻報道APE發作后最初幾個月,大多數患者肺動脈恢復通暢,很多患者仍持續性呼吸困難或運動受限,約1.0%~3.8%患者進展為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16]。一項大型回顧性研究納入7 068例診斷為PE因各種原因院內進行隨訪的患者,發現大多數患者在PE后仍有癥狀包括呼吸困難、疲乏、頭重腳輕或下肢水腫等,但在2年的隨訪中僅61%的患者進行了與CTEPH相關的檢查如CTPA、肺通氣灌注掃描和心電圖[17]。此外,也有研究表明APE患者有較高的栓塞復發率,早期識別APE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對制定個體化的抗凝方案、改善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18]。因此,需要對PE患者進行定期隨訪,可通過建立PERT門診,完善PE患者的隨訪數據庫,及早發現PE患者更多與診斷、病情嚴重程度和預后相關的信息,討論制定長期管理計劃,更好地預防肺栓塞再發,減少致殘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目前,抗凝治療方面,新型口服抗凝藥(non-vitamin K antagonist oral anticoagulants,NOACs)正逐漸成為APE患者口服抗凝首選的治療策略。近年來,國外多項大型隨機對照試驗已證實直接口服抗凝藥(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DOACs)在急性PE急性期抗凝治療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由于起效迅速、半衰期短、藥代動力學和藥效動力學明確、劑量固定和較少的藥物相互作用,DOACs對于低危PE患者已成為一線治療,而對于中高危PE患者在臨床穩定或高級別治療完成后也應考慮應用。2019年ESC發布的APE診斷和管理指南中,DOACs在低中危患者中獲優先推薦,一旦需要啟動口服抗凝治療,如無禁忌,應優先使用NOACs治療而非華法林(Ⅰ/A)[7]。本研究隨訪數據顯示,Post-PERT組和Pre-PERT組在出院后使用華法林、利伐沙班和低分子肝素比例分別為24例(43.6%)、30例(54.5%)和1例(1.8%),以及49例(59.0%),27例(32.5%)和4例(4.8%);華法林改利伐沙班3例(3.6%)。結果顯示,Post-PERT組使用利伐沙班比Pre-PERT組患者比例增多,而使用華法林患者比例逐漸減少,Post-PERT組抗凝時長比Pre-PERT組長,平均療程接近1年,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ost-PERT組患者抗凝治療依從性比Pre-PERT組好,抗凝時間更充分,這可能與PERT制定的隨訪計劃,以及利伐沙班抗凝簡單、易于維持、藥物食物相互作用少、無需注射、單藥治療、依從性好有關系。但是,每個國家和地區根據可獲得藥品的資源來確定使用哪種新型口服抗凝藥,而且抗凝療程依照患者具體情況而定[4,7]。隨訪1年后兩組病死率、出血事件發生率和因肺栓塞再住院率相比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兩組患者死亡原因多為惡性腫瘤和非肺栓塞相關的其他疾病導致的死亡,出血事件發生均為臨床相關的非大出血,比如眼睛出血、消化道出血、皮膚瘀斑、紫癜、牙齦出血、鼻出血等。研究也表明,雖然APE先進的手術治療手段在1年里有增加趨勢,但全因死亡率以及出血事件并沒有呈現增加趨勢。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受近年來新冠疫情的影響,APE收治流程跟隨國家政策和北京市政府防疫管理要求做相應變化,因此未能連續納入自PERT建立以來收治的所有APE患者;本研究只對比了PERT成立前后1年的數據,納入樣本量較少;此外,部分患者電子病歷記錄不完整,長期隨訪受到限制也造成研究對象的偏倚。
綜上所述,PERT模式雖然在中國迅速發展,但是與西方國家相比,具有先進療法的專業參與度相對較低,高級別治療方法較少,仍處于PERT發展的初級階段。在本醫療中心PERT運行的早期階段,APE治療仍以抗凝為主,開展高級治療較少,不穩定PE患者高級別治療方法的實施還有很大的空間。隨訪發現APE患者對于新型口服抗凝藥依從性更好,更好規范化管理出院的PE患者。此外,PERT患者隨訪率低而且隨訪數據記錄不完善,需要進一步完善PERT隨訪體系和數據庫建設,加強肺栓塞患者自我管理意識,減少出血和死亡等不良事件。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