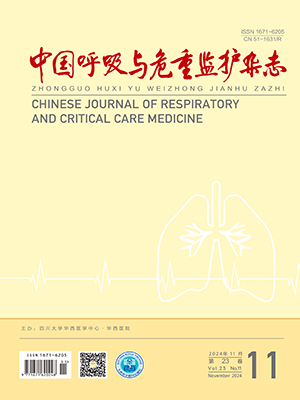引用本文: 何炎芮, 林平, 胡群, 周海霞, 梁宗安, 王茂筠. VTE抗凝相關大出血風險及相關預測模型研究進展.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4, 23(2): 138-143. doi: 10.7507/1671-6205.202311001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靜脈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embolism,VTE)是一種常見的,危害人類健康的血管疾病,包括深靜脈血栓形成和肺動脈栓塞,年發病率可達1-2例/1000人,給全球帶來重大的健康和經濟負擔[1]。抗凝治療是VTE治療的基礎,可有效改善疾病預后[2]。除傳統的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聯合華法林抗凝治療,直接口服抗凝藥物(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DOACs)也不斷發展。然而,抗凝治療也帶來患者出血風險的增加。國際血栓與止血學會(ISTH)將抗凝后出血分為大出血、小出血和臨床相關非大出血三種情況,其中大出血定義為:(1)致死性出血;(2)重要區域或器官中的癥狀性出血:顱內、脊柱內、眼內、腹膜后、關節內、心包內以及出血引起的骨筋膜室綜合征;(3)出血導致血紅蛋白水平下降20 g / L以上,或導致輸注2個或2個以上單位的全血或紅細胞。一旦發生活動性出血,尤其是大出血,患者往往預后不良,致死率和致殘率均明顯升高[3-4]。因此,對于進行抗凝治療的VTE患者,識別并監測抗凝相關大出血的危險因素尤為重要。目前已經有不少研究關注抗凝相關大出血危險因素,并開發出一些出血風險預測模型,從早期的Landefeld評分[5-6]、Nieuwenhuis評分[7],到最近的PE-SARD評分等[8]。本綜述對不同抗凝藥物及不同抗凝階段的大出血風險進行比較、對VTE抗凝治療相關大出血風險預測模型研究進行了總結,期望可以給未來VTE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的發展提供新思路。
1 不同抗凝藥物相關大出血風險比較
1.1 低分子肝素與普通肝素抗凝相關大出血風險
普通肝素作為最傳統的抗凝藥物,主要通過結合抗凝血酶III從而增加對活化的II、IX、X、XI和XII凝血因子的抑制,自發性出血傾向是其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可表現為各種粘膜出血、關節腔積血及傷口出血,其治療過程中需根據嚴密監測的APTT調整劑量。低分子肝素是普通肝素裂解后的產物,分子量低于普通肝素,引起的出血風險小于普通肝素。
多項關于VTE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療效及安全性的隨機對照試驗結果顯示:在普通肝素組中的大出血發生頻率均高于低分子肝素組[9-11];Cochrane的一項meta分析納入了25項在靜脈血栓栓塞患者中比較固定劑量皮下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heparin,LWMH)與調整劑量靜脈或皮下注射普通肝素(unfractionated heparin,UFH)的隨機對照試驗[12],結果表明:初始治療期間使用低分子肝素不僅可以減少靜脈血栓栓塞事件的復發,而且大出血發生率明顯降低(LWMH:65/4333 VS UFH:94/4447,Peto OR:0.69,95%CI:0.50-0.95,P=0.02),DVT患者的亞組分析結果支持上述結論。LWMH固定的給藥劑量和方式提供了更穩定的抗凝血水平,而普通肝素則需根據實驗室監測指標不斷進行劑量調整,這可能導致抗凝血水平的波動,或許是普通肝素出血風險更大的原因。從實際應用角度來說,LWMH每日1-2次皮下注射的給藥途徑更加便捷,患者行動可不受限制,依從行可能更高。并且藥代動力學更具有可預測性,無需實驗室監測和后續劑量調整。
1.2 華法林聯合低分子肝素與DOACs抗凝相關大出血
目前多項研究發現,在VTE患者中使用DOACs藥物,相較于傳統的華法林聯合低分子肝素抗凝方案,可減少抗凝相關大出血的風險。
AMPLFY研究顯示,阿哌沙班組比低分子肝素組大出血風險更低(RR:0.31,95% CI:0.17-0.55,P <0.00)[13]。一項納入了6個有關DOAC與華法林在治療急性癥狀性VTE的療效與安全性的3期臨床試驗的meta分析表明[14],DOAC治療組比華法林治療組在預防復發性VTE方面作用相似,但DOAC治療組比華法林治療組的大出血發生明顯降低(1.1% VS 1.75%,RR:0.61,95%CI:0.45 - 0.83),上述兩個結論在顱內出血、致死性出血、中度腎功能不全、大于75歲的患者亞組中的結果均是一致的。
在需要延長抗凝治療患者中,VKA的使用會帶來出血風險增高。一項Meta分析納入了16個延長使用抗凝藥物(VKA或者DOACs)與安慰劑的在VTE治療相關生存獲益、血栓復發及安全性方面的比較的隨機對照試驗[15],結果表明,相較于對照組(觀察、安慰劑或阿司匹林),VKA組中大出血風險增高(RR 2.67,95%CI:1.28-5.60,P<0.01),而在DOACs組中未見到大出血風險的增高(P>0.5)。
2 延展期抗凝對抗凝相關大出血影響
對于VTE抗凝治療,常規推薦3-6個月抗凝,但對于首次無誘因小腿近端DVT或PE、復發性無誘因的VTE患者、VTE合并活動性腫瘤(“癌癥相關血栓”),國內外多個指南[16-17]推薦進行延展期抗凝。延長抗凝治療可能帶來大出血風險增加,Mai等關于延長抗凝治療效果及安全性的隨機對照試驗的meta分析顯示[15],延長抗凝組較對照組(安慰劑組/觀察組)的大出血風險顯著增加(0.76% VS 0.32%,RR:2.00,95%CI:1.14-3.53,P=0.02;I2=4 0 %)。需要注意的是,是否進行延長抗凝的決策仍取決于對于患者出血及復發性血栓的收益評估,且需定期評估。
3 VTE患者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
3.1 Landefeld評分
Landefeld等[5]開發并驗證了一項抗凝大出血評分表,根據四個條目:開始治療時合并癥的數目、開始治療時的年齡、治療過程中最大PT或APTT與對照組倍數、肝功能異常惡化,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風險等級。該評分在同源的206名患者中進行了驗證,結果表明大出血發生率隨著危險級別增高而增高。該模型四個危險因素包含了治療開始時及治療過程中的情況,這反映了抗凝出血風險的動態評估。從研究數據來看,相較于僅包含治療開始時的兩個危險因素過程的預測模型進行比較,四個危險因素的模型更加準確。然而,該模型在建立的過程中收集的資料較少,可能遺漏一些影響抗凝相關大出血的危險因素,例如住院期間的其他藥物使用情況。暫無相關研究對該模型進行外部驗證。
3.2 Landefeld及Goldman評分
Landefeld等[6]通過回顧性分析562名出院后開始華法林門診治療的患者,構建了評分。條目包括:年齡、腦卒中病史、消化道出血病史、嚴重合并癥(近期有心肌梗死、腎功能不全或嚴重貧血、房顫),同樣將出血風險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風險等級。該評分在驗證組中,低危患者48個月的大出血累積發生率為2%,中危患者為17%,高危患者為63%。在亞組分析中,心臟瓣膜手術組和其他抗凝適應證組(包括二尖瓣病變、房顫、中風、短暫性腦缺血發作、肺栓塞、深靜脈血栓或其他血栓栓塞癥)中,三個風險組別間大出血發生率也有顯著差別。同時,研究中發現發生顱內出血的病例中房顫患者占比64%。考慮到房顫形成的小動脈血栓形成的亞臨床缺血從而可能誘發出血,該評分將房顫作為抗凝相關大出血的危險因素之一。這也提醒臨床醫生,在因房顫進行預防性抗凝治療的患者中的大出血風險尤其是顱內出血可能較高。Nieuwenhuis等[7]在VTE患者的抗凝相關大出血研究中對該模型進行了外部驗證,結果表明此評分并未在驗證人群中識別出大出血患者。
3.3 Nieuwenhuis評分
Nieuwenhuis等[7]在一項比較LMWH 與標準肝素治療急性靜脈血栓栓塞癥的隨機對照試驗中探索了大出血危險因素。研究發現WHO體能狀態分級級別越高,出血風險越大。體表總面積小于2 m2的患者出血風險增加7.3倍。最終納入預測抗凝治療后大出血評分中的內容為:WHO體能分級、既往有出血病史、近期(< 2個月)外傷或手術、體表面積小于2 m2,危險等級劃分為低危、中危和高危。在研究人群中,評分≥5分(高危)的患者中44%的患者發生了嚴重出血,中危組11%,低危組2%。本研究將WHO體能分級納入評估,且發現該指標與抗凝相關大出血的相關性,這為今后的抗凝相關大出血的獨立危險因素研究提供了一個思路。
3.4 OBRI評分
Beyth等[]根據口服華法林抗凝的565名門診患者,建立了含有4個危險因素的大出血風險評分:年齡>65歲、胃腸道出血史、卒中史和存在一種或多種特定的合并癥(近期心肌梗死、腎功能不全、重度貧血或糖尿病),將風險劃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等級。在模型建立人群中的C指數為0.72。在外部驗證中,OBRI評分C指數為0.78,這說明該模型預測效能中等偏上。但由于該模型納入了不同原因服用華法林的患者,并未區分具體病種,這使OBRI評分在不同疾病中應用受限。
3.5 Kuijer評分
Kuijer等[19]利用一項比較VTE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進行初始治療的優劣的隨機對照試驗,構建了抗凝出血風險預測評分。該簡化風險評分為包含年齡、性別、惡性腫瘤三個因子;按風險等級劃分為低中高危三個等級。在模型建立人群中的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為0.82,21%患者被列為高危,他們發生抗凝相關大出血頻率為14%。在驗證人群中,20%的患者被kuijer出血風險預測評分識別為高風險,而這些患者的大出血頻率為7%,這說明相比于模型建立人群中預測能力所有下降。該評分在既往已經明確的抗凝后出血風險危險因素基礎上選擇了3個簡單、易獲得的臨床變量,簡單易操作。然而,在Riva等[] 針對Kuijer評分的驗證研究中,使用華法林治療的VTE患者組AUC僅為0.51。
3.6 Kearon評分
Kearon等[21]在研究低強度華法林治療(目標INR:1.3-1.9)與常規強度華法林治療(目標INR:2.0-3.0)療效及安全性的過程中,提出抗凝后大出血相關危險因素包括:年齡≥65歲、既往卒中、既往消化性潰瘍病、既往消化道出血、腎損傷、貧血、血小板減少、肝病、糖尿病以及抗血小板治療。大出血頻率隨著入組時已存在的危險因素數目增加而增加。Gage等[22]為老年房顫患者抗凝出血風險制定了分級方案,并在美國全國心房顫動登記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Atrial Fibrillation,NARF)隊列人群進行了外部驗證。結果顯示,在NARF隊列使用華法林抗凝的患者中,Kearson評分的C指數僅為0.66,這說明該評分的預測準確度較低。
3.7 RIETE評分
RIETE隊列是一個由西班牙、法國、意大利、以色列、阿根廷等國家合作構建的多中心、前瞻連續隊列,該隊列由經客觀檢查確診的癥狀性急性VTE患者構成。Ruiz等[23]在RIETE隊列中隨機抽取了67%患者作為模型建立樣本,另33%患者作為內部驗證樣本。該模型指標包括近期出血史、血肌酐>106 mmol/L、貧血、年齡>75歲、基線時具有腫瘤診斷、基線時PE診斷。同樣劃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風險等級。在驗證隊列中,低危患者發生大出血事件的概率為0.1 %;中危患者發生大出血概率為2.8 %,高危組大出血風險概率為6.2%。三個風險等級組間大出血發生率有統計學差異。該評分通過抽取隊列研究人群,相對于臨床隨機對照試驗中選取的人群,更接近于真實世界情況下VTE患者臨床特征和疾病轉歸情況。Tchen等[24]后來在使用DOACs的患者中(未特定病種)對RIETE進行了驗證,其AUC為0.638,這說明預測能力較低。
3.8 ACCP評分
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CCP)基于既往研究,總結了抗凝治療大出血風險危險因素,并進行了低危、中危、高危的風險分級。發布在第9版《VTE抗栓指南:抗血栓治療與血栓預防》中[25]。該指南建議針對一些特定患者,如血栓危險因素暫時不能消除的近端小腿DVT、無誘因的首次小腿近端或孤立遠端DVT、無誘因的復發性VTE的患者,在評估是否進行延展期抗凝治療時需同時評估抗凝相關大出血的風險。Riva等[20]使用ACCP評分在急性肺栓塞患者隊列研究中進行了前瞻性驗證,該評分在抗凝治療六個月內預測大出血準確度低,AUC僅為0.59。Palareti等[26]在2263名進行了延展期抗凝的VTE患者中驗證了ACCP評分,結果也表明,ACCP評分在低危、中危、高危三個出血風險組別中的C指數僅有0.50-0.56。上述研究均表明,ACCP評分不能準確預測延展期抗凝患者的大出血風險。
3.9 VTE-BLEED評分
Klok等[27]在比較達比加群酯和華法林抗凝的RE-COVER 和RE-COVER II試驗中建立了VTE-BLEED評分:活動性癌癥、具有未控制的高血壓的男性、貧血、出血史、>60歲。根據分數劃分為低危和高危兩個風險等級。在達比加群酯衍生人群中,該評分表現良好,AUC為0.72。同時從抗凝穩定期(30天-6個月)表現來看,達比加群酯組的AUC為0.7;華法林組的AUC為0.78。在以上組別中,該評分的區分能力較高,高危患者的大出血風險為低危患者的5-7倍。同時作者還進行了達比加群酯試驗組中急性肺栓塞亞組和深靜脈血栓亞組的驗證,其表現相似。VTE-BLEED評分特別關注了抗凝延展期大出血風險,期望可在抗凝治療3 - 6個月后延長治療的決策過程中提供幫助。
3.10 EINSTEIN評分
Di Nisio等[28]利用EINSTEIN DVT和EINSTEIN PE研究(利伐沙班與依諾肝素和VKA組成的標準療法的比較試驗)DVT或PE患者的大出血情況,探索了大出血的獨立危險因素,衍生出在治療前三周、三周后及整個治療研究期間各自的出血風險模型。前三周的包含所有變量的預后模型具有較高的區分度,C指數為0.79;三周后預測模型的C指數為0.74;整個研究期間預測模型的C指數為0.77。這些表明該模型區分效能尚可。該模型考慮了患者在治療期間病情的變化,出血因素可能發生變化,動態關注了三個時期。該研究將一些危險因素按嚴重程度分類,例如血小板計數、腎功能、年齡等,將臨床特征細化,準確性可能更高。利用Hokusai-VTE研究(比較艾多沙班與華法林的有效性的隨機對照試驗)3期臨床試驗的研究人群外部驗證了EINSTEIN評分,該評分表現尚可,在艾多沙班組的AUC為0.69,而在華法林組的AUC為0.7[29]。然而,由于該模型是在III期臨床試驗的人群基礎上進行的,排除標準較為嚴格,既往評分中與出血顯著相關的一些因素,如肝衰竭、活動性胃十二指腸潰瘍、消化道出血、嚴重腎功能不全、酗酒等是EINSTEIN研究的排除標準,而實際臨床情況卻并非如此。且此評分未提供明確的界值,計算較為復雜,不便于臨床推廣。
3.11 PE-SARD評分
一項來源于法國急性肺栓塞患者隊列人群—BFC-FRANCE注冊中心的關于APE抗凝早期大出血風險預測評分[8],經過按標準納排,最終2754名患者被納入了模型研究。最終的預測模型為包含三個因子:貧血、暈厥、腎功能不全,根據總積分將患者分為低危、中危、高危3個大出血風險類別。從預測表現來看,在研究人群中觀察到的大出血發生率隨著風險組的增加而增加,從低風險組的0.97 %增加到8.93 %,預測中出血風險與實際觀察的出血風險相似。對于模型的內部驗證,PE-SARD評分的區分度較好且校準良好,C指數為0.74。且該評分的敏感性分析顯示各亞組的預測性能相似。該評分是第一個完全使用肺栓塞人群衍生的風險評分,該評分簡潔,所含變量均為二分類變量,但同時也損失了一些連續性變量的信息。作者報告的模型性能良好,但在Poénou等人將其應用在癌癥相關VTE患者中進行外部驗證時,其表現卻不佳,AUC僅為0.5,這提示在癌癥相關VTE抗凝相關大出血方面預測價值有限。該模型究竟預測能力如何尚需更多大規模人群進行外部驗證。
4 房顫患者中建立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及在VTE人群中研究
抗凝治療作為房顫的重要治療之一,抗凝治療相關大出血也是許多臨床醫生關注的問題,因此也開發出了不少抗凝后出血相關的預測模型。模型中涉及到的危險因素主要包含高齡、女性、酗酒、既往出血史、卒中史、貧血、肝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史、抗血小板藥物或非甾體類抗炎藥使用、不穩定INR等,其中一些模型在房顫患者驗證中表現良好。因上述危險因素與VTE抗凝相關大出血危險因素相似,目前也有一些關于這些模型在VTE患者中應用的相關探索研究。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外部驗證結果提示這些模型表現不佳,尚不足以支持其在VTE患者中推廣應用。
Shireman模型來源于美國19875名大于65歲的房顫患者接受華法林抗凝3個月內大出血風險 ,Riva等[]利用華法林至少抗凝3個月的VTE患者中進行了驗證,在預測大出血方面,該模型的AUC僅有0.63[30]。
HAS-BLED評分的建立源于2003-2004年間歐洲心臟調查的大型人口數據庫中的5 333例AF患者1年的隨訪數據[31]。HAS-BLED評分在VTE人群中的驗證表現并不一致。537名在急性期使用華法林治療的VTE患者半年內隨訪中,將HAS-BLED用于評估抗凝治療大出血風險時[32],高危組大出血累積發生率為顯高于非高危組(9.6% VS 1.3%),提示HAS-BLED可有效預測VTE抗凝大出血高危的患者。然而,Riva等[]的在針對使用華法林抗凝治療三個月以上的VTE患者的驗證中,HAS - BLED評分對于抗凝相關大出血風險的預測能力中等,AUC僅為0.6。
HEMORR2HAGES評分來自于2006年Gage等[22]對門診出血風險指數、Kuijer評分和Kearon評分3個評分模型的整合,主要用于評估老年房顫患者抗凝治療后出血風險。Klok等[33]將HEMORR2HAGES應用于急性肺栓塞患者,結果表明在30天隨訪期內,該評分的AUC僅為0.5,提示該評分在急性肺栓塞患者中預測抗凝相關出血表現不佳。
Fang等[34]利用北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醫院中9186名使用華法林進行抗凝治療的房顫患者的研究數據,開發了ARTIA評分。然而,ARTIA在急性肺栓塞患者的預測表現下降不少,Mathonier等[35]在2754例法國急性肺栓塞患者住院期間的數據中進行驗證,ARTIA的C指數僅為0.67,靈敏度為75.6%,特異度為51.2%。
Obrien等[36]利用ORBIT-AF研究的10132名使用口服抗凝藥物(華法林或達比加群)的房顫患者,根據其2年以上的隨訪數據,構建了ORBIT風險評分。在Mathonier等人的急性肺栓塞患者的驗證中,其預測能力一般,ORBIT評分C指數也僅有0.68,特異度僅為43.8%[35]。
5 預測模型外部驗證研究的評價結果
較多研究者對抗凝相關大出血模型進行了外部驗證,但結果顯示,這些預測模型預測效能均不佳,難以應用于臨床。一項比較Landefeld評分、 Beyth評分、Kuijer評分以及RIETE評分對抗凝早期出血風險預測的研究中,盡管每項評分的擬合優度足夠,但四項評分在預測抗凝早期(90天)大出血風險的敏感性較低、陽性預測值較低[37]。
老年人是出血高危人群。在瑞士的一項急性VTE前瞻性隊列的663名老年患者中,應用ORBI評分、Kuijer評分、Kearon評分以及RIETE評分對抗凝治療90天內首次大出血進行預測,結果并不理想,敏感度及陽性預測值均低,且AUC從0.4到0.6不等[38]。
Klok等[33]針對Kuijer評分、RIETE評分、HEMORR2HAGES評分、HAS-BLED評分、ATRIA評分在VTE患者中的預測表現進行了研究。發現5個評分對出血的預測能力都欠佳(AUC:0.57-0.64)。因此,不論是VTE特異性的抗凝大出血風險評分或是房顫抗凝出血評分尚不具備足夠的準確性來預測急性PE患者的抗凝相關大出血。
6 總結
抗凝治療作為靜脈血栓栓塞疾病的基本治療,不論從抗凝藥物或是抗凝策略方面都在逐步發展,力求達到最佳的臨床療效,同時盡可能避免大出血發生。對于抗凝相關大出血的評估,目前對于危險因素的探索已有一些共識,但如何量化并形成一個風險評級,尚未統一觀點。雖然已有不少關于VTE抗凝出血預測模型發表,以及來源于房顫患者開發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風險預測模型在VTE中應用等,這些模型在建立人群中的預測表現尚可,采用外部人群驗證時,但這些模型表現不佳,不具有普適性,目前尚未有被國際指南一致推薦的預測模型。這可能歸因于量表中涉及的變量定義在不同研究之間的差異,這提示后來的研究需要更高的研究質量控制;研究人群的隨訪時間差異,而一些臨床特征或合并癥情況會隨時間變化,大出血風險隨著治療的進行會發生改變,因此關于抗凝治療相關大出血風險評估研究需要關注病情的動態變化。因此,還需更多的研究去優化相關預測模型,通過對上述模型研究的總結,我們發現一些在未來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研究中可以借鑒的,例如出血風險的動態評估、一些綜合指標例如,體能分級的納入、不同抗凝時期預測模型的演變、多中心人群研究等。期望未來能開發出穩定的、普適性強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便于指導臨床抗凝策略,減少抗凝大出血并發癥,減少死亡率,改善患者預后。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靜脈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embolism,VTE)是一種常見的,危害人類健康的血管疾病,包括深靜脈血栓形成和肺動脈栓塞,年發病率可達1-2例/1000人,給全球帶來重大的健康和經濟負擔[1]。抗凝治療是VTE治療的基礎,可有效改善疾病預后[2]。除傳統的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聯合華法林抗凝治療,直接口服抗凝藥物(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DOACs)也不斷發展。然而,抗凝治療也帶來患者出血風險的增加。國際血栓與止血學會(ISTH)將抗凝后出血分為大出血、小出血和臨床相關非大出血三種情況,其中大出血定義為:(1)致死性出血;(2)重要區域或器官中的癥狀性出血:顱內、脊柱內、眼內、腹膜后、關節內、心包內以及出血引起的骨筋膜室綜合征;(3)出血導致血紅蛋白水平下降20 g / L以上,或導致輸注2個或2個以上單位的全血或紅細胞。一旦發生活動性出血,尤其是大出血,患者往往預后不良,致死率和致殘率均明顯升高[3-4]。因此,對于進行抗凝治療的VTE患者,識別并監測抗凝相關大出血的危險因素尤為重要。目前已經有不少研究關注抗凝相關大出血危險因素,并開發出一些出血風險預測模型,從早期的Landefeld評分[5-6]、Nieuwenhuis評分[7],到最近的PE-SARD評分等[8]。本綜述對不同抗凝藥物及不同抗凝階段的大出血風險進行比較、對VTE抗凝治療相關大出血風險預測模型研究進行了總結,期望可以給未來VTE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的發展提供新思路。
1 不同抗凝藥物相關大出血風險比較
1.1 低分子肝素與普通肝素抗凝相關大出血風險
普通肝素作為最傳統的抗凝藥物,主要通過結合抗凝血酶III從而增加對活化的II、IX、X、XI和XII凝血因子的抑制,自發性出血傾向是其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可表現為各種粘膜出血、關節腔積血及傷口出血,其治療過程中需根據嚴密監測的APTT調整劑量。低分子肝素是普通肝素裂解后的產物,分子量低于普通肝素,引起的出血風險小于普通肝素。
多項關于VTE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療效及安全性的隨機對照試驗結果顯示:在普通肝素組中的大出血發生頻率均高于低分子肝素組[9-11];Cochrane的一項meta分析納入了25項在靜脈血栓栓塞患者中比較固定劑量皮下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heparin,LWMH)與調整劑量靜脈或皮下注射普通肝素(unfractionated heparin,UFH)的隨機對照試驗[12],結果表明:初始治療期間使用低分子肝素不僅可以減少靜脈血栓栓塞事件的復發,而且大出血發生率明顯降低(LWMH:65/4333 VS UFH:94/4447,Peto OR:0.69,95%CI:0.50-0.95,P=0.02),DVT患者的亞組分析結果支持上述結論。LWMH固定的給藥劑量和方式提供了更穩定的抗凝血水平,而普通肝素則需根據實驗室監測指標不斷進行劑量調整,這可能導致抗凝血水平的波動,或許是普通肝素出血風險更大的原因。從實際應用角度來說,LWMH每日1-2次皮下注射的給藥途徑更加便捷,患者行動可不受限制,依從行可能更高。并且藥代動力學更具有可預測性,無需實驗室監測和后續劑量調整。
1.2 華法林聯合低分子肝素與DOACs抗凝相關大出血
目前多項研究發現,在VTE患者中使用DOACs藥物,相較于傳統的華法林聯合低分子肝素抗凝方案,可減少抗凝相關大出血的風險。
AMPLFY研究顯示,阿哌沙班組比低分子肝素組大出血風險更低(RR:0.31,95% CI:0.17-0.55,P <0.00)[13]。一項納入了6個有關DOAC與華法林在治療急性癥狀性VTE的療效與安全性的3期臨床試驗的meta分析表明[14],DOAC治療組比華法林治療組在預防復發性VTE方面作用相似,但DOAC治療組比華法林治療組的大出血發生明顯降低(1.1% VS 1.75%,RR:0.61,95%CI:0.45 - 0.83),上述兩個結論在顱內出血、致死性出血、中度腎功能不全、大于75歲的患者亞組中的結果均是一致的。
在需要延長抗凝治療患者中,VKA的使用會帶來出血風險增高。一項Meta分析納入了16個延長使用抗凝藥物(VKA或者DOACs)與安慰劑的在VTE治療相關生存獲益、血栓復發及安全性方面的比較的隨機對照試驗[15],結果表明,相較于對照組(觀察、安慰劑或阿司匹林),VKA組中大出血風險增高(RR 2.67,95%CI:1.28-5.60,P<0.01),而在DOACs組中未見到大出血風險的增高(P>0.5)。
2 延展期抗凝對抗凝相關大出血影響
對于VTE抗凝治療,常規推薦3-6個月抗凝,但對于首次無誘因小腿近端DVT或PE、復發性無誘因的VTE患者、VTE合并活動性腫瘤(“癌癥相關血栓”),國內外多個指南[16-17]推薦進行延展期抗凝。延長抗凝治療可能帶來大出血風險增加,Mai等關于延長抗凝治療效果及安全性的隨機對照試驗的meta分析顯示[15],延長抗凝組較對照組(安慰劑組/觀察組)的大出血風險顯著增加(0.76% VS 0.32%,RR:2.00,95%CI:1.14-3.53,P=0.02;I2=4 0 %)。需要注意的是,是否進行延長抗凝的決策仍取決于對于患者出血及復發性血栓的收益評估,且需定期評估。
3 VTE患者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
3.1 Landefeld評分
Landefeld等[5]開發并驗證了一項抗凝大出血評分表,根據四個條目:開始治療時合并癥的數目、開始治療時的年齡、治療過程中最大PT或APTT與對照組倍數、肝功能異常惡化,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風險等級。該評分在同源的206名患者中進行了驗證,結果表明大出血發生率隨著危險級別增高而增高。該模型四個危險因素包含了治療開始時及治療過程中的情況,這反映了抗凝出血風險的動態評估。從研究數據來看,相較于僅包含治療開始時的兩個危險因素過程的預測模型進行比較,四個危險因素的模型更加準確。然而,該模型在建立的過程中收集的資料較少,可能遺漏一些影響抗凝相關大出血的危險因素,例如住院期間的其他藥物使用情況。暫無相關研究對該模型進行外部驗證。
3.2 Landefeld及Goldman評分
Landefeld等[6]通過回顧性分析562名出院后開始華法林門診治療的患者,構建了評分。條目包括:年齡、腦卒中病史、消化道出血病史、嚴重合并癥(近期有心肌梗死、腎功能不全或嚴重貧血、房顫),同樣將出血風險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風險等級。該評分在驗證組中,低危患者48個月的大出血累積發生率為2%,中危患者為17%,高危患者為63%。在亞組分析中,心臟瓣膜手術組和其他抗凝適應證組(包括二尖瓣病變、房顫、中風、短暫性腦缺血發作、肺栓塞、深靜脈血栓或其他血栓栓塞癥)中,三個風險組別間大出血發生率也有顯著差別。同時,研究中發現發生顱內出血的病例中房顫患者占比64%。考慮到房顫形成的小動脈血栓形成的亞臨床缺血從而可能誘發出血,該評分將房顫作為抗凝相關大出血的危險因素之一。這也提醒臨床醫生,在因房顫進行預防性抗凝治療的患者中的大出血風險尤其是顱內出血可能較高。Nieuwenhuis等[7]在VTE患者的抗凝相關大出血研究中對該模型進行了外部驗證,結果表明此評分并未在驗證人群中識別出大出血患者。
3.3 Nieuwenhuis評分
Nieuwenhuis等[7]在一項比較LMWH 與標準肝素治療急性靜脈血栓栓塞癥的隨機對照試驗中探索了大出血危險因素。研究發現WHO體能狀態分級級別越高,出血風險越大。體表總面積小于2 m2的患者出血風險增加7.3倍。最終納入預測抗凝治療后大出血評分中的內容為:WHO體能分級、既往有出血病史、近期(< 2個月)外傷或手術、體表面積小于2 m2,危險等級劃分為低危、中危和高危。在研究人群中,評分≥5分(高危)的患者中44%的患者發生了嚴重出血,中危組11%,低危組2%。本研究將WHO體能分級納入評估,且發現該指標與抗凝相關大出血的相關性,這為今后的抗凝相關大出血的獨立危險因素研究提供了一個思路。
3.4 OBRI評分
Beyth等[]根據口服華法林抗凝的565名門診患者,建立了含有4個危險因素的大出血風險評分:年齡>65歲、胃腸道出血史、卒中史和存在一種或多種特定的合并癥(近期心肌梗死、腎功能不全、重度貧血或糖尿病),將風險劃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等級。在模型建立人群中的C指數為0.72。在外部驗證中,OBRI評分C指數為0.78,這說明該模型預測效能中等偏上。但由于該模型納入了不同原因服用華法林的患者,并未區分具體病種,這使OBRI評分在不同疾病中應用受限。
3.5 Kuijer評分
Kuijer等[19]利用一項比較VTE患者使用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進行初始治療的優劣的隨機對照試驗,構建了抗凝出血風險預測評分。該簡化風險評分為包含年齡、性別、惡性腫瘤三個因子;按風險等級劃分為低中高危三個等級。在模型建立人群中的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為0.82,21%患者被列為高危,他們發生抗凝相關大出血頻率為14%。在驗證人群中,20%的患者被kuijer出血風險預測評分識別為高風險,而這些患者的大出血頻率為7%,這說明相比于模型建立人群中預測能力所有下降。該評分在既往已經明確的抗凝后出血風險危險因素基礎上選擇了3個簡單、易獲得的臨床變量,簡單易操作。然而,在Riva等[] 針對Kuijer評分的驗證研究中,使用華法林治療的VTE患者組AUC僅為0.51。
3.6 Kearon評分
Kearon等[21]在研究低強度華法林治療(目標INR:1.3-1.9)與常規強度華法林治療(目標INR:2.0-3.0)療效及安全性的過程中,提出抗凝后大出血相關危險因素包括:年齡≥65歲、既往卒中、既往消化性潰瘍病、既往消化道出血、腎損傷、貧血、血小板減少、肝病、糖尿病以及抗血小板治療。大出血頻率隨著入組時已存在的危險因素數目增加而增加。Gage等[22]為老年房顫患者抗凝出血風險制定了分級方案,并在美國全國心房顫動登記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Atrial Fibrillation,NARF)隊列人群進行了外部驗證。結果顯示,在NARF隊列使用華法林抗凝的患者中,Kearson評分的C指數僅為0.66,這說明該評分的預測準確度較低。
3.7 RIETE評分
RIETE隊列是一個由西班牙、法國、意大利、以色列、阿根廷等國家合作構建的多中心、前瞻連續隊列,該隊列由經客觀檢查確診的癥狀性急性VTE患者構成。Ruiz等[23]在RIETE隊列中隨機抽取了67%患者作為模型建立樣本,另33%患者作為內部驗證樣本。該模型指標包括近期出血史、血肌酐>106 mmol/L、貧血、年齡>75歲、基線時具有腫瘤診斷、基線時PE診斷。同樣劃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個風險等級。在驗證隊列中,低危患者發生大出血事件的概率為0.1 %;中危患者發生大出血概率為2.8 %,高危組大出血風險概率為6.2%。三個風險等級組間大出血發生率有統計學差異。該評分通過抽取隊列研究人群,相對于臨床隨機對照試驗中選取的人群,更接近于真實世界情況下VTE患者臨床特征和疾病轉歸情況。Tchen等[24]后來在使用DOACs的患者中(未特定病種)對RIETE進行了驗證,其AUC為0.638,這說明預測能力較低。
3.8 ACCP評分
美國胸科醫師學會(ACCP)基于既往研究,總結了抗凝治療大出血風險危險因素,并進行了低危、中危、高危的風險分級。發布在第9版《VTE抗栓指南:抗血栓治療與血栓預防》中[25]。該指南建議針對一些特定患者,如血栓危險因素暫時不能消除的近端小腿DVT、無誘因的首次小腿近端或孤立遠端DVT、無誘因的復發性VTE的患者,在評估是否進行延展期抗凝治療時需同時評估抗凝相關大出血的風險。Riva等[20]使用ACCP評分在急性肺栓塞患者隊列研究中進行了前瞻性驗證,該評分在抗凝治療六個月內預測大出血準確度低,AUC僅為0.59。Palareti等[26]在2263名進行了延展期抗凝的VTE患者中驗證了ACCP評分,結果也表明,ACCP評分在低危、中危、高危三個出血風險組別中的C指數僅有0.50-0.56。上述研究均表明,ACCP評分不能準確預測延展期抗凝患者的大出血風險。
3.9 VTE-BLEED評分
Klok等[27]在比較達比加群酯和華法林抗凝的RE-COVER 和RE-COVER II試驗中建立了VTE-BLEED評分:活動性癌癥、具有未控制的高血壓的男性、貧血、出血史、>60歲。根據分數劃分為低危和高危兩個風險等級。在達比加群酯衍生人群中,該評分表現良好,AUC為0.72。同時從抗凝穩定期(30天-6個月)表現來看,達比加群酯組的AUC為0.7;華法林組的AUC為0.78。在以上組別中,該評分的區分能力較高,高危患者的大出血風險為低危患者的5-7倍。同時作者還進行了達比加群酯試驗組中急性肺栓塞亞組和深靜脈血栓亞組的驗證,其表現相似。VTE-BLEED評分特別關注了抗凝延展期大出血風險,期望可在抗凝治療3 - 6個月后延長治療的決策過程中提供幫助。
3.10 EINSTEIN評分
Di Nisio等[28]利用EINSTEIN DVT和EINSTEIN PE研究(利伐沙班與依諾肝素和VKA組成的標準療法的比較試驗)DVT或PE患者的大出血情況,探索了大出血的獨立危險因素,衍生出在治療前三周、三周后及整個治療研究期間各自的出血風險模型。前三周的包含所有變量的預后模型具有較高的區分度,C指數為0.79;三周后預測模型的C指數為0.74;整個研究期間預測模型的C指數為0.77。這些表明該模型區分效能尚可。該模型考慮了患者在治療期間病情的變化,出血因素可能發生變化,動態關注了三個時期。該研究將一些危險因素按嚴重程度分類,例如血小板計數、腎功能、年齡等,將臨床特征細化,準確性可能更高。利用Hokusai-VTE研究(比較艾多沙班與華法林的有效性的隨機對照試驗)3期臨床試驗的研究人群外部驗證了EINSTEIN評分,該評分表現尚可,在艾多沙班組的AUC為0.69,而在華法林組的AUC為0.7[29]。然而,由于該模型是在III期臨床試驗的人群基礎上進行的,排除標準較為嚴格,既往評分中與出血顯著相關的一些因素,如肝衰竭、活動性胃十二指腸潰瘍、消化道出血、嚴重腎功能不全、酗酒等是EINSTEIN研究的排除標準,而實際臨床情況卻并非如此。且此評分未提供明確的界值,計算較為復雜,不便于臨床推廣。
3.11 PE-SARD評分
一項來源于法國急性肺栓塞患者隊列人群—BFC-FRANCE注冊中心的關于APE抗凝早期大出血風險預測評分[8],經過按標準納排,最終2754名患者被納入了模型研究。最終的預測模型為包含三個因子:貧血、暈厥、腎功能不全,根據總積分將患者分為低危、中危、高危3個大出血風險類別。從預測表現來看,在研究人群中觀察到的大出血發生率隨著風險組的增加而增加,從低風險組的0.97 %增加到8.93 %,預測中出血風險與實際觀察的出血風險相似。對于模型的內部驗證,PE-SARD評分的區分度較好且校準良好,C指數為0.74。且該評分的敏感性分析顯示各亞組的預測性能相似。該評分是第一個完全使用肺栓塞人群衍生的風險評分,該評分簡潔,所含變量均為二分類變量,但同時也損失了一些連續性變量的信息。作者報告的模型性能良好,但在Poénou等人將其應用在癌癥相關VTE患者中進行外部驗證時,其表現卻不佳,AUC僅為0.5,這提示在癌癥相關VTE抗凝相關大出血方面預測價值有限。該模型究竟預測能力如何尚需更多大規模人群進行外部驗證。
4 房顫患者中建立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及在VTE人群中研究
抗凝治療作為房顫的重要治療之一,抗凝治療相關大出血也是許多臨床醫生關注的問題,因此也開發出了不少抗凝后出血相關的預測模型。模型中涉及到的危險因素主要包含高齡、女性、酗酒、既往出血史、卒中史、貧血、肝腎功能不全、惡性腫瘤史、抗血小板藥物或非甾體類抗炎藥使用、不穩定INR等,其中一些模型在房顫患者驗證中表現良好。因上述危險因素與VTE抗凝相關大出血危險因素相似,目前也有一些關于這些模型在VTE患者中應用的相關探索研究。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外部驗證結果提示這些模型表現不佳,尚不足以支持其在VTE患者中推廣應用。
Shireman模型來源于美國19875名大于65歲的房顫患者接受華法林抗凝3個月內大出血風險 ,Riva等[]利用華法林至少抗凝3個月的VTE患者中進行了驗證,在預測大出血方面,該模型的AUC僅有0.63[30]。
HAS-BLED評分的建立源于2003-2004年間歐洲心臟調查的大型人口數據庫中的5 333例AF患者1年的隨訪數據[31]。HAS-BLED評分在VTE人群中的驗證表現并不一致。537名在急性期使用華法林治療的VTE患者半年內隨訪中,將HAS-BLED用于評估抗凝治療大出血風險時[32],高危組大出血累積發生率為顯高于非高危組(9.6% VS 1.3%),提示HAS-BLED可有效預測VTE抗凝大出血高危的患者。然而,Riva等[]的在針對使用華法林抗凝治療三個月以上的VTE患者的驗證中,HAS - BLED評分對于抗凝相關大出血風險的預測能力中等,AUC僅為0.6。
HEMORR2HAGES評分來自于2006年Gage等[22]對門診出血風險指數、Kuijer評分和Kearon評分3個評分模型的整合,主要用于評估老年房顫患者抗凝治療后出血風險。Klok等[33]將HEMORR2HAGES應用于急性肺栓塞患者,結果表明在30天隨訪期內,該評分的AUC僅為0.5,提示該評分在急性肺栓塞患者中預測抗凝相關出血表現不佳。
Fang等[34]利用北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醫院中9186名使用華法林進行抗凝治療的房顫患者的研究數據,開發了ARTIA評分。然而,ARTIA在急性肺栓塞患者的預測表現下降不少,Mathonier等[35]在2754例法國急性肺栓塞患者住院期間的數據中進行驗證,ARTIA的C指數僅為0.67,靈敏度為75.6%,特異度為51.2%。
Obrien等[36]利用ORBIT-AF研究的10132名使用口服抗凝藥物(華法林或達比加群)的房顫患者,根據其2年以上的隨訪數據,構建了ORBIT風險評分。在Mathonier等人的急性肺栓塞患者的驗證中,其預測能力一般,ORBIT評分C指數也僅有0.68,特異度僅為43.8%[35]。
5 預測模型外部驗證研究的評價結果
較多研究者對抗凝相關大出血模型進行了外部驗證,但結果顯示,這些預測模型預測效能均不佳,難以應用于臨床。一項比較Landefeld評分、 Beyth評分、Kuijer評分以及RIETE評分對抗凝早期出血風險預測的研究中,盡管每項評分的擬合優度足夠,但四項評分在預測抗凝早期(90天)大出血風險的敏感性較低、陽性預測值較低[37]。
老年人是出血高危人群。在瑞士的一項急性VTE前瞻性隊列的663名老年患者中,應用ORBI評分、Kuijer評分、Kearon評分以及RIETE評分對抗凝治療90天內首次大出血進行預測,結果并不理想,敏感度及陽性預測值均低,且AUC從0.4到0.6不等[38]。
Klok等[33]針對Kuijer評分、RIETE評分、HEMORR2HAGES評分、HAS-BLED評分、ATRIA評分在VTE患者中的預測表現進行了研究。發現5個評分對出血的預測能力都欠佳(AUC:0.57-0.64)。因此,不論是VTE特異性的抗凝大出血風險評分或是房顫抗凝出血評分尚不具備足夠的準確性來預測急性PE患者的抗凝相關大出血。
6 總結
抗凝治療作為靜脈血栓栓塞疾病的基本治療,不論從抗凝藥物或是抗凝策略方面都在逐步發展,力求達到最佳的臨床療效,同時盡可能避免大出血發生。對于抗凝相關大出血的評估,目前對于危險因素的探索已有一些共識,但如何量化并形成一個風險評級,尚未統一觀點。雖然已有不少關于VTE抗凝出血預測模型發表,以及來源于房顫患者開發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風險預測模型在VTE中應用等,這些模型在建立人群中的預測表現尚可,采用外部人群驗證時,但這些模型表現不佳,不具有普適性,目前尚未有被國際指南一致推薦的預測模型。這可能歸因于量表中涉及的變量定義在不同研究之間的差異,這提示后來的研究需要更高的研究質量控制;研究人群的隨訪時間差異,而一些臨床特征或合并癥情況會隨時間變化,大出血風險隨著治療的進行會發生改變,因此關于抗凝治療相關大出血風險評估研究需要關注病情的動態變化。因此,還需更多的研究去優化相關預測模型,通過對上述模型研究的總結,我們發現一些在未來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研究中可以借鑒的,例如出血風險的動態評估、一些綜合指標例如,體能分級的納入、不同抗凝時期預測模型的演變、多中心人群研究等。期望未來能開發出穩定的、普適性強的抗凝相關大出血預測模型,便于指導臨床抗凝策略,減少抗凝大出血并發癥,減少死亡率,改善患者預后。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