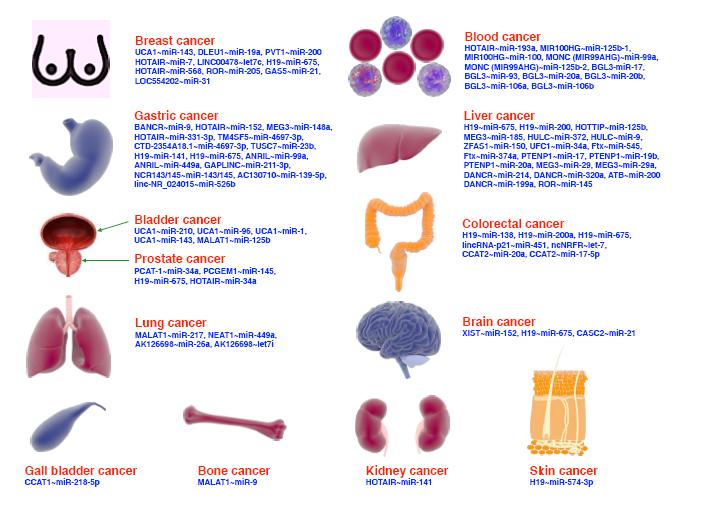失眠是當前人類健康面臨的重大挑戰,失眠的明確診斷對于健康的評估十分重要。世界生物精神病學學會聯合會睡眠障礙工作組就基于主觀主訴的評定量表及生物標志物在失眠診斷中的價值達成共識。本文在該共識的基礎上,對其進行解讀,旨在為臨床實踐與科學研究提供相關幫助。
引用本文: 馬瀾, 時晶. 診斷失眠的潛在指標:WFSBP共識聲明解讀.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4, 24(7): 845-852. doi: 10.7507/1672-2531.202309129 復制
失眠是人類健康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2023年,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2023中國健康睡眠白皮書》顯示,中國人群平均睡眠時間為7.23小時,但睡眠質量普遍較低,睡眠障礙比例高達38.2%。睡眠情況與人體的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密切相關,故對失眠的明確診斷具有重要意義[1]。目前,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WHO)、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和美國睡眠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AASM)對失眠的診斷主要基于患者主觀表達的臨床癥狀,如:難以入睡、睡眠難以維持、睡眠少、睡眠質量差等。盡管基于主觀表述的評定量表和其他心理測量手段或有相當大的診斷有效性,但部分指南開始推薦將生物標志物用于失眠的診斷[2,3]。然而,目前關于生物標志物的敏感性、特異性等多方面的證據非常有限,無法確定將其作為診斷失眠的生物標志物的有效性。基于此,世界生物精神病學學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WFSBP)睡眠障礙工作組就心理測驗和生物標志物在失眠診斷中的價值達成共識。本文通過對“診斷失眠的潛在指標:WFSBP共識聲明”進行解讀,以期為失眠的臨床診斷應用與研究提供參考。
1 方法
WFSBP睡眠障礙工作組由在失眠研究/臨床領域具有一定學術造詣的專家組成。為建立相對完整的診斷體系,睡眠障礙工作組根據研究中所使用的評價指標,將失眠診斷的相關性分為A、B、C、D四個等級(表1),結合評價指標數值的大小,將診斷準確性分為1、2、3、4四個等級(表2)。由此將診斷相關性和診斷準確性的等級結合起來,為每項研究建立一個診斷分級指標,從而評估心理測驗量表與生物標志物診斷失眠的價值。
2 結果
2.1 評估失眠的量表和問卷
諸多量表和問卷均可用于診斷失眠,其中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AIS);全球睡眠評估問卷(global sleep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GSAQ);睡眠50問卷(SLEEP-50 questionnaire,SLEEP-50Q);簡要失眠問卷(brief insomnia questionnaire,BIQ)是診斷效能較高的五個量表,診斷失眠的敏感性(71%~93%)、特異性(57%~98.9%)、陽性預測值(86%~96.7%)、陰性預測值(88.7%~92%)以及ROC-AUC(0.72~0.86)五個方面均較高。除了診斷的有效性外,Cronbach的alpha值(0.83~0.90)和重測信度(0.78~0.89)也較高,表明上述五種量表具有較強的內部一致性。通過對比發現,這五個量表和問卷是評估失眠的有效工具,其中三個量表診斷等級為A1,兩個量表診斷等級為A2(表3)。
PSQI的內容相對冗長,其評級程序較為復雜,但是,由于它具備全面性和心理測量特性,在目前的研究中被廣泛應用。AIS由8個條目組成,易于使用和評分;雖然AIS沒有提供除失眠以外的其他睡眠障礙的信息,但由于它的簡單性和易診斷性,也被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廣泛使用。BIQ的內容也相當冗長,評估難度較大,但是,復雜的設計程序卻使其成為一個更加有價值的評估工具,尤其是對大型流行病學研究而言。SLEEP-50Q主要用于評估睡眠障礙,涉及的內容主要與失眠有關,所以它一般只用于失眠的人群研究中。GSAQ對原發性失眠的敏感性、特異性和AUC相對較低,而對除失眠以外的睡眠障礙的敏感性、特異性和AUC普遍較高,表明GSAQ更適宜于評估除失眠以外的睡眠障礙。
2.2 評估睡眠功能失調性信念與態度量表
認知過程在失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了量化與睡眠相關的認知,Morin等[9]設計了睡眠功能失調性信念和態度量表(dysfunction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about sleep scale,DBAS),該量表共包含30個項目。同時,也出版了簡短版本,即DBAS-16[10]。總的來說,所有版本的DBAS均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可以將失眠患者和睡眠良好者區別開來。但DBAS對失眠患者和健康人的鑒別準確率相對較高,而DBAS-16是一種簡便、有效的評估工具,可用于普遍的失眠群體。雖然其他類型的睡眠障礙中也存在DBAS評分增加的情況,如不安腿綜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RLS)或伴有睡眠呼吸暫停的RLS,但這并不影響DBAS評分與失眠嚴重程度呈正相關的事實。除DBAS外,其他與認知過程相關的量表對失眠的診斷也具有較好的有效性,如格拉斯哥思想內容量表(Glasgow content of thoughts inventory,GCTI)和格拉斯哥睡眠努力度問卷(Glasgow sleep effort scale,GSES)(表4)。實際上,GCTI量表主要用于認知心理學領域,側重于評估睡眠前的認知活動,而不是用于評估失眠本身;因此,它在日常臨床實踐中應用較為有限。相同的是,GSES量表也并不是為了評估失眠,而是作為一種自我控制睡眠的措施而設計的,所以更適宜于由心理原因導致的失眠。
2.3 人格特征評估量表
心理測量工具和生物測量工具診斷失眠的效能評分見表5。一項基于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驗(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的研究發現[17],與睡眠良好者相比,失眠癥患者出現至少一個病理量表升高的情況更頻繁,其中,失眠癥患者的抑郁、精神衰弱、癔病、疑病癥臨床量表得分較高,表明抑郁、沉思、焦慮等特征多為失眠癥患者的人格特征。這種消極的情緒引起心理生理上的變化或許是導致失眠產生和持續惡性循環的原因。Van de Laar等[18]通過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即失眠癥患者的癥狀常伴隨著抑郁、精神衰弱、癔病、疑病癥等臨床量表評分的增高而增加。但是,還需要進一步的縱向研究來探索人格特征和失眠之間的關系,尤其長期失眠是否會導致人格的改變。
五大人格特征包括神經質、外向型、開放型、宜人型、盡責型。有研究對失眠者的人格特征進行觀察發現,無論對失眠進行主觀或還是客觀評估,高神經質評分是預測失眠的有效因素[19];然而,神經質與失眠并沒有被發現具有確定的診斷性聯系[20]。在這五大人格特征中,外向型和情感積極型人格特征人群的睡眠質量良好[21, 22]。隨著時間的推移,責任心低與睡眠質量下降有較弱的相關性[20]。
除上述MMPI和五大人格特征外,其他關于人格特征的研究表明,慢性失眠癥患者比健康對照組人群更追求完美主義[23]。無論橫斷面研究還是縱向研究都證實了完美主義與睡眠不佳之間存在顯著聯系性,為避免睡眠不佳的報告具有主觀性,研究通過多導睡眠監測儀來測量睡眠情況,結果亦然[24,25]。但是,現有數據有限,還無法完全確定完美主義人格的測量方法對失眠癥的診斷是否有影響。
2.4 多導睡眠監測和睡眠腦電圖
多導睡眠監測是最常用的睡眠監測手段,為了闡明多導睡眠監測診斷失眠的臨床價值,Regen等[26]進行了一項包括582例慢性原發性失眠癥患者和485名良好睡眠人群的Meta分析,結果發現失眠癥患者和睡眠良好人群雖然在多方面存在差異,如前者睡眠效率降低,睡眠潛伏期增加,總睡眠時間減少,覺醒次數增加,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動睡眠減少,覺醒時間增加;但兩組間總睡眠時間的差異僅為25 min;此外,所有表示睡眠量減少的指標差異普遍較小,差異最明顯的是睡眠效率和慢波睡眠持續時間(診斷分級B3)。但是,從總睡眠時間數據可發現,兩組主觀描述總睡眠時間的差異卻比較明顯,平均相差2小時。因此,對于失眠癥的診斷準確性來說,多導睡眠監測的上述指標還屬于較弱水平。因此,關于多導睡眠監測診斷失眠的其他證據力度更強的指標值得進一步探索。
多導睡眠監測中的循環交替模式(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CAP)是在非快動眼睡眠期多導睡眠監測出現的一種呈周期性的腦電變化,它以一系列明顯突出于背景的短暫性腦電事件的發放為特點,這些腦電事件重復出現的間隔時間為20~40秒[27]。CAP的變化標志著覺醒波動,數值越大,表示睡眠越紊亂和睡眠質量越差。Chouvarda等[28]的研究表明,通過CAP的改變來區分失眠癥患者和睡眠良好人群具有高效的準確性,表明CAP是診斷失眠的潛在可行途徑(診斷等級A1)。
睡眠腦電圖可以記錄睡眠期間的腦電波清空。Spiegelhalder等[29]發現原發性失眠人群在非快速眼動睡眠期間的快速頻率波段(sigma波和beta波)的數量增加,表明存在大腦皮層的覺醒與亢奮(診斷分級B3)。Colombo等[30]通過高密度腦電圖檢測到失眠癥患者在清醒時、靜息狀態下的腦電圖也存在beta波數量增加的情況,該結果表明單憑快速頻率波段尚不能說明對失眠癥的準確診斷具有意義。Riedner等[31]發現慢性失眠癥患者的整夜非快速眼動睡眠腦電圖的高頻腦電活動功率(>16 Hz)比對照組更強,分布在整個頭皮,表明即使在深睡眠階段,慢性失眠癥患者仍可能存在高喚醒狀態。Buysse等[32]發現,與對照組相比,失眠癥患者僅在第一個非快速眼動睡眠期存在高喚醒狀態(高頻腦電活動功率18~40 Hz)。然而,Svetnik等[33]卻認為失眠癥患者睡眠時的高喚醒狀態可能與受試者的性別有關,其中女性受試者出現上述情況的可能性更大。與此相反,Schwabedal等[34]發現,男性失眠癥患者在睡眠喚醒時的alpha波頻率與清醒時相似,但低于對照組,表明男性失眠癥患者在睡眠時也可能存在高喚醒狀態。總之,這些研究數據均不足以說明診斷失眠癥的有效性(診斷分級均為D)。
2.5 神經影像學
神經放射學和核醫學技術早已被用于研究失眠的診斷。有研究使用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對5名失眠患者和4名健康人進行檢查[35],發現失眠患者的額葉、頂葉和枕部大腦區域以及基底神經節在非快速眼動睡眠存在血流量減少,且該結果具有較高的診斷效度(診斷分級B1)。
18F-氟代脫氧葡萄糖正電子發射計算機體層攝影(18F-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18F-FDG-PET)可被用于評估大腦代謝模式。Nofzinger等[36]比較了7名失眠患者和20名健康人在非快速眼動睡眠和清醒期間的18F-FDG-PET結果,與健康對照比較,失眠患者的大腦從清醒到非快速眼動睡眠期間18FDG代謝降低的幅度更小,尤其是在上行網狀激活系統、情緒調節相關區域(杏仁核、海馬體和前扣帶皮層)和認知相關區域(前額葉皮層)。該結果在后續的一項包含44名失眠癥患者和40名健康對照人群的研究中得以驗證[37](診斷分級D)。研究進一步發現涉及意識的大腦區域可能參與了覺醒-睡眠過渡的感知[38],這導致大腦代謝模式在失眠患者中可能具有特征性的改變[39]。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診斷失眠癥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特定任務中,另一類是在靜息狀態下。一項與任務相關的研究調查了22名失眠癥患者和38名健康對照人群,結果表明失眠癥患者與睡眠刺激相關的杏仁核反應增加[40]。在執行認知任務期間,額葉區域的血流活動減少[41-43](診斷分級B1)。
許多研究對失眠癥中的靜息狀態功能連通性(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C)進行了觀察,但是結果均不太一致。Leerssen等[44]報告了65名失眠癥患者海馬前體和前額皮質靜息狀態功能連通性增加(診斷分級B1),而Regen等[26]在20名失眠癥患者和20名健康對照人群中卻未發現顯著的組間差異,但是RSFC的一些其他數據與睡眠效率和睡眠潛伏期存在弱相關(診斷分級C3)。
Meta分析報告稱,目前不同研究中源于失眠癥的大腦影像學改變尚缺乏一致性[45]。結合現有證據可知上述各種指標對失眠的診斷具有一定有效性,然而,這些指標的不一致性和多樣性尚不能建立神經影像學的共同標準。究其原因,或許是研究涉及的樣本量太小,而探索性數據分析策略限制了研究的價值,導致了較高出現假陰性和假陽性結果的風險。
2.6 活動記錄儀
活動記錄儀是一種監測人體休息-活動周期的非侵入性手段。在睡眠醫學中用于評估晝夜節律、睡眠-覺醒節律和休息時間[46, 47]。目前,有兩項大型研究報告了活動記錄儀對失眠癥診斷的準確性,認為活動記錄儀具有比較好的診斷有效性,能夠區分失眠者和正常睡眠者[48, 49](診斷分級為A1和A2)。但是,其他許多關于失眠癥活動記錄儀的研究只報告了失眠癥患者與睡眠良好人群兩組間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并未提及具體的睡眠參數及其敏感性、特異性和預測值的臨界值。這便意味著活動記錄儀缺乏檢測睡眠情況的軟件算法標準,導致活動記錄儀可能會將躺在床上不睡覺的情況誤測為睡眠低效率。雖然,活動記錄儀對于失眠的診斷潛力較高,但是其應用還需進一步討論。
2.7 皮膚電傳導
皮膚電導水平(skin conductance level,SCL)是自主神經系統的一個心理/生理指標,代表了對情緒刺激反應的交感神經活動。在一項關于清醒時間的習慣性實驗研究中,Broman和Hetta[50]發現失眠癥患者與健康人對比,雖然SCL增加,但習慣性的重復指標很少,表明SCL對失眠癥的診斷敏感性偏低(診斷分級A4)。
2.8 心率和心率變異性
精神生理壓力可引起睡眠覺醒,同時導致心率(heart rate,HR)增加和心率變異(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降低。研究發現,在睡眠前和入睡早期會出現HR增加情況,但是該指標對失眠癥的診斷準確性水平在不同研究中的級別從B1至B3不等[51-53](診斷分級B1至B3)。HRV,即連續心動周期之間的時間變異性,通常指RR(R波到R波)間隔。在清醒或睡眠期間,心電圖所記錄的RR間隔隨著自主神經系統的功能改變而有所不同[54]。光譜分析顯示了RR間隔在三個等級頻率下對應的自主神經系統功能:高頻率(high frequency, HF),反映副交感神經輸入;低頻率(low frequency,LF),依賴于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輸入;極低頻率(very low frequency,VLF),受副交感神經的影響。LF/HF比值是評估交感神經平衡的一個指標[55]。Bonnet和Arand[51]在客觀診斷失眠癥的患者中發現,LF增加,HF減少,該結果反映了失眠癥患者交感神經平衡的變化情況。有研究觀察了失眠癥患者與健康對照者在靜息狀態、睡眠開始前后或特定睡眠階段的HRV,結果發現失眠者的HRV有兩種模式:要么低頻或高頻,且沒有顯著差異;要么高頻趨于降低,表明副交感神經張力降低[56];或低頻增加,表明交感神經活動增加[52];這些現象主要表現在睡眠開始前和睡眠的第二階段[53]。總之,睡眠前后HR的增加或許可被認為是診斷失眠癥的一個潛在指標(診斷分級B1至B3)。然而,根據上述研究結果,HRV尚不能作為診斷失眠的標志(診斷分級B4)。
2.9 體溫調節
溫度調節是指核心體溫和皮膚溫度的晝夜節律[57, 58]。健康的睡眠常伴隨著夜間核心體溫的下降。覺醒-睡眠和溫度節律之間不同步可能代表著某些特定類型的失眠[59]。研究顯示,老年人失眠與夜間核心體溫升高有關[60]。Gradisar等[61]指出,失眠癥患者與正常睡眠者相比,其核心體溫升高,但診斷準確性較低(診斷分級B3)。
2.10 耗氧率
總耗氧量作為全身代謝率的替代指標,可以評估身體的生理活動。Chapman等[62]指出,失眠癥患者的代謝率在白天和整個夜間都略有升高。這與高喚醒模型相一致,即覺醒時間和睡眠時間代謝率也升高。代謝率的增高不僅出現在客觀診斷的失眠患者中,在主觀感覺性失眠患者中也存在較小程度的升高(診斷分級B3和B4)。因此,總耗氧量也可能是客觀診斷失眠的潛在標志物。
2.11 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
目前關于失眠癥患者皮質醇水平變化的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63],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失眠癥患者在晚上和失眠前半夜的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和皮質醇水平顯著升高[64, 65](診斷分級B1),但其他的研究則沒有發現這個現象[66, 67]。不同嚴重程度的失眠或許是差異產生的原因。有研究觀察到總睡眠時間(total sleep time,TST)縮短的失眠癥患者在晚上的前半段和早上都表現出ACTH和皮質醇濃度升高;相比之下,TST正常或TST僅輕度減少的人群皮質醇水平并沒有改變[68, 69]。
有研究在失眠癥患者早晨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活動中觀察到不一致的結果,即失眠癥患者醒后的唾液皮質醇減少,或與正常睡眠者的皮質醇水平相當[66, 67, 70],表明較低的醒后皮質醇濃度與較低的睡眠質量和相關。有研究卻發現較短的客觀TST與早晨醒后皮質醇水平升高有關[69]。然而,通過地塞米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試驗證實失眠癥患者的HPA軸并沒有過度活躍[71]。可能慢性失眠一般是輕度至中度的睡眠時間縮短,因此,在這期間,出現適度的HPA軸活動屬于正常。
2.12 褪黑素
褪黑素是晝夜睡眠-覺醒節律的重要調節劑。夜間黑暗依賴的褪黑素水平的上升誘導了睡眠傾向,也參與前半夜以慢波睡眠為優勢的生理睡眠結構[67]。此外,褪黑素被認為可以調節HPA軸活動的晝夜節律[71]。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失眠癥患者的褪黑素在傍晚開始上升,在夜間的峰值較低,對失眠癥的診斷具有較好的效能[72](診斷分級B2)。
2.13 炎癥標志物
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介素6(interleukin 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是典型的炎癥標志物。有研究顯示,失眠與CRP中度水平升高有關,與IL-6和TNF-a水平無關[73]。與非失眠患者或非長期失眠患者相比,6年失眠病史的患者的CRP水平升高(診斷分級D)[74]。
2.14 神經可塑性標志物
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是一類具有營養神經作用的蛋白,在腦內和外周血清均有分布,對神經元的生長、發育、誘導分化及突觸連接具有調節功能。突觸穩態調節和大腦記憶鞏固通常發生在睡眠期間,表明睡眠不足可能與神經可塑性存在相關性。因此,隨著研究的進展,BDNF與失眠的聯系也逐漸被關注。研究顯示,對于抑郁癥出現失眠的患者,當抑郁癥控制后,存在失眠的患者的血清BDNF水平低于健康對照組[75]。另有研究也發現,失眠癥患者的血清BDNF水平比健康睡眠者更低,說明血清BDNF或許是診斷失眠癥的生物標志物[64](診斷分級A1)。在另一項研究中發現,低BDNF水平是診斷短睡眠時間性失眠和正常睡眠時間性失眠的生物標志物(診斷分級B1),而且在失眠和睡眠時間縮短的人群中,低BDNF水平和認知表現差之間存在關聯性[76]。可見,BDNF對于失眠的診斷具有一定的潛在價值。
3 結論
失眠、睡眠信念與態度的量表和問卷是基于既定的截止分數來作為診斷失眠的金標準,這些量表和問卷在至少一項研究中,診斷分級為A1,診斷效能屬于“極好”。MMPI作為一種診斷失眠的評估工具,其診斷效能屬于“好”,盡管低于前述失眠、睡眠信念與態度的量表和問卷,但是其診斷潛力相對較好。此外,對失眠具有高效診斷性能,并可被視為潛在生物標志物的指標有活動記錄儀,血清BDNF水平,CAP;其次是心率增加(入睡前或入睡后早期)、神經影像學改變(在睡眠和/或清醒時大腦部分回路高度激活)。褪黑素水平對于失眠的診斷效能屬于“一般”,而HPA軸則屬于“不好”。因此,在沒有更高證據的研究報告之前,一般不推薦將用褪黑素水平和HPA軸的激素水平來診斷、評估失眠。
對于其他測量指標,盡管失眠患者的核心體溫的升高具有一定的診斷潛力,但是測量核心體溫的過程不適合臨床目的。耗氧量也對失眠顯示出了一定的診斷能力,但不適用于只有主觀主訴的失眠癥患者,因此,這種方法的臨床應用不切實際。對SCL而言,該指標還未顯示出較好的診斷準確性。如前所述,CRP與慢性失眠有關,而慢性失眠常伴隨壓力與焦慮的出現,壓力與焦慮對CRP的影響尚未清楚,因此,CRP對于診斷失眠的用途僅處于探索階段。
因為成本效益和程序復雜程度,上述部分診斷失眠的潛在指標(如核磁共振或需要采血的指標)的廣泛性和適用性受限。為提供敏感性、特異性都比較高的指標作為失眠的診斷標準,還有諸多工作需要進行:如進行數量足夠多的研究來重復評估診斷偏倚;設計普遍接受的方法來評估一項研究的有效性;對指標設立適當的診斷截點等。
失眠是人類健康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2023年,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2023中國健康睡眠白皮書》顯示,中國人群平均睡眠時間為7.23小時,但睡眠質量普遍較低,睡眠障礙比例高達38.2%。睡眠情況與人體的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密切相關,故對失眠的明確診斷具有重要意義[1]。目前,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WHO)、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和美國睡眠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AASM)對失眠的診斷主要基于患者主觀表達的臨床癥狀,如:難以入睡、睡眠難以維持、睡眠少、睡眠質量差等。盡管基于主觀表述的評定量表和其他心理測量手段或有相當大的診斷有效性,但部分指南開始推薦將生物標志物用于失眠的診斷[2,3]。然而,目前關于生物標志物的敏感性、特異性等多方面的證據非常有限,無法確定將其作為診斷失眠的生物標志物的有效性。基于此,世界生物精神病學學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WFSBP)睡眠障礙工作組就心理測驗和生物標志物在失眠診斷中的價值達成共識。本文通過對“診斷失眠的潛在指標:WFSBP共識聲明”進行解讀,以期為失眠的臨床診斷應用與研究提供參考。
1 方法
WFSBP睡眠障礙工作組由在失眠研究/臨床領域具有一定學術造詣的專家組成。為建立相對完整的診斷體系,睡眠障礙工作組根據研究中所使用的評價指標,將失眠診斷的相關性分為A、B、C、D四個等級(表1),結合評價指標數值的大小,將診斷準確性分為1、2、3、4四個等級(表2)。由此將診斷相關性和診斷準確性的等級結合起來,為每項研究建立一個診斷分級指標,從而評估心理測驗量表與生物標志物診斷失眠的價值。
2 結果
2.1 評估失眠的量表和問卷
諸多量表和問卷均可用于診斷失眠,其中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AIS);全球睡眠評估問卷(global sleep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GSAQ);睡眠50問卷(SLEEP-50 questionnaire,SLEEP-50Q);簡要失眠問卷(brief insomnia questionnaire,BIQ)是診斷效能較高的五個量表,診斷失眠的敏感性(71%~93%)、特異性(57%~98.9%)、陽性預測值(86%~96.7%)、陰性預測值(88.7%~92%)以及ROC-AUC(0.72~0.86)五個方面均較高。除了診斷的有效性外,Cronbach的alpha值(0.83~0.90)和重測信度(0.78~0.89)也較高,表明上述五種量表具有較強的內部一致性。通過對比發現,這五個量表和問卷是評估失眠的有效工具,其中三個量表診斷等級為A1,兩個量表診斷等級為A2(表3)。
PSQI的內容相對冗長,其評級程序較為復雜,但是,由于它具備全面性和心理測量特性,在目前的研究中被廣泛應用。AIS由8個條目組成,易于使用和評分;雖然AIS沒有提供除失眠以外的其他睡眠障礙的信息,但由于它的簡單性和易診斷性,也被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廣泛使用。BIQ的內容也相當冗長,評估難度較大,但是,復雜的設計程序卻使其成為一個更加有價值的評估工具,尤其是對大型流行病學研究而言。SLEEP-50Q主要用于評估睡眠障礙,涉及的內容主要與失眠有關,所以它一般只用于失眠的人群研究中。GSAQ對原發性失眠的敏感性、特異性和AUC相對較低,而對除失眠以外的睡眠障礙的敏感性、特異性和AUC普遍較高,表明GSAQ更適宜于評估除失眠以外的睡眠障礙。
2.2 評估睡眠功能失調性信念與態度量表
認知過程在失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為了量化與睡眠相關的認知,Morin等[9]設計了睡眠功能失調性信念和態度量表(dysfunctional beliefs and attitudes about sleep scale,DBAS),該量表共包含30個項目。同時,也出版了簡短版本,即DBAS-16[10]。總的來說,所有版本的DBAS均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可以將失眠患者和睡眠良好者區別開來。但DBAS對失眠患者和健康人的鑒別準確率相對較高,而DBAS-16是一種簡便、有效的評估工具,可用于普遍的失眠群體。雖然其他類型的睡眠障礙中也存在DBAS評分增加的情況,如不安腿綜合征(restless legs syndrome,RLS)或伴有睡眠呼吸暫停的RLS,但這并不影響DBAS評分與失眠嚴重程度呈正相關的事實。除DBAS外,其他與認知過程相關的量表對失眠的診斷也具有較好的有效性,如格拉斯哥思想內容量表(Glasgow content of thoughts inventory,GCTI)和格拉斯哥睡眠努力度問卷(Glasgow sleep effort scale,GSES)(表4)。實際上,GCTI量表主要用于認知心理學領域,側重于評估睡眠前的認知活動,而不是用于評估失眠本身;因此,它在日常臨床實踐中應用較為有限。相同的是,GSES量表也并不是為了評估失眠,而是作為一種自我控制睡眠的措施而設計的,所以更適宜于由心理原因導致的失眠。
2.3 人格特征評估量表
心理測量工具和生物測量工具診斷失眠的效能評分見表5。一項基于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驗(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的研究發現[17],與睡眠良好者相比,失眠癥患者出現至少一個病理量表升高的情況更頻繁,其中,失眠癥患者的抑郁、精神衰弱、癔病、疑病癥臨床量表得分較高,表明抑郁、沉思、焦慮等特征多為失眠癥患者的人格特征。這種消極的情緒引起心理生理上的變化或許是導致失眠產生和持續惡性循環的原因。Van de Laar等[18]通過研究也發現了相似的結果,即失眠癥患者的癥狀常伴隨著抑郁、精神衰弱、癔病、疑病癥等臨床量表評分的增高而增加。但是,還需要進一步的縱向研究來探索人格特征和失眠之間的關系,尤其長期失眠是否會導致人格的改變。
五大人格特征包括神經質、外向型、開放型、宜人型、盡責型。有研究對失眠者的人格特征進行觀察發現,無論對失眠進行主觀或還是客觀評估,高神經質評分是預測失眠的有效因素[19];然而,神經質與失眠并沒有被發現具有確定的診斷性聯系[20]。在這五大人格特征中,外向型和情感積極型人格特征人群的睡眠質量良好[21, 22]。隨著時間的推移,責任心低與睡眠質量下降有較弱的相關性[20]。
除上述MMPI和五大人格特征外,其他關于人格特征的研究表明,慢性失眠癥患者比健康對照組人群更追求完美主義[23]。無論橫斷面研究還是縱向研究都證實了完美主義與睡眠不佳之間存在顯著聯系性,為避免睡眠不佳的報告具有主觀性,研究通過多導睡眠監測儀來測量睡眠情況,結果亦然[24,25]。但是,現有數據有限,還無法完全確定完美主義人格的測量方法對失眠癥的診斷是否有影響。
2.4 多導睡眠監測和睡眠腦電圖
多導睡眠監測是最常用的睡眠監測手段,為了闡明多導睡眠監測診斷失眠的臨床價值,Regen等[26]進行了一項包括582例慢性原發性失眠癥患者和485名良好睡眠人群的Meta分析,結果發現失眠癥患者和睡眠良好人群雖然在多方面存在差異,如前者睡眠效率降低,睡眠潛伏期增加,總睡眠時間減少,覺醒次數增加,慢波睡眠和快速眼動睡眠減少,覺醒時間增加;但兩組間總睡眠時間的差異僅為25 min;此外,所有表示睡眠量減少的指標差異普遍較小,差異最明顯的是睡眠效率和慢波睡眠持續時間(診斷分級B3)。但是,從總睡眠時間數據可發現,兩組主觀描述總睡眠時間的差異卻比較明顯,平均相差2小時。因此,對于失眠癥的診斷準確性來說,多導睡眠監測的上述指標還屬于較弱水平。因此,關于多導睡眠監測診斷失眠的其他證據力度更強的指標值得進一步探索。
多導睡眠監測中的循環交替模式(cyclic alternating pattern,CAP)是在非快動眼睡眠期多導睡眠監測出現的一種呈周期性的腦電變化,它以一系列明顯突出于背景的短暫性腦電事件的發放為特點,這些腦電事件重復出現的間隔時間為20~40秒[27]。CAP的變化標志著覺醒波動,數值越大,表示睡眠越紊亂和睡眠質量越差。Chouvarda等[28]的研究表明,通過CAP的改變來區分失眠癥患者和睡眠良好人群具有高效的準確性,表明CAP是診斷失眠的潛在可行途徑(診斷等級A1)。
睡眠腦電圖可以記錄睡眠期間的腦電波清空。Spiegelhalder等[29]發現原發性失眠人群在非快速眼動睡眠期間的快速頻率波段(sigma波和beta波)的數量增加,表明存在大腦皮層的覺醒與亢奮(診斷分級B3)。Colombo等[30]通過高密度腦電圖檢測到失眠癥患者在清醒時、靜息狀態下的腦電圖也存在beta波數量增加的情況,該結果表明單憑快速頻率波段尚不能說明對失眠癥的準確診斷具有意義。Riedner等[31]發現慢性失眠癥患者的整夜非快速眼動睡眠腦電圖的高頻腦電活動功率(>16 Hz)比對照組更強,分布在整個頭皮,表明即使在深睡眠階段,慢性失眠癥患者仍可能存在高喚醒狀態。Buysse等[32]發現,與對照組相比,失眠癥患者僅在第一個非快速眼動睡眠期存在高喚醒狀態(高頻腦電活動功率18~40 Hz)。然而,Svetnik等[33]卻認為失眠癥患者睡眠時的高喚醒狀態可能與受試者的性別有關,其中女性受試者出現上述情況的可能性更大。與此相反,Schwabedal等[34]發現,男性失眠癥患者在睡眠喚醒時的alpha波頻率與清醒時相似,但低于對照組,表明男性失眠癥患者在睡眠時也可能存在高喚醒狀態。總之,這些研究數據均不足以說明診斷失眠癥的有效性(診斷分級均為D)。
2.5 神經影像學
神經放射學和核醫學技術早已被用于研究失眠的診斷。有研究使用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對5名失眠患者和4名健康人進行檢查[35],發現失眠患者的額葉、頂葉和枕部大腦區域以及基底神經節在非快速眼動睡眠存在血流量減少,且該結果具有較高的診斷效度(診斷分級B1)。
18F-氟代脫氧葡萄糖正電子發射計算機體層攝影(18F-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18F-FDG-PET)可被用于評估大腦代謝模式。Nofzinger等[36]比較了7名失眠患者和20名健康人在非快速眼動睡眠和清醒期間的18F-FDG-PET結果,與健康對照比較,失眠患者的大腦從清醒到非快速眼動睡眠期間18FDG代謝降低的幅度更小,尤其是在上行網狀激活系統、情緒調節相關區域(杏仁核、海馬體和前扣帶皮層)和認知相關區域(前額葉皮層)。該結果在后續的一項包含44名失眠癥患者和40名健康對照人群的研究中得以驗證[37](診斷分級D)。研究進一步發現涉及意識的大腦區域可能參與了覺醒-睡眠過渡的感知[38],這導致大腦代謝模式在失眠患者中可能具有特征性的改變[39]。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診斷失眠癥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特定任務中,另一類是在靜息狀態下。一項與任務相關的研究調查了22名失眠癥患者和38名健康對照人群,結果表明失眠癥患者與睡眠刺激相關的杏仁核反應增加[40]。在執行認知任務期間,額葉區域的血流活動減少[41-43](診斷分級B1)。
許多研究對失眠癥中的靜息狀態功能連通性(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RSFC)進行了觀察,但是結果均不太一致。Leerssen等[44]報告了65名失眠癥患者海馬前體和前額皮質靜息狀態功能連通性增加(診斷分級B1),而Regen等[26]在20名失眠癥患者和20名健康對照人群中卻未發現顯著的組間差異,但是RSFC的一些其他數據與睡眠效率和睡眠潛伏期存在弱相關(診斷分級C3)。
Meta分析報告稱,目前不同研究中源于失眠癥的大腦影像學改變尚缺乏一致性[45]。結合現有證據可知上述各種指標對失眠的診斷具有一定有效性,然而,這些指標的不一致性和多樣性尚不能建立神經影像學的共同標準。究其原因,或許是研究涉及的樣本量太小,而探索性數據分析策略限制了研究的價值,導致了較高出現假陰性和假陽性結果的風險。
2.6 活動記錄儀
活動記錄儀是一種監測人體休息-活動周期的非侵入性手段。在睡眠醫學中用于評估晝夜節律、睡眠-覺醒節律和休息時間[46, 47]。目前,有兩項大型研究報告了活動記錄儀對失眠癥診斷的準確性,認為活動記錄儀具有比較好的診斷有效性,能夠區分失眠者和正常睡眠者[48, 49](診斷分級為A1和A2)。但是,其他許多關于失眠癥活動記錄儀的研究只報告了失眠癥患者與睡眠良好人群兩組間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并未提及具體的睡眠參數及其敏感性、特異性和預測值的臨界值。這便意味著活動記錄儀缺乏檢測睡眠情況的軟件算法標準,導致活動記錄儀可能會將躺在床上不睡覺的情況誤測為睡眠低效率。雖然,活動記錄儀對于失眠的診斷潛力較高,但是其應用還需進一步討論。
2.7 皮膚電傳導
皮膚電導水平(skin conductance level,SCL)是自主神經系統的一個心理/生理指標,代表了對情緒刺激反應的交感神經活動。在一項關于清醒時間的習慣性實驗研究中,Broman和Hetta[50]發現失眠癥患者與健康人對比,雖然SCL增加,但習慣性的重復指標很少,表明SCL對失眠癥的診斷敏感性偏低(診斷分級A4)。
2.8 心率和心率變異性
精神生理壓力可引起睡眠覺醒,同時導致心率(heart rate,HR)增加和心率變異(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降低。研究發現,在睡眠前和入睡早期會出現HR增加情況,但是該指標對失眠癥的診斷準確性水平在不同研究中的級別從B1至B3不等[51-53](診斷分級B1至B3)。HRV,即連續心動周期之間的時間變異性,通常指RR(R波到R波)間隔。在清醒或睡眠期間,心電圖所記錄的RR間隔隨著自主神經系統的功能改變而有所不同[54]。光譜分析顯示了RR間隔在三個等級頻率下對應的自主神經系統功能:高頻率(high frequency, HF),反映副交感神經輸入;低頻率(low frequency,LF),依賴于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輸入;極低頻率(very low frequency,VLF),受副交感神經的影響。LF/HF比值是評估交感神經平衡的一個指標[55]。Bonnet和Arand[51]在客觀診斷失眠癥的患者中發現,LF增加,HF減少,該結果反映了失眠癥患者交感神經平衡的變化情況。有研究觀察了失眠癥患者與健康對照者在靜息狀態、睡眠開始前后或特定睡眠階段的HRV,結果發現失眠者的HRV有兩種模式:要么低頻或高頻,且沒有顯著差異;要么高頻趨于降低,表明副交感神經張力降低[56];或低頻增加,表明交感神經活動增加[52];這些現象主要表現在睡眠開始前和睡眠的第二階段[53]。總之,睡眠前后HR的增加或許可被認為是診斷失眠癥的一個潛在指標(診斷分級B1至B3)。然而,根據上述研究結果,HRV尚不能作為診斷失眠的標志(診斷分級B4)。
2.9 體溫調節
溫度調節是指核心體溫和皮膚溫度的晝夜節律[57, 58]。健康的睡眠常伴隨著夜間核心體溫的下降。覺醒-睡眠和溫度節律之間不同步可能代表著某些特定類型的失眠[59]。研究顯示,老年人失眠與夜間核心體溫升高有關[60]。Gradisar等[61]指出,失眠癥患者與正常睡眠者相比,其核心體溫升高,但診斷準確性較低(診斷分級B3)。
2.10 耗氧率
總耗氧量作為全身代謝率的替代指標,可以評估身體的生理活動。Chapman等[62]指出,失眠癥患者的代謝率在白天和整個夜間都略有升高。這與高喚醒模型相一致,即覺醒時間和睡眠時間代謝率也升高。代謝率的增高不僅出現在客觀診斷的失眠患者中,在主觀感覺性失眠患者中也存在較小程度的升高(診斷分級B3和B4)。因此,總耗氧量也可能是客觀診斷失眠的潛在標志物。
2.11 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
目前關于失眠癥患者皮質醇水平變化的研究結果存在不一致。一些研究表明[63],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失眠癥患者在晚上和失眠前半夜的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和皮質醇水平顯著升高[64, 65](診斷分級B1),但其他的研究則沒有發現這個現象[66, 67]。不同嚴重程度的失眠或許是差異產生的原因。有研究觀察到總睡眠時間(total sleep time,TST)縮短的失眠癥患者在晚上的前半段和早上都表現出ACTH和皮質醇濃度升高;相比之下,TST正常或TST僅輕度減少的人群皮質醇水平并沒有改變[68, 69]。
有研究在失眠癥患者早晨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活動中觀察到不一致的結果,即失眠癥患者醒后的唾液皮質醇減少,或與正常睡眠者的皮質醇水平相當[66, 67, 70],表明較低的醒后皮質醇濃度與較低的睡眠質量和相關。有研究卻發現較短的客觀TST與早晨醒后皮質醇水平升高有關[69]。然而,通過地塞米松/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試驗證實失眠癥患者的HPA軸并沒有過度活躍[71]。可能慢性失眠一般是輕度至中度的睡眠時間縮短,因此,在這期間,出現適度的HPA軸活動屬于正常。
2.12 褪黑素
褪黑素是晝夜睡眠-覺醒節律的重要調節劑。夜間黑暗依賴的褪黑素水平的上升誘導了睡眠傾向,也參與前半夜以慢波睡眠為優勢的生理睡眠結構[67]。此外,褪黑素被認為可以調節HPA軸活動的晝夜節律[71]。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失眠癥患者的褪黑素在傍晚開始上升,在夜間的峰值較低,對失眠癥的診斷具有較好的效能[72](診斷分級B2)。
2.13 炎癥標志物
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介素6(interleukin 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是典型的炎癥標志物。有研究顯示,失眠與CRP中度水平升高有關,與IL-6和TNF-a水平無關[73]。與非失眠患者或非長期失眠患者相比,6年失眠病史的患者的CRP水平升高(診斷分級D)[74]。
2.14 神經可塑性標志物
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是一類具有營養神經作用的蛋白,在腦內和外周血清均有分布,對神經元的生長、發育、誘導分化及突觸連接具有調節功能。突觸穩態調節和大腦記憶鞏固通常發生在睡眠期間,表明睡眠不足可能與神經可塑性存在相關性。因此,隨著研究的進展,BDNF與失眠的聯系也逐漸被關注。研究顯示,對于抑郁癥出現失眠的患者,當抑郁癥控制后,存在失眠的患者的血清BDNF水平低于健康對照組[75]。另有研究也發現,失眠癥患者的血清BDNF水平比健康睡眠者更低,說明血清BDNF或許是診斷失眠癥的生物標志物[64](診斷分級A1)。在另一項研究中發現,低BDNF水平是診斷短睡眠時間性失眠和正常睡眠時間性失眠的生物標志物(診斷分級B1),而且在失眠和睡眠時間縮短的人群中,低BDNF水平和認知表現差之間存在關聯性[76]。可見,BDNF對于失眠的診斷具有一定的潛在價值。
3 結論
失眠、睡眠信念與態度的量表和問卷是基于既定的截止分數來作為診斷失眠的金標準,這些量表和問卷在至少一項研究中,診斷分級為A1,診斷效能屬于“極好”。MMPI作為一種診斷失眠的評估工具,其診斷效能屬于“好”,盡管低于前述失眠、睡眠信念與態度的量表和問卷,但是其診斷潛力相對較好。此外,對失眠具有高效診斷性能,并可被視為潛在生物標志物的指標有活動記錄儀,血清BDNF水平,CAP;其次是心率增加(入睡前或入睡后早期)、神經影像學改變(在睡眠和/或清醒時大腦部分回路高度激活)。褪黑素水平對于失眠的診斷效能屬于“一般”,而HPA軸則屬于“不好”。因此,在沒有更高證據的研究報告之前,一般不推薦將用褪黑素水平和HPA軸的激素水平來診斷、評估失眠。
對于其他測量指標,盡管失眠患者的核心體溫的升高具有一定的診斷潛力,但是測量核心體溫的過程不適合臨床目的。耗氧量也對失眠顯示出了一定的診斷能力,但不適用于只有主觀主訴的失眠癥患者,因此,這種方法的臨床應用不切實際。對SCL而言,該指標還未顯示出較好的診斷準確性。如前所述,CRP與慢性失眠有關,而慢性失眠常伴隨壓力與焦慮的出現,壓力與焦慮對CRP的影響尚未清楚,因此,CRP對于診斷失眠的用途僅處于探索階段。
因為成本效益和程序復雜程度,上述部分診斷失眠的潛在指標(如核磁共振或需要采血的指標)的廣泛性和適用性受限。為提供敏感性、特異性都比較高的指標作為失眠的診斷標準,還有諸多工作需要進行:如進行數量足夠多的研究來重復評估診斷偏倚;設計普遍接受的方法來評估一項研究的有效性;對指標設立適當的診斷截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