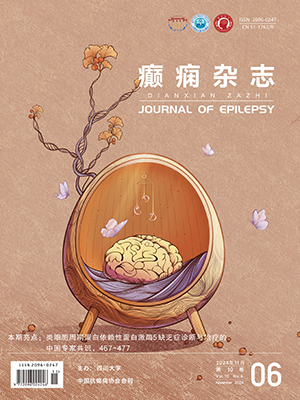引用本文: 連雨晴, 普布, 陳玉秀, 王文輕, 郝渝, 次央, 趙偉偉, 趙玉華. 西藏高原地區多藥物聯合治療癲癇患者的臨床特征分析. 癲癇雜志, 2024, 10(6): 503-507. doi: 10.7507/2096-0247.202408009 復制
癲癇是一種有著不同病因基礎但以反復癲癇發作為共同特征的慢性腦部疾病狀態[1]。目前我國癲癇患者數量至少達到900萬,但約有2/3的患者未得到正確和充分的治療,這一比例在西藏地區高達87%[2]。在國內相關研究中,西藏高原地區癲癇治療缺口最大,這與當地診療缺陷、經濟條件落后、獨特的地理環境、文化信仰和到達醫療機構的距離有關[3]。目前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是最重要的治療手段,我國有超過20種ASMs可供臨床選擇,初始單藥治療仍為首選,當初始單藥未達到癲癇緩解的治療目標時,可選擇更換單藥或聯合添加治療[4]。目前西藏高原地區尚無有關多藥物聯合治療癲癇患者的研究報道,因此在本地區開展此研究對于指導西藏高原地區的規范性癲癇診療很有必要。本研究收集了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癲癇患者的臨床資料,旨在提供西藏高原地區癲癇患者臨床特征的最新信息,以幫助改進該地區癲癇診療管理策略。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出院診斷“癲癇”、“癇性發作”、“癲癇發作”、“癲癇持續狀態”、“難治性癲癇”為關鍵詞,回顧性搜索2018年9月—2023年9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住院的癲癇患者共計2 295例,最終納入142例(6.2%)。該研究獲得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ME-TBHP-23-09)及所有患者或監護人知情同意。
1.1.1 納入標準
① 住院期間確診癲癇,診斷符合《臨床診療指南?癲癇病分冊(2023年修訂版)》中癲癇診斷標準,且臨床資料相對完整;② 聯合使用≥2種ASMs。
1.1.2 排除標準
① 單種ASM治療者,或接受手術等其他治療方式者;② 存在嚴重的全身系統性疾病,例如昏迷、嚴重精神障礙性疾病、嚴重肝腎疾病等;③ 拒絕參與者。
1.2 研究方法
通過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病例檢索系統,回顧性收集符合入排標準的癲癇患者性別、年齡、民族等人口學資料及診斷信息、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檢查、服用藥物、癲癇發作頻率等臨床相關資料,并分析相關人口學特征及臨床特征。后期以電話隨訪的方式記錄服藥及癲癇發作控制等情況。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 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數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 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及病因分析
93.7%的患者為藏族(133/142)。所有患者中年齡最小者僅為10天,年齡最大者84歲,平均發病年齡(28.7±22.0)歲,未成年及青年發病人數多于中老年(106 vs. 36,P<0.05)。87.3%的患者接受了MRI或CT檢查,71.1%(101例)患者發現異常。結構性病因為癲癇主要原因,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構性病因中,腦卒中占比最大(38/84,45.2%)。感染性病因中有8例(8/13,61.5%)為腦部寄生蟲感染繼發的癲癇發作。腦炎或腦膜炎急性期的癥狀性癲癇發作3例不參與病因分析(3/142,2.1%)。詳見表1。
2.2 抗癲癇發作藥物使用情況
2種藥物聯合使用最多(127/142例,89.4%),其中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合使用占比最大(46/142,32.4%),其次為丙戊酸鈉與奧卡西平聯合使用(30/142,21.1%),左乙拉西坦與奧卡西平聯合使用次之(19/142,13.4%),其余處方數量占比均在5%以下。3種及4種藥物聯合使用分別為13例(9.2%)和2例(1.4%)。詳見表2。
2.3 聯合用藥療效分析
以電話隨訪的方式記錄了所有患者目前癲癇發作控制的情況,失聯及死亡33例、有效隨訪109例,平均隨訪時間為(34.74±17.03)個月,基線資料示癲癇平均發作頻率(51.68±93.58)次/月,聯合用藥后癲癇平均發作頻率(6.28±30.90)次/月,規范多藥聯合治療后癲癇平均發作頻率較基線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產生藥物副作用12例,其中9例患者聯合用藥后出現記憶力減退、3例患者復查血液指標出現肝腎功能異常。
2.4 藥物難治性癲癇
因<14歲人群主要就診于兒科,此次在≥14歲的98例患者中進行了明確藥物難治性癲癇(drug-refractory epilepsy,DRE)診斷的相關隨訪,平均隨訪時間為(32.80±16.85)個月,結果如下:DRE 15例(15.3%)、規范聯合用藥已控制發作18例(18.4%)、聯合用藥減為單藥已控制發作16例(16.3%)、目前控制良好已停藥5例(5.1%)、用藥依從性差導致癲癇頻繁發作3例(3.1%)、不規范用藥15例(15.3%)、死亡17例(17.3%)、失聯9例(9.2%)。針對DRE進一步分析,患者均為藏族,居住地海拔均在2 700米以上,男女性別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未成年及青年發病人數多于中老年(11 vs. 4,P>0.05),2種藥物聯用最多(8/15例,53.3%),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兩藥聯合及丙戊酸鈉、左乙拉西坦與奧卡西平三藥聯合各3例(3/15,20%),數量占比最大。詳見表4。
3 討論
西藏自治區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因獨特的地理歷史環境,此次研究中93.7%的患者為藏族(133/142),其中男性(86/142,60.6%)多于女性(56/142,39.4%),未成年及青年發病人數多于中老年,101例(71.1%)患者完善頭顱MRI/CT后發現異常。對照西藏地區現有研究結論高原地區癲癇患者以青壯年為主,男性多于女性,且高原低壓低氧環境對人體神經系統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5-8],與本次研究結論相符。
病因分析中,結構性病因84例(84/142,59.2%),為多藥物聯合治療癲癇患者的主要原因,與既往多項研究結論一致[9,10]。結構性病因中腦卒中疾病占比最大(38/84,45.2%),腦卒中是約10%的癲癇患者和55%的老年人群新診斷癲癇的病因,卒中后癲癇(post stroke epilepsy,PSE)是腦卒中的常見并發癥,發病率為2%~20%[11]。本團隊有關PSE的研究發現蛛網膜下腔出血及腦靜脈竇血栓形成引起PSE的發生率高,而腦卒中引起PSE的發生率最低[12],這與既往研究結論一致[11]。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感染性病因中有8例(8/13,61.5%)為腦部寄生蟲感染繼發的癲癇發作,主要為腦囊尾蚴病和棘球蚴病,這與藏族人民飲食生活習慣相關,許多當地人以畜牧為生,且多喜食生肉,從而使感染囊尾蚴及棘球絳蟲蚴蟲的機率增加[5,13]。因此,在西藏地區開展科學衛生的飲食生活方式教育及積極防治卒中后癲癇尤為重要,這對減少癲癇發生和改善預后至關重要。
癲癇早期、正確的診斷及有效的治療,可能達到終身無發作[14]。對于局灶性或全面性起源的癲癇,ASMs的選擇應考慮癲癇發作類型和癲癇綜合征,以及患者的年齡和性別、禁忌癥、合并癥和潛在的藥物相互作用[15]。此次研究多藥聯合治療癲癇患者占比為6.2%,較現有研究結論低[16],由于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本地區腦部寄生蟲感染繼發癲癇發作病例較多,而此種病例多為單藥控制癲癇為主,這也促使本地區多藥物聯用治療癲癇比例相對較低,另收集病例時患者可能處于基線治療等因素也會使多藥聯用比例更少。多藥規范聯用療效肯定,本次研究數據顯示癲癇平均發作頻率較基線明顯降低,與既往多項研究結論一致[17,18]。2種藥物聯合使用最多,根據最新ASMs聯合使用專家共識推薦意見當初始單藥治療未達到癲癇緩解時,可選擇更換單藥或聯合添加治療[4]。藥物處方聯用大多合理,以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用數量占比最大,國內一項小兒癲癇藥物療效研究中肯定了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用治療效果,且此處方有利于減輕神經損傷與炎癥反應,用藥安全性高[19]。本次研究中不規范用藥15例,主要原因是在單藥治療時未達到足量即開始添加另一種藥物,據我院癲癇專科門診數據得知眾多患者在服藥后未達到理想療效時即前往某私人診所就診,當地開具的藥物處方多為直接3、4或5種藥物聯用,患者癲癇發作雖較前稍控制但毒副作用很多,致使癲癇發展為藥物難治性的機率大大增加,類似現象在既往也有報道[20],這與患者對癲癇疾病認識不夠及私人診所不規范行醫相關,故本地區加強癲癇疾病的科普宣傳教育至關重要。此外還包括診斷錯誤、選藥錯誤、患者的依從性差等因素進一步使癲癇發作控制不佳[21]。在后續隨訪的98例患者中DRE 15例(15/98,15.3%),低于以往1/3以上的研究比例[22-24],經分析15例DRE患者均為藏族,性別及年齡無統計學差異,居住地海拔均在2 700米以上,2種藥物聯用最多,且以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用為主,藥物處方合理,但DRE比例較低,這可能與后續隨訪中死亡與失聯病例信息獲取不完整相關。有報道40%的癲癇與遺傳性病因相關[25],但此次DRE病因多為結構性,考慮與西藏高原地理環境特殊所導致的腦部血管疾病增多相關。
綜上所述,通過此次研究顯示本地區多藥聯合治療占比為6.2%,療效肯定,其中DRE占比為15.3%,低于通常的1/3以上的比例,不可確定是否有被低估,未來尚需開展前瞻性、大樣本、多中心的研究。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
癲癇是一種有著不同病因基礎但以反復癲癇發作為共同特征的慢性腦部疾病狀態[1]。目前我國癲癇患者數量至少達到900萬,但約有2/3的患者未得到正確和充分的治療,這一比例在西藏地區高達87%[2]。在國內相關研究中,西藏高原地區癲癇治療缺口最大,這與當地診療缺陷、經濟條件落后、獨特的地理環境、文化信仰和到達醫療機構的距離有關[3]。目前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seizure medications,ASMs)是最重要的治療手段,我國有超過20種ASMs可供臨床選擇,初始單藥治療仍為首選,當初始單藥未達到癲癇緩解的治療目標時,可選擇更換單藥或聯合添加治療[4]。目前西藏高原地區尚無有關多藥物聯合治療癲癇患者的研究報道,因此在本地區開展此研究對于指導西藏高原地區的規范性癲癇診療很有必要。本研究收集了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癲癇患者的臨床資料,旨在提供西藏高原地區癲癇患者臨床特征的最新信息,以幫助改進該地區癲癇診療管理策略。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出院診斷“癲癇”、“癇性發作”、“癲癇發作”、“癲癇持續狀態”、“難治性癲癇”為關鍵詞,回顧性搜索2018年9月—2023年9月在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住院的癲癇患者共計2 295例,最終納入142例(6.2%)。該研究獲得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ME-TBHP-23-09)及所有患者或監護人知情同意。
1.1.1 納入標準
① 住院期間確診癲癇,診斷符合《臨床診療指南?癲癇病分冊(2023年修訂版)》中癲癇診斷標準,且臨床資料相對完整;② 聯合使用≥2種ASMs。
1.1.2 排除標準
① 單種ASM治療者,或接受手術等其他治療方式者;② 存在嚴重的全身系統性疾病,例如昏迷、嚴重精神障礙性疾病、嚴重肝腎疾病等;③ 拒絕參與者。
1.2 研究方法
通過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病例檢索系統,回顧性收集符合入排標準的癲癇患者性別、年齡、民族等人口學資料及診斷信息、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或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檢查、服用藥物、癲癇發作頻率等臨床相關資料,并分析相關人口學特征及臨床特征。后期以電話隨訪的方式記錄服藥及癲癇發作控制等情況。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 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數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 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及病因分析
93.7%的患者為藏族(133/142)。所有患者中年齡最小者僅為10天,年齡最大者84歲,平均發病年齡(28.7±22.0)歲,未成年及青年發病人數多于中老年(106 vs. 36,P<0.05)。87.3%的患者接受了MRI或CT檢查,71.1%(101例)患者發現異常。結構性病因為癲癇主要原因,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構性病因中,腦卒中占比最大(38/84,45.2%)。感染性病因中有8例(8/13,61.5%)為腦部寄生蟲感染繼發的癲癇發作。腦炎或腦膜炎急性期的癥狀性癲癇發作3例不參與病因分析(3/142,2.1%)。詳見表1。
2.2 抗癲癇發作藥物使用情況
2種藥物聯合使用最多(127/142例,89.4%),其中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合使用占比最大(46/142,32.4%),其次為丙戊酸鈉與奧卡西平聯合使用(30/142,21.1%),左乙拉西坦與奧卡西平聯合使用次之(19/142,13.4%),其余處方數量占比均在5%以下。3種及4種藥物聯合使用分別為13例(9.2%)和2例(1.4%)。詳見表2。
2.3 聯合用藥療效分析
以電話隨訪的方式記錄了所有患者目前癲癇發作控制的情況,失聯及死亡33例、有效隨訪109例,平均隨訪時間為(34.74±17.03)個月,基線資料示癲癇平均發作頻率(51.68±93.58)次/月,聯合用藥后癲癇平均發作頻率(6.28±30.90)次/月,規范多藥聯合治療后癲癇平均發作頻率較基線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產生藥物副作用12例,其中9例患者聯合用藥后出現記憶力減退、3例患者復查血液指標出現肝腎功能異常。
2.4 藥物難治性癲癇
因<14歲人群主要就診于兒科,此次在≥14歲的98例患者中進行了明確藥物難治性癲癇(drug-refractory epilepsy,DRE)診斷的相關隨訪,平均隨訪時間為(32.80±16.85)個月,結果如下:DRE 15例(15.3%)、規范聯合用藥已控制發作18例(18.4%)、聯合用藥減為單藥已控制發作16例(16.3%)、目前控制良好已停藥5例(5.1%)、用藥依從性差導致癲癇頻繁發作3例(3.1%)、不規范用藥15例(15.3%)、死亡17例(17.3%)、失聯9例(9.2%)。針對DRE進一步分析,患者均為藏族,居住地海拔均在2 700米以上,男女性別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未成年及青年發病人數多于中老年(11 vs. 4,P>0.05),2種藥物聯用最多(8/15例,53.3%),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兩藥聯合及丙戊酸鈉、左乙拉西坦與奧卡西平三藥聯合各3例(3/15,20%),數量占比最大。詳見表4。
3 討論
西藏自治區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因獨特的地理歷史環境,此次研究中93.7%的患者為藏族(133/142),其中男性(86/142,60.6%)多于女性(56/142,39.4%),未成年及青年發病人數多于中老年,101例(71.1%)患者完善頭顱MRI/CT后發現異常。對照西藏地區現有研究結論高原地區癲癇患者以青壯年為主,男性多于女性,且高原低壓低氧環境對人體神經系統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5-8],與本次研究結論相符。
病因分析中,結構性病因84例(84/142,59.2%),為多藥物聯合治療癲癇患者的主要原因,與既往多項研究結論一致[9,10]。結構性病因中腦卒中疾病占比最大(38/84,45.2%),腦卒中是約10%的癲癇患者和55%的老年人群新診斷癲癇的病因,卒中后癲癇(post stroke epilepsy,PSE)是腦卒中的常見并發癥,發病率為2%~20%[11]。本團隊有關PSE的研究發現蛛網膜下腔出血及腦靜脈竇血栓形成引起PSE的發生率高,而腦卒中引起PSE的發生率最低[12],這與既往研究結論一致[11]。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感染性病因中有8例(8/13,61.5%)為腦部寄生蟲感染繼發的癲癇發作,主要為腦囊尾蚴病和棘球蚴病,這與藏族人民飲食生活習慣相關,許多當地人以畜牧為生,且多喜食生肉,從而使感染囊尾蚴及棘球絳蟲蚴蟲的機率增加[5,13]。因此,在西藏地區開展科學衛生的飲食生活方式教育及積極防治卒中后癲癇尤為重要,這對減少癲癇發生和改善預后至關重要。
癲癇早期、正確的診斷及有效的治療,可能達到終身無發作[14]。對于局灶性或全面性起源的癲癇,ASMs的選擇應考慮癲癇發作類型和癲癇綜合征,以及患者的年齡和性別、禁忌癥、合并癥和潛在的藥物相互作用[15]。此次研究多藥聯合治療癲癇患者占比為6.2%,較現有研究結論低[16],由于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本地區腦部寄生蟲感染繼發癲癇發作病例較多,而此種病例多為單藥控制癲癇為主,這也促使本地區多藥物聯用治療癲癇比例相對較低,另收集病例時患者可能處于基線治療等因素也會使多藥聯用比例更少。多藥規范聯用療效肯定,本次研究數據顯示癲癇平均發作頻率較基線明顯降低,與既往多項研究結論一致[17,18]。2種藥物聯合使用最多,根據最新ASMs聯合使用專家共識推薦意見當初始單藥治療未達到癲癇緩解時,可選擇更換單藥或聯合添加治療[4]。藥物處方聯用大多合理,以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用數量占比最大,國內一項小兒癲癇藥物療效研究中肯定了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用治療效果,且此處方有利于減輕神經損傷與炎癥反應,用藥安全性高[19]。本次研究中不規范用藥15例,主要原因是在單藥治療時未達到足量即開始添加另一種藥物,據我院癲癇專科門診數據得知眾多患者在服藥后未達到理想療效時即前往某私人診所就診,當地開具的藥物處方多為直接3、4或5種藥物聯用,患者癲癇發作雖較前稍控制但毒副作用很多,致使癲癇發展為藥物難治性的機率大大增加,類似現象在既往也有報道[20],這與患者對癲癇疾病認識不夠及私人診所不規范行醫相關,故本地區加強癲癇疾病的科普宣傳教育至關重要。此外還包括診斷錯誤、選藥錯誤、患者的依從性差等因素進一步使癲癇發作控制不佳[21]。在后續隨訪的98例患者中DRE 15例(15/98,15.3%),低于以往1/3以上的研究比例[22-24],經分析15例DRE患者均為藏族,性別及年齡無統計學差異,居住地海拔均在2 700米以上,2種藥物聯用最多,且以丙戊酸鈉與左乙拉西坦聯用為主,藥物處方合理,但DRE比例較低,這可能與后續隨訪中死亡與失聯病例信息獲取不完整相關。有報道40%的癲癇與遺傳性病因相關[25],但此次DRE病因多為結構性,考慮與西藏高原地理環境特殊所導致的腦部血管疾病增多相關。
綜上所述,通過此次研究顯示本地區多藥聯合治療占比為6.2%,療效肯定,其中DRE占比為15.3%,低于通常的1/3以上的比例,不可確定是否有被低估,未來尚需開展前瞻性、大樣本、多中心的研究。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