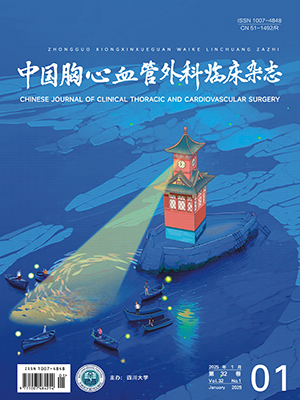微創是21世紀外科的發展方向,腔鏡外科技能是所有外科醫生都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腔鏡技能培訓也是外科住院醫師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目前國際上腔鏡外科技能培訓的方法存在差異,且考核方式仍停留在考官肉眼觀察學員操作及主觀評價階段。本文綜述了目前國內外腔鏡模擬培訓與考核的研究現狀,并討論了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研發過程和應用成果,旨在為腔鏡模擬教育發展提供一定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
引用本文: 周健, 廖虎, 鄭權, 劉倫旭. 腔鏡模擬培訓和考核研究現狀分析與探討.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4, 31(5): 667-671. doi: 10.7507/1007-4848.202311033 復制
版權信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華西期刊社《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改編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腔鏡手術的應用范圍逐漸從診斷擴展到治療,其適應病種也不斷增多,已逐漸成為外科的常規術式[1-2]。根據美國一項全國手術病例數據庫的研究[1],2003—2018年普外科的6種常見術式中,腔鏡微創手術占比均顯著增加,其中膽囊切除術、闌尾切除術、Nissen胃底折疊術在2018年的腔鏡手術占比均超過90%。一項在2016年開展的調查[3]顯示,在國內開展胸外科手術的三級醫院中,已有超過90%的醫院開展了胸腔鏡手術。腔鏡外科手術是外科微創化的標志,小切口、微創化提升了患者的術后生活質量[4-7]。腔鏡技能已成為所有外科醫生都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而腔鏡技能培訓也是外科住院醫師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腔鏡外科技能培訓的重點在于提升醫師的腔鏡意識運動技能(laparoscopic psychomotor skills,LPS),即醫師在處理人體組織時所需的意識動作協調一致的精細操作能力。有效而持續的重復訓練對LPS的培養至關重要[8-9]。因此,開展腔鏡外科技能培訓具有重要意義。
傳統的腔鏡外科技能培訓多采用“師徒傳承”模式,在手術室內進行,學員通過反復觀察老師的操作后進行自主實踐[10-11]。學員需要觀察學習和實際操作一定數量的手術后,才能達到熟練水平。例如,對于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在完成25~50例手術后,學員才能達到相對穩定的操作水平[12]。對腹腔鏡肝切除術學習曲線的研究[13-14]表明,術者在完成37~42例手術后學習曲線進入平穩期。在學習曲線的初期,學員難免會有較高的錯誤率[15]。然而,如今醫師人數不斷增加,年輕腔鏡醫生在手術室內的實踐和練習機會有所減少。為保障患者安全,亟需一種手術室外的訓練方式,即模擬訓練。模擬訓練為學員提供了在高效、安全的訓練環境中進行手術室外腔鏡技能訓練的機會,有助于積累操作經驗,縮短醫師手術室內訓練時間,避免學習曲線上的高錯誤率階段出現[16]。
為確保醫師腔鏡訓練的有效性,確保其培訓成果能夠提升腔鏡手術技術水平[17],有必要建立標準化的考核評估體系。這一體系主要包括“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前者作為訓練過程中的考核,持續為訓練者提供反饋;后者則是對學員訓練成果的綜合評估,用于確定整體訓練的合格情況[4, 18]。通過不同階段和不同維度的考核,能夠客觀反映腔鏡訓練效果,提升腔鏡技能培訓水平。
1 腔鏡外科技能培訓與考核研究現狀
1.1 腔鏡外科技能培訓設備
目前常見的腔鏡外科技能培訓設備主要是腔鏡模擬訓練箱[19],其類型可分為實體模具和虛擬仿真模具。實體模具通常采用硅膠材料或動物實體器官來模擬人體體腔結構,通過操作真實的腔鏡手術器械進行抓持、傳遞、裁剪、縫合等訓練[19-20]。這種方法有助于學員練習必備的腔鏡手術基本技能,并提供了近似真實的腔鏡器械操作體驗。其設計簡單易推廣,但普遍缺乏對訓練效果進行客觀評價的標準。
虛擬仿真模具以虛擬現實和人機交互的形式實現訓練目的[21-22],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進行精細解剖、組織切除等腔鏡基本技能的訓練,還可以模擬各種基本手術流程。此外,基于人機交互,能夠實時記錄學員的操作數據,并對學員操作水平進行動態、客觀的評價。然而,虛擬仿真模具的力反饋等人機交互系統尚無法完全還原實際操作的感覺。研究[21]顯示,相比于實體模具訓練箱,虛擬仿真模具在培訓效果上并沒有明顯優勢,其昂貴的價格也限制了廣泛應用。
1.2 腔鏡外科技能培訓和考核體系
國內的腔鏡培訓尚未形成統一的體系,目前仍由各醫學院校或者醫院因地制宜開展。例如,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提出了基于SMART(specific,measurable, attainable,relevant,time-bound)原則建立的三階段腔鏡規范化培訓模式[23]。該模式按階段逐漸深入,首先是器具模擬訓練,包括熟悉夾持、切割、縫合等操作。只有器具模擬訓練合格后,學員才能進行動物離體手術訓練,掌握手術方式的規范操作模式。在通過動物離體手術考核后,學員才能參與真實的人體手術培訓。其他國內院校也提出了類似的三層次培訓模式。例如安徽醫科大學的外科基本操作訓練、腔鏡基本理論授課;腔鏡模擬器訓練、手術錄像教學;腔鏡手術中的扶鏡及一助操作訓練[24]。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提出包括解剖影像基礎、胸腔鏡操作意識和臨床實際操作的三層次培訓模式[25]。這些培訓體系強調層次遞進的培訓模式,但實際應用情況有所不同,目前多限于院校內部使用。
在北美地區,廣泛應用的腔鏡訓練考核系統是美國胃腸內鏡手術學會于2004年提出的腹腔鏡手術基礎操作(fundamental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FLS),已得到美國外科醫師學會認證[26-27]。FLS旨在為腔鏡醫師提供標準教材,并為理論知識與技能提供相應的評定標準[26]。其訓練和考核項目包括傳遞、裁剪、圈套器結扎、縫合與體內外打結[28]。有研究[29]表明,FLS培訓可以顯著提升學員在實際手術中的操作水平。然而,成績評定的主觀性、反饋滯后以及較高的費用等因素限制了其推廣應用[30]。因此,一些中心開始嘗試構建自動化的FLS考核方式[31],客觀化和自動化考核是FLS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在歐洲地區,應用較廣的是歐洲婦科腔鏡協會和歐洲婦科腔鏡培訓學院在2004年聯合開發的婦科內窺鏡外科手術教育與評估系統(Gynecological Endoscopic Surgical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GESEA)[32]。腔鏡醫師首先進行線上教程學習,隨后在系統模型中進行訓練及考核[33]。近年來,國內部分醫院也在醫師培訓考核體系中引入GESEA,有些地區還開展了基于GESEA的腔鏡外科技能比賽。例如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婦產科報道了GESEA對住院醫師腔鏡手術技能的提升作用[34]。然而,該項目的考核結果主要依賴于考官對GESEA標準與考核者表現的人工比對[28],因此存在較強主觀性。
總體而言,目前腔鏡模擬培訓主要側重于理論課程學習和模擬訓練,并且考核多依賴人工評分。由于缺乏統一的考核標準,主觀評分難以準確體現腔鏡模擬培訓效果,未來重要的研究方向將是如何建立客觀的考核標準。
1.3 腔鏡外科技能考核標準
國內腔鏡模擬培訓技能考核標準多基于完成傳遞、裁剪、縫合、打結等操作所用時間和操作流暢度,在合格分數線設置方面尚無統一的標準,且流暢度主要依賴考官的主觀評價[35-38]。相較之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Vassiliou等[39]提出的全球腔鏡手術技術評估(Global Operative Assessment of Laparoscopic Skills, GOALS)在國外得到了廣泛應用[40-42]。該評估方式基于5個領域評價醫師的腔鏡外科技能水平,包括深度知覺、雙手靈巧度、效率、組織處理和自主性。考官通過肉眼觀察打分,每一領域評分以1~5的整數表示,描述性的分界點為1、3、5分[40] (表1)。通過分析腔鏡醫師在各領域的考核平均分,可區分初學者與經驗豐富者,同時GOALS評分也能很好地反映FLS訓練成果[43]。然而,這種考核方法仍局限于考官對學員操作的肉眼觀察和主觀評價,一方面缺乏客觀評價標準與手段,另一方面需耗費大量師資和人力。
2 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的研發和應用
針對以上問題,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劉倫旭、廖虎牽頭研發了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44]。通過圖像識別、精細化感知等技術,涵蓋了視野定位、抓持、傳遞、精細裁剪和縫合打結共5個腔鏡基本操作模塊,實現了智能化腔鏡技能培訓與考核。該系統利用智能算法,將難以量化考核的臨床操作技能轉化為可測量、可評估、可重復的客觀考核指標。技能考核評分的過程實現全自動化,無需人工參與。該系統還能進行實時數據反饋:系統在學員訓練過程中動態收集數據,并提供客觀評分和個性化學習方案;同時,結合大數據處理、深度學習與長短期記憶網絡技術,動態更新、貼近臨床要求的考核標準,提升了評分標準的客觀性。初步研究[45]表明,相較于傳統的人工評估,該系統可以更好地區分腔鏡技術水平。該系統使微創外科培訓的評估手段和標準從主觀走向客觀,做到規范化、可量化,提升了可控性和工作效率,從而實現腔鏡外科技能的標準化、自動化和智能化評估(圖1,表2)。
 圖1
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設備
圖1
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設備
以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為契機,經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立項,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組織實施了“四川省基層醫院微創胸外科能力提升項目”,為達州、西昌、涼山州、甘孜州等地區的醫療技術、醫療硬件各方面提供幫助。項目已在24家縣級建設醫院開展試點,并完成了各建設醫院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教具的配置和使用培訓。通過短期專項培訓、專家現場示教、手術指導、線上遠程教育、遠程會診等方式,穩步提升建設醫院的醫療水平。在項目的持續推動下,這24家建設醫院已全面開展微創胸外科手術,部分醫院已實現微創胸外科手術的自主開臺,醫院門診量、手術量、微創率顯著提升,部分醫院已單獨成立了胸外科。
3 討論
目前國內部分醫學院校和機構開展了腔鏡培訓和考核的探索,但系統化、標準化仍有欠缺。相較之下,FLS、GESEA腔鏡培訓系統和GOALS考核體系在北美、歐洲應用較廣泛,但仍存在系統項目模塊設置較單一、評價標準客觀性不足等問題。
為提升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1)制定統一的腔鏡操作規范,為腔鏡外科技能訓練和考核提供明確指導,使訓練、考核標準更加科學合理,符合臨床需求;(2)統一培訓考核項目與評分標準,以便高效地分析訓練結果和制定下一步訓練計劃,促進培訓與考核系統的推廣;(3)加強考核評分客觀性,利用智能算法消除人為主觀判斷對于學員評估的影響,從而對學員的培訓成效進行準確評判;(4)縮短腔鏡模擬培訓和真實手術操作的差距。研究[46]表明,訓練者在模擬訓練得分與手術室中表現分數存在差異,如何縮小這一差距是未來研究的重點之一。
綜上所述,腔鏡模擬訓練與考核系統的建設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面臨多方面挑戰。通過制定規范、統一培訓考核項目與標準、增強客觀性以及縮短培訓和真實操作的距離,可以進一步提升腔鏡模擬訓練與考核系統的價值,為培養高水平的腔鏡醫師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劉倫旭主導研究實施,負責選題與設計;周健、廖虎和鄭權參與文獻收集和分析;全體作者參與文章撰寫及審閱。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腔鏡手術的應用范圍逐漸從診斷擴展到治療,其適應病種也不斷增多,已逐漸成為外科的常規術式[1-2]。根據美國一項全國手術病例數據庫的研究[1],2003—2018年普外科的6種常見術式中,腔鏡微創手術占比均顯著增加,其中膽囊切除術、闌尾切除術、Nissen胃底折疊術在2018年的腔鏡手術占比均超過90%。一項在2016年開展的調查[3]顯示,在國內開展胸外科手術的三級醫院中,已有超過90%的醫院開展了胸腔鏡手術。腔鏡外科手術是外科微創化的標志,小切口、微創化提升了患者的術后生活質量[4-7]。腔鏡技能已成為所有外科醫生都必須掌握的基本技能,而腔鏡技能培訓也是外科住院醫師培訓的重要組成部分。腔鏡外科技能培訓的重點在于提升醫師的腔鏡意識運動技能(laparoscopic psychomotor skills,LPS),即醫師在處理人體組織時所需的意識動作協調一致的精細操作能力。有效而持續的重復訓練對LPS的培養至關重要[8-9]。因此,開展腔鏡外科技能培訓具有重要意義。
傳統的腔鏡外科技能培訓多采用“師徒傳承”模式,在手術室內進行,學員通過反復觀察老師的操作后進行自主實踐[10-11]。學員需要觀察學習和實際操作一定數量的手術后,才能達到熟練水平。例如,對于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在完成25~50例手術后,學員才能達到相對穩定的操作水平[12]。對腹腔鏡肝切除術學習曲線的研究[13-14]表明,術者在完成37~42例手術后學習曲線進入平穩期。在學習曲線的初期,學員難免會有較高的錯誤率[15]。然而,如今醫師人數不斷增加,年輕腔鏡醫生在手術室內的實踐和練習機會有所減少。為保障患者安全,亟需一種手術室外的訓練方式,即模擬訓練。模擬訓練為學員提供了在高效、安全的訓練環境中進行手術室外腔鏡技能訓練的機會,有助于積累操作經驗,縮短醫師手術室內訓練時間,避免學習曲線上的高錯誤率階段出現[16]。
為確保醫師腔鏡訓練的有效性,確保其培訓成果能夠提升腔鏡手術技術水平[17],有必要建立標準化的考核評估體系。這一體系主要包括“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前者作為訓練過程中的考核,持續為訓練者提供反饋;后者則是對學員訓練成果的綜合評估,用于確定整體訓練的合格情況[4, 18]。通過不同階段和不同維度的考核,能夠客觀反映腔鏡訓練效果,提升腔鏡技能培訓水平。
1 腔鏡外科技能培訓與考核研究現狀
1.1 腔鏡外科技能培訓設備
目前常見的腔鏡外科技能培訓設備主要是腔鏡模擬訓練箱[19],其類型可分為實體模具和虛擬仿真模具。實體模具通常采用硅膠材料或動物實體器官來模擬人體體腔結構,通過操作真實的腔鏡手術器械進行抓持、傳遞、裁剪、縫合等訓練[19-20]。這種方法有助于學員練習必備的腔鏡手術基本技能,并提供了近似真實的腔鏡器械操作體驗。其設計簡單易推廣,但普遍缺乏對訓練效果進行客觀評價的標準。
虛擬仿真模具以虛擬現實和人機交互的形式實現訓練目的[21-22],可以在虛擬環境中進行精細解剖、組織切除等腔鏡基本技能的訓練,還可以模擬各種基本手術流程。此外,基于人機交互,能夠實時記錄學員的操作數據,并對學員操作水平進行動態、客觀的評價。然而,虛擬仿真模具的力反饋等人機交互系統尚無法完全還原實際操作的感覺。研究[21]顯示,相比于實體模具訓練箱,虛擬仿真模具在培訓效果上并沒有明顯優勢,其昂貴的價格也限制了廣泛應用。
1.2 腔鏡外科技能培訓和考核體系
國內的腔鏡培訓尚未形成統一的體系,目前仍由各醫學院校或者醫院因地制宜開展。例如,北京協和醫院泌尿外科提出了基于SMART(specific,measurable, attainable,relevant,time-bound)原則建立的三階段腔鏡規范化培訓模式[23]。該模式按階段逐漸深入,首先是器具模擬訓練,包括熟悉夾持、切割、縫合等操作。只有器具模擬訓練合格后,學員才能進行動物離體手術訓練,掌握手術方式的規范操作模式。在通過動物離體手術考核后,學員才能參與真實的人體手術培訓。其他國內院校也提出了類似的三層次培訓模式。例如安徽醫科大學的外科基本操作訓練、腔鏡基本理論授課;腔鏡模擬器訓練、手術錄像教學;腔鏡手術中的扶鏡及一助操作訓練[24]。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提出包括解剖影像基礎、胸腔鏡操作意識和臨床實際操作的三層次培訓模式[25]。這些培訓體系強調層次遞進的培訓模式,但實際應用情況有所不同,目前多限于院校內部使用。
在北美地區,廣泛應用的腔鏡訓練考核系統是美國胃腸內鏡手術學會于2004年提出的腹腔鏡手術基礎操作(fundamentals of laparoscopic surgery,FLS),已得到美國外科醫師學會認證[26-27]。FLS旨在為腔鏡醫師提供標準教材,并為理論知識與技能提供相應的評定標準[26]。其訓練和考核項目包括傳遞、裁剪、圈套器結扎、縫合與體內外打結[28]。有研究[29]表明,FLS培訓可以顯著提升學員在實際手術中的操作水平。然而,成績評定的主觀性、反饋滯后以及較高的費用等因素限制了其推廣應用[30]。因此,一些中心開始嘗試構建自動化的FLS考核方式[31],客觀化和自動化考核是FLS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
在歐洲地區,應用較廣的是歐洲婦科腔鏡協會和歐洲婦科腔鏡培訓學院在2004年聯合開發的婦科內窺鏡外科手術教育與評估系統(Gynecological Endoscopic Surgical Education and Assessment,GESEA)[32]。腔鏡醫師首先進行線上教程學習,隨后在系統模型中進行訓練及考核[33]。近年來,國內部分醫院也在醫師培訓考核體系中引入GESEA,有些地區還開展了基于GESEA的腔鏡外科技能比賽。例如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婦產科報道了GESEA對住院醫師腔鏡手術技能的提升作用[34]。然而,該項目的考核結果主要依賴于考官對GESEA標準與考核者表現的人工比對[28],因此存在較強主觀性。
總體而言,目前腔鏡模擬培訓主要側重于理論課程學習和模擬訓練,并且考核多依賴人工評分。由于缺乏統一的考核標準,主觀評分難以準確體現腔鏡模擬培訓效果,未來重要的研究方向將是如何建立客觀的考核標準。
1.3 腔鏡外科技能考核標準
國內腔鏡模擬培訓技能考核標準多基于完成傳遞、裁剪、縫合、打結等操作所用時間和操作流暢度,在合格分數線設置方面尚無統一的標準,且流暢度主要依賴考官的主觀評價[35-38]。相較之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Vassiliou等[39]提出的全球腔鏡手術技術評估(Global Operative Assessment of Laparoscopic Skills, GOALS)在國外得到了廣泛應用[40-42]。該評估方式基于5個領域評價醫師的腔鏡外科技能水平,包括深度知覺、雙手靈巧度、效率、組織處理和自主性。考官通過肉眼觀察打分,每一領域評分以1~5的整數表示,描述性的分界點為1、3、5分[40] (表1)。通過分析腔鏡醫師在各領域的考核平均分,可區分初學者與經驗豐富者,同時GOALS評分也能很好地反映FLS訓練成果[43]。然而,這種考核方法仍局限于考官對學員操作的肉眼觀察和主觀評價,一方面缺乏客觀評價標準與手段,另一方面需耗費大量師資和人力。
2 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的研發和應用
針對以上問題,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劉倫旭、廖虎牽頭研發了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44]。通過圖像識別、精細化感知等技術,涵蓋了視野定位、抓持、傳遞、精細裁剪和縫合打結共5個腔鏡基本操作模塊,實現了智能化腔鏡技能培訓與考核。該系統利用智能算法,將難以量化考核的臨床操作技能轉化為可測量、可評估、可重復的客觀考核指標。技能考核評分的過程實現全自動化,無需人工參與。該系統還能進行實時數據反饋:系統在學員訓練過程中動態收集數據,并提供客觀評分和個性化學習方案;同時,結合大數據處理、深度學習與長短期記憶網絡技術,動態更新、貼近臨床要求的考核標準,提升了評分標準的客觀性。初步研究[45]表明,相較于傳統的人工評估,該系統可以更好地區分腔鏡技術水平。該系統使微創外科培訓的評估手段和標準從主觀走向客觀,做到規范化、可量化,提升了可控性和工作效率,從而實現腔鏡外科技能的標準化、自動化和智能化評估(圖1,表2)。
 圖1
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設備
圖1
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設備
以華西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為契機,經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立項,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組織實施了“四川省基層醫院微創胸外科能力提升項目”,為達州、西昌、涼山州、甘孜州等地區的醫療技術、醫療硬件各方面提供幫助。項目已在24家縣級建設醫院開展試點,并完成了各建設醫院智能腔鏡培訓與考核教具的配置和使用培訓。通過短期專項培訓、專家現場示教、手術指導、線上遠程教育、遠程會診等方式,穩步提升建設醫院的醫療水平。在項目的持續推動下,這24家建設醫院已全面開展微創胸外科手術,部分醫院已實現微創胸外科手術的自主開臺,醫院門診量、手術量、微創率顯著提升,部分醫院已單獨成立了胸外科。
3 討論
目前國內部分醫學院校和機構開展了腔鏡培訓和考核的探索,但系統化、標準化仍有欠缺。相較之下,FLS、GESEA腔鏡培訓系統和GOALS考核體系在北美、歐洲應用較廣泛,但仍存在系統項目模塊設置較單一、評價標準客觀性不足等問題。
為提升腔鏡培訓與考核系統,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1)制定統一的腔鏡操作規范,為腔鏡外科技能訓練和考核提供明確指導,使訓練、考核標準更加科學合理,符合臨床需求;(2)統一培訓考核項目與評分標準,以便高效地分析訓練結果和制定下一步訓練計劃,促進培訓與考核系統的推廣;(3)加強考核評分客觀性,利用智能算法消除人為主觀判斷對于學員評估的影響,從而對學員的培訓成效進行準確評判;(4)縮短腔鏡模擬培訓和真實手術操作的差距。研究[46]表明,訓練者在模擬訓練得分與手術室中表現分數存在差異,如何縮小這一差距是未來研究的重點之一。
綜上所述,腔鏡模擬訓練與考核系統的建設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面臨多方面挑戰。通過制定規范、統一培訓考核項目與標準、增強客觀性以及縮短培訓和真實操作的距離,可以進一步提升腔鏡模擬訓練與考核系統的價值,為培養高水平的腔鏡醫師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劉倫旭主導研究實施,負責選題與設計;周健、廖虎和鄭權參與文獻收集和分析;全體作者參與文章撰寫及審閱。